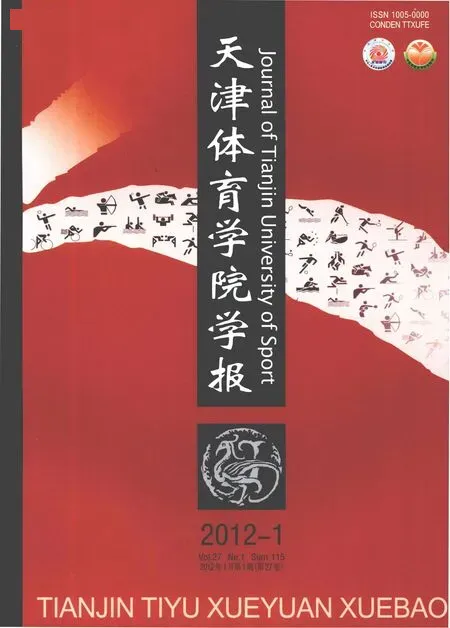关于确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的思考
王显荣
关于确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的思考
王显荣1,2
司法介入竞技体育纠纷的理论障碍主要在于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德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给该原则以理论支持,然而今天,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势微,我国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缺乏中立的体育仲裁制度保证,且其本身过于绝对,再加上我国现行体育社团内部解决机制因受体育行政权的制约而缺乏独立性。故应当确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并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和章程、设立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和体育法院来实现。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举国体制;体育仲裁;司法介入
近年来,司法能否介入竞技体育纠纷,已成中国体育界和法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这必将影响我国体育法治的发展进程,远的如“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诉中国足协”、“广州吉利集团诉中国足协”等,近的如“王濛与领队王春露爆发冲突”。对竞技体育纠纷的救济方式,理论界提出的解决方案除了落实《体育法》规定的仲裁机构及规则外,就是将竞技体育纠纷纳入司法机关的受案范围,并已从法理角度论证了该观点的合法性,但现实中该方案并未被司法机关采纳[1]。实际上该方案无法绕过《体育法》有关非刑事类体育纠纷排除司法介入的规定。因此,务必打破现行《体育法》所确立的纠纷解决框架,重构解决此类纠纷之理论根据。
1 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的指导原则——纠纷解决自治
鉴于竞技体育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等特点,以及其纠纷解决的效率要求和体育纠纷需要内部解决等特点,应当赋予体育行业以自治的方式进行管理,故世界上多数体育行业章程和规则均规定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司法介入。那么我国对该自治原则的态度如何呢?
1.1 我国体育立法和体育规则有关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的规定
我国现行《体育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该规定在打破体育社团垄断纠纷解决的同时,也为司法介入非刑事类体育纠纷关上了大门;第四十九条就纪律处罚权作出了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第八条规定:“在中国足球协会主办的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由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负责审核处理……”;第九十二条规定“纪律委员会的处罚决定一经发出或者公布立即生效”;《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中国足球协会各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中国足球协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中国篮球协会《2010全国男子篮球联赛纪律处罚规定》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所有处罚自主办单位公布处理决定之日起生效,主办单位的处理决定为最终决定。综上,我国立法和各体育协会章程及处罚罚则等通过上述规定,确立了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
1.2 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体育法》和各单项体育协会章程等规定导致很多人都误认为,竞技体育纠纷只是体育社团内部的事,应当遵守由体育社团内部解决的纠纷解决自治原则。鉴此,无论是2002年前对假球、黑哨的调查打击,还是最近对王濛与领队王春露之间冲突的处理,相关体育社团均没有做出令社会普遍接受的处理结果,最后都是以不了了之收场。体育社团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到底能否胜任解决竞技体育纠纷这一职责,则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而作为社会纠纷解决的最后屏障的司法也迟迟不见全面介入[2-4]。之所以说司法没有全面介入,是因为司法拒绝介入也并非象过去那样铁板一块,其在某些领域已有所松动,如从2003年足球裁判龚建平被判刑到近年的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谢亚龙、中国足球裁判委员会原主任李冬生、中国足球队原领队蔚少辉等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和审判,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六)的出台,表明我国司法介入体育刑事犯罪领域已不存在多大障碍,争议的仅仅是介入的广度问题。而在体育行政诉讼领域,“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诉中国足协”、“广东凤铝诉中国蓝协”等案件的起诉过程及审理结果表明,司法机关仍然严守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而拒绝介入[5]。而在体育民事诉讼领域,尚无案件因起诉到法院而引起全国关注。至于黑龙江五大连池法院判决身陷兴奋剂丑闻的孙英杰是被人下药、其名誉权被侵害一案的性质及所涉及的问题,则与上述案件均不相同。第一,该案不属于竞技体育纠纷。该案发生在竞技体育过程中,由与该竞赛无关的局外人海江的介入而引发,虽然其结果影响了运动成绩,但作为孙英杰与侵权人海江之间的法律关系来说,属于普通的民事侵权关系,与体育无涉。第二,田协的处罚程序与法院审判的关系。法院审判的对象是海江侵犯孙英杰名誉权,该案判决结果只能附带证实孙英杰服用兴奋剂时不具备主观故意,田协审理的是孙英杰是否服用兴奋剂,两者审理的对象不同,不能用法院审判来代替田协审理。第三,法院的判决对田协处罚孙英杰一案有无既判力。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判决认定的事实无需证实,其他机构应据此认定孙英杰不具备主观故意。第四,田协处罚服用兴奋剂运动员是否以运动员主观故意为前提。如果需要,那么孙英杰不应被处罚,因为从法理上讲,法院判决认定孙英杰不具备主观故意的事实应当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其他组织具有既判力。反之,法院判决则对田协不具有既判力。“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的反兴奋剂条例,对于服用兴奋剂不管原因如何,只要查出服用就要处罚,实行看结果不论原因的严格责任原则。”[6]故田协对孙英杰的处罚正确。第五,假如海江是此次比赛的参赛队员,那么该案就不再是普通民事纠纷,而是竞争型体育纠纷,按照《体育法》的规定,法院不得介入,只能由田协处理。但如果法院不顾前述法律规定,受理并作出了生效判决,在前述判决未被审判监督程序撤销之前,对田协具有既判力,田协不得作出相反的裁决,即便作出了,也当然无效,国际惯例不能成为田协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借口,其法理类有点类似于欧盟法院在博斯曼案裁决中所依据的法理。
1.3 我国现行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当前国内反对司法介入的主要理由就是体育行业作为行业的一种,应当实现行业自治,而行业自治的理论依据则是德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7],根据该理论,体育社团之成员“基于维护行政之功能和目的以及国家或营造物的特别依存关系,个体在进入国家或营造物时,就必须放弃其个人的自由权利,而特别权力关系由此而产生”[8],既然该放弃系基于成员的自愿,也就无所谓侵害,体育社团则据此获得对其成员的绝对处罚权,并可随时根据内部规定施加处罚,无需法律授权,并排斥司法介入,故不宜将这类纠纷纳入法院的受案范围。而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正是我国现行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至于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否走样,则另当别论。作为世界竞技体育的一部分,我国在制定《体育法》和各项规则时,无疑借鉴了世界竞技体育所共有的一些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有其理论根据,至于其内含的各种理论依据是否在借鉴时被意识到,并不影响该理论依据的实际存在。尽管“20世纪中期以后,原来被严格限制的司法权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审查范围逐渐放宽”[9],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并不是彻底消亡,其仍继续为各行业自治提供理论根据,体育行业也不例外。这从国际体育组织及各国的体育立法或规则均规定了纠纷解决自治原则即可得到证实。
2 对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之批判
2.1 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过于绝对化,与司法介入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不符
根据前面的论证可知,我国体育纠纷解决在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绝对排除司法介入。而在体育刑事诉讼领域,虽然对龚建平涉及黑哨一案在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但龚建平是以个人名义被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所定罪名与体育无关,而对于涉及比赛的体育社团和龚建平所属行业协会的行为并没有被追究刑责[10]。而纵观国际体育组织和许多国家有关体育规则或立法和实践,司法早已介入。首先,在许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章程中都规定了在穷尽体育组织内部救济的情况下,其成员不仅可以向CAS等国际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还可以直接起诉到瑞士联邦法院,寻求司法救济[11];其次,一些体育发达的欧洲国家已就是否应当拟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来处理竞技体育纠纷这一问题多次召开过理论研讨会。如欧洲理事会体育发展委员会与法国青年与体育部于1995年10月在法国巴黎共同组织召开了《在诉讼机构还是通过体育组织解决争议问题》的理论研讨会,欧洲35个国家的50多位代表参加了该研讨会[9];再次,许多体育发达国家在其体育立法中都规定了可以启动普通法院司法程序或设立专门的体育(准)司法机构来裁决体育纠纷,从而为司法介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例如英、美、德、法、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当事人均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有关裁决诉至法院。最后,提到司法介入的判例,国外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判例当属博斯曼案件,而该案最终的判决结果表明,体育行业规则与欧盟条约(法律)相冲突时,体育行业规则无效。
2.2 与国际体育组织和许多其他体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缺乏配套制度保证
国际上各大体育组织为追求裁判标准尽可能一致,并确保在裁判技术上能够胜任和立场上的中立,设立了一些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其名称从《纪律委员会》到《国际仲裁庭》等不一而足,如国际奥委会在洛桑设立了CAS。此外,许多体育发达国家也充分借鉴CAS的成功经验,分别结合各自的国情,建构了自己的体育仲裁机制:要么创设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或综合性的体育纠纷解决机构),如日本体育仲裁机构(简称JSAA)和英国体育纠纷解决中心(简称SRs);要么在已有国家仲裁机构内分设专门的体育仲裁小组,如在美国,除冰球、棒球、篮球、橄榄球等四大职业体育运动联盟内部设有仲裁机构外,其他的体育协会大多在其章程或规则中明确由美国仲裁协会专门设立的体育仲裁小组处理有关的纠纷;要么在全国管理性质的体育行业协会内部设立高度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12-13]。反观我国,虽然《体育法》明确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协调、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国务院至今还没有“另行规定”,导致我国体育社团事实上仍然垄断着体育纠纷裁决权。
2.3 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即举国体制决定了现行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缺乏独立性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被称为举国体制,是指我国为了在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国际竞技体育大赛上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在发展竞技体育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制度设计[14]。“组织一条龙”是对竞技体育管理方式行政化的高度概括。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引入市场因素后,虽然形成了以政府管理为主、社会管理为辅的新型管理体制,但实质上仍为举国体制。因为“随着我国行政机关的机构改革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的历史变迁,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目前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基本上也是合署办公,中国奥委会的工作人员大体上是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人员。”[15]至于中国奥委会下的各单项体育协会,其领导由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或指派,甚至由政府部门领导人兼任,并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各单项体育协会规制竞赛财务的规范系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财务管理办法》,尽管各单项体育协会可以收取会费,但不占其经费的主导地位,其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其普通工作人员也按国家事业单位编制工作人员对待,领取行政工资与国家福利,因此,在现行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下,实质上运动管理中心与体育协会尚未彻底分离,协会尚未彻底实体化,从而导致体育社团对体育行政权的严重依赖,其日常管理中难免受到行政权的制约,更不必说裁决纠纷了,因此,现行竞技体育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独立性。
3 对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之扬弃
3.1 我国竞技体育应当保留纠纷解决自治权
3.1.1 竞技体育固有特点和规律决定了体育社团应拥有纠纷解决自治权 竞技体育具有如下特点和规律:首先,具有即时性。由于在竞技体育比赛中,运动员或其他参与人的权利等到活动结束时不可能恢复,这就要求必须及时裁决纠纷,而由社团内部相关机构按照其已有的规则处理纠纷比其他手段较为即时。其次,具有技术性和专业性,这决定了有时依靠行业外的解决根本行不通,如在悉尼奥运会期间,CAS在Bernardo Segularvs.IAAF案就明确指出:“CAS仲裁庭不会审查由负责实施运动规则的裁判员在竞技场上做出的裁定,除非该规则是因恶意而实施,如是因为贿赂而得之结果”[16]。第三,纠纷裁决依据具有特殊性。对竞技体育纠纷,尤其是那些只可能发生在竞技体育领域内的,除依据法律外,还必须主要依据行业惯例和行业规则裁决,否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亵渎体育精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于运动致人伤亡不能按犯罪对待,而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即便过失致人死亡也应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体育专业人士比法官更熟悉相关惯例和规则。最后,纠纷救济方式具有特殊性。运动员及其所在的组织提请解决纠纷的首要目的在于恢复其某些权利,只有在在权利不能恢复的情况下时才会主张赔偿,因此这类纠纷之救济必须是以恢复其权利为主,赔偿为辅[17]。而只有体育社团才有及时恢复权利的权力和便利。
3.1.2 拥有管理自治权和处罚自治权系体育社团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作为社会群体的社团,必然要有能力对其成员之违反其要求的行为做出反应[18],这种反应即是指享有处罚权。同时,社团为了充分实现其目的与管理职能,客观上要求赋予其相应的内部裁决权[19]。只有行使处罚权和裁决权,才能保证其内部的稳定和统一。而社团只有首先实现了内部的统一和稳定,才能集中力量与外部进行有效的竞争,并获得发展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任何一个社团,都需耗费大量精力去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和协调内部关系[20]。体育社团也不例外。鉴于体育行业的特殊性和专业性,通过体育社团内部处罚和裁决来解决纠纷,比起其他解决模式更容易协调内部矛盾和平衡相关各方之利益。综上,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确保体育行业正常运行的关键在于其内部的自律和自我裁决。如果体育社团自己能够有效地管理体育运动,并自觉做到以体育规则规制体育运动及其纠纷,那么司法则缺乏介入的理由。“除非有关行为已经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其存在已经超出体育规则的范围和纪律约束,涉及到公平、公正问题,进而会涉及到法律问题,这才需要国家司法机关的介入。”[18]从尊重体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出发,其社团应当享有处罚权和裁决权,司法应当对其自治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我国司法也不应有例外。
3.2 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的确立及其在理论上的障碍和克服
3.2.1 应当对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加以限制即确立有限自治原则 正如前文对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批判时所论述的一样,由于我国现行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既缺乏独立性,又缺乏中立的体育仲裁制度保证,而该纠纷解决自治过于绝对化,与世界上的司法早已介入的发展趋势不符,而支撑纠纷解决自治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国外已经被加以限制,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国外实践来看,都需要从社团以外对其内部纠纷解决的自治权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方式主要依赖体育仲裁和司法介入。
3.2.2 司法介入的障碍及其克服 对于仲裁介入竞技体育纠纷,已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并且我国《体育法》已明确规定,故不存在争议,争议的只是介入的方式。然而司法介入仍然存在着法律和协会章程上的障碍,并且“举国体制”确系我国国情,目前还没有其他先进的体制能够取代其地位,故立法上就不能无视其存在,而应根据我国国情,修改《体育法》以及《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等相关内容,赋予司法介入的机会,从而赋予我国竞技“体育自治”适合国情的内涵,而不是固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的规定,毫无意义地争论体育社团是否取得授权。
3.2.3 对司法介入的限制 目前体育界和法学界对司法介入都心存顾虑。这就要求司法在介入时应当受到更多限制,至少要受到以下3项原则的限制:仲裁协议效力优先原则、用尽内部解决原则和技术事项例外原则。概括上述3项原则,就是指任何竞技体育纠纷均可诉至法院或被司法机关追究刑责。对于体育仲裁和司法解决模式,或裁或审模式是对仲裁与司法关系的法理定位,那么体育仲裁与体育司法的关系也不应有例外,因此,一旦当事人协议选择了体育仲裁,则法院不得受理任一方当事人之诉讼。即便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体育仲裁,司法也应当保持谦抑的态度,应当在当事人用尽体育社团内部救济手段后才能介入。而对于某些临场技术性纠纷,应由临场裁判及临时设立的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司法不必介入。“但是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处罚引发的是否公正问题和因职业运动员与金钱有关的案件,或者是体育行政或刑事案件,司法介入则是责无旁贷。”[22]由此还可见,司法介入不单指司法机关对体育刑事案件、体育行政争议案件或当事人诉请的体育民事纠纷案件中某一类案件的处理。“换言之,体育纠纷的司法介入包括3种情形,即体育民事纠纷、行政争议、刑事犯罪的司法处理。”[21]
4 实现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之机制保障
4.1 司法机制保障
英国、美国和瑞士等使用普通法院兼司竞技体育纠纷,法国行政法院全面干预体育联合会的管理,例如行政法院通过的法令来确定该联合会的章程,且章程的内容和形式必须与该法令规定的样本相一致[23]。意大利行政法院审查体育行会行使公共职能的行为,而民事法院管辖普通民事性质的体育纠纷[24]。可见,世界各国司法介入的方式也并不完全一致,那么,我国到底应当借鉴哪国经验来处理体育纠纷呢?对此,一种“我国设立体育法院专事解决体育纠纷似不可行,一方面难以保证司法权的完整统一,另一方面亦难以建立相应的机构”[21]的观点被广泛引用,但该观点并不正确。首先,我国本来就存在专门法院,他们都是按特定的组织或特定范围的案件建立的审判机关,也都是我国统一审判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故设立体育法院并不破坏我国司法权的完整统一,建立体育法院也不存在困难;其次,尽管目前存在取消铁路运输法院的说法,其最主要的理由在于这类法院作为官商结合体,与1999年转制前的海事法院一样属企业性质,其经费保障模式为“自收自支”或称“以收抵支”,诉讼费收入成为法院主要经费来源,导致这些法院的经费得不到保障,此外还存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弊端。但笔者认为不必取消,可以象海事法院一样,转制归地方供养而不改变其受案范围,实践中铁路法院也正按此模式转制。因此,如果设立体育法院,与现在的海事法院一样划归地方供养,不存在上述弊端。第三,该观点不了解我国司法严重地方化和行政化的弊端,若按该类案件的性质跨地区设置体育法院正好可以摆脱地方体育行政权的制约;第四,该观点完全脱离了我国法院审判实践,即便体育审判庭组成人员既懂法律又懂体育,但也无法保障审批案件的庭领导和分管院领导以及审委会委员们都既懂法律又懂体育,并且竞技体育有很多种类,要求按照不同种类的体育纠纷配备法官不现实。综上,为了确保此类案件审理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我们可以借鉴国外设专门法院的做法,设立体育法院,在审理某些专业性较强的体育纠纷案件时,可以邀请相关专业人士作为人民陪审员。
4.2 体育仲裁机制保障
《体育法》规定由国务院制定体育仲裁条例,而《立法法》第八条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也就是说,仲裁事务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根据《立法法》,国务院行政法规不能规定只有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才能规定的立法事项。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的原理,应当执行《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即通过制定体育仲裁法或直接修改《体育法》来设置我国体育仲裁机制。至于有人提出《体育法》属于授权国务院规定体育仲裁条例,即便如此,因违反《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也应当以后者为准。而制定体育仲裁法的难度不小,社团章程具有民间性,系成员意志的集中反映,因此,只有有利于保护成员自身合法权利的修改,成员一般会支持,关键在于现实中体育行政机关不再阻挠修改即可,这就要看我国政府有无彻底治理这类纠纷的决心,如果有的话,修改章程比制定或修改法律容易,因此,当务之急,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25],修改各社团的章程,表明接受CAS的管理,由CAS来作为我国国内体育纠纷的最终解决机构。
从长远来看,则应当通过制定体育仲裁法或修改《体育法》来设置我国体育仲裁机制。对此,不少学者主张“在国家体育总局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在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内设立体育仲裁庭。体育仲裁委员会的经费由国家奥委会和中华体育总会负责拨付,并可以接受社会捐助。”[26]这种思路似乎受到我国法院设置的启发,但我国法院设置模式已遭诟病,作为纯民间组织的体育仲裁再采此模式,其中立性何来,值得深思。应当注意到,在“全国体总和后来的中国奥委会仅在名义上存在,体育管理职权由国家体育总局的各司处负责”[27]大背景下,“专职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从体育行政部门中专门从事体育纠纷处理工作并具有仲裁员资格的人员中聘任”[26],经费由全国体总和后来的中国奥委会负担实际上成了国家体育总局负担,这样一来,岂不是人财物实质上完全受制于国家体育总局?鉴此,建议一步到位设立独立于任何机构的纯民间的体育仲裁机构,命名为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如CAS一样,在大型体育竞赛期间可设立临时派出机构。同时,为了减少经费支出,只设立兼职体育仲裁员,“从具有仲裁员资格的资深教练、运动员、专家、学者、律师中聘任。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奥委会成员不得兼任仲裁员,仲裁员与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奥委会、体育行会或其他体育组织无利害关系。”[26]至于经费,则主要由仲裁费来解决,但也不排除社会捐助。同时鼓励民间自行设立体育仲裁中心,与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共同参与市场竞争。至于仲裁制度和程序方面,采取协议仲裁、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的原则。其受案范围应为与竞技体育运动有关的一切纠纷,但刑事纠纷除外。仲裁裁决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对外公开。法院对体育仲裁裁决只进行程序问题的司法审查,并遵守“承认当事人自愿放弃司法救济”原则。仲裁时效方面,借鉴日本《体育仲裁规则》的规定,运动员必须在得知体育协会裁决结果之日起的4周内或者裁决生效之日起6周内提起仲裁,否则丧失提起仲裁权。
[1]高升.我国体育协会内部纠纷的法律救济—以体育仲裁与司法介入的关系为中心[J].体育科学,2009(8):41.
[2]郭春玲.中国体育社团改革的若干法律制度设计[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6):7-10.
[3]谭九生.论体育社会惩戒权的边界 [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6):44-47.
[4]徐海柱,马红娟.体育社团法治环境与法律保障机制构建[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4):31-34.
[5]裴洋.对职业体育联赛准入制度的反垄断法分析—兼评“风铝事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8(6):24-28.
[6]张鑫.孙英杰减轻处罚为何没有指望 [E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12/21/content_239220.htm,2011-09-06.
[7]冯之东,徐志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行业自治中的适用—以中国足协为研究个案[J].社科纵横,2007(2):88.
[8]蔡震荣.行政法理论与基本人权之保障[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
[9]林卉.浅析司法介入体育纠纷的难度及理由[J].浙江体育科学,2007,29(5):6-9.
[10]胡建淼.体育竞赛法律纠纷与对策 [EB/OL].http://www.sport.gov.cn/n16/n1152/n2523/n377568/n377613/n377703/392388.html,2011-09-06.
[11]KebaMbaye.Introduction to Digest of CAS Awards III 2001-2003(A).Digest of CAS Awards III 2001-2003 (Z).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
[12]张恩利,周爱光.竞技体育仲裁发展演变初探[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25(6):15.
[13]沈建华,汤卫东.职业足球俱乐部纠纷解决机制探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5(3):8-11,20.
[14]王伯超,吕树庭,高建磊,等.举国体制视野下的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体制改革[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11):1 450.
[15]周玲.北京奥组委与中国奥委会法律地位比较 [J].体育文化导刊,2003(6):10.
[16]Frost H M.Wolff's Law and Bone's Structural Adaptation to Mechanical Usage:Anoverviewfor Clinicans[J].Angle Orthod,1994,64:175-188.
[17]李江,周玲美,肖威,等.论体育仲裁的特征[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5,19(2):40.
[18]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23.
[19]Terry Mcmorris.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decision-makingskills[J].Int J Sport Psychol,1999(30):151-172.
[20]赵许明.体育社团处罚权与司法审查权关系之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5,41(4):42.
[21]魏波,罗大钧.体育纠纷司法介入之思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4):6-8.
[22]汪跃平.论我国体育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优化[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7(3):54.
[23]Mcmorrist,Graydonj.The Effect of Exercise on the Decision Making Performance ofExperienced and Inexperienced Soccer Players[J].Res Q Exe Sport,1997,(67):109.
[24]郭树理.意大利体育法律实践初探[J].浙江体育科学,2003,25(4):2.
[25]郭树理.德国体育法律实践管窥 [EB/OL].http://www..chinalawinfo.com,2011-09-06.
[26]陈进华,王纪荣.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制度探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8,22(5):39.
[27]秦椿林,张春萍,魏来,等.再论“举国体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4):437.
Thought about Establishing a Limited Autonomy Principle for Resolu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Disputes in China
WANG Xianrong1,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0031,China;2.Zhuhai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Zhuhai 519002,China)
The theoretical obstruct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 in competitive sports disputes is mainly the autonomy principle for resolu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disputes.This principle is supported by the Theory of Special Power Relationship,but it losses gradually its affection nowadays.The autonomy principle for resolu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disputes lacks neutral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to guarantee,and it's too absolute.In China,the current sports community sports dispute internal settlement mechanism is restricted by sports administration power and lack of independence.So we should establish a limited autonomy principle for resolu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disputes in China,which is realized by modifying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port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and sports court.
Theory of Special Power Relationship;the autonomy principle for resolution of sports disputes;the limited autonomy principle for resolution of disputes;whole nation system;sports arbitration;judicial intervention
G 80-05
A
1005-0000(2012)01-0049-05
2011-09-06;
;2011-12-05;录用日期:2011-12-08
王显荣(1973-),男,四川广安人,助审员,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体育法。
1.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401120;2.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珠海519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