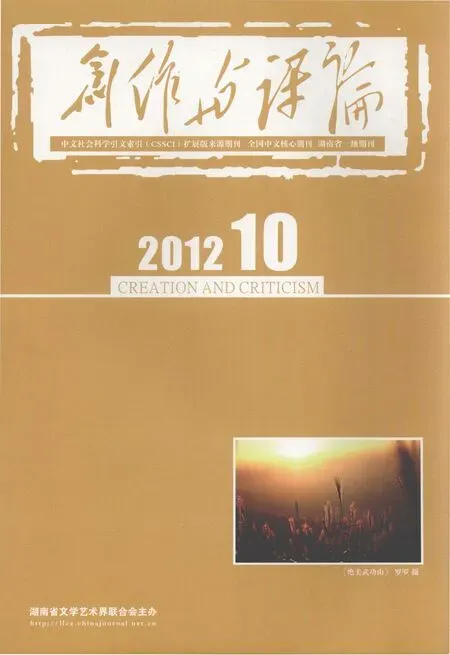夏夜书话
■周迅
一、5.57元的那套书
在我的一万多册藏书当中,有一些书是与个人的经历和成长密切相关的。比如那一套1974年7月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1974年,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幸运”地从“五七干校”被“解放”,降职下放到农场工作。我和小弟自然也随父母从省城来到位于湘江之滨的这家农场。
那个时候学校已经完全按照“领袖指示”,以“学农,学工,学军”为主,同学们似乎也已经习惯了不读书的生活。偏偏我这个城里来的小孩天生喜好书籍,把不知什么时候积攒的几分钱几角钱,都用来买书。农场供销社里有一个很小的柜台,放了寥寥可数的十来本书,大多数还是“批判材料”,偶尔也有几本“供内部参考”的读物。我便是这一类读物的常客。
这年秋季的一天,下午放学(其实是“学农”——做完红砖),我照例又来到“书店”(固执地要把三尺长的柜台叫做“书店”,是我在同学面前可以吹牛的事情)。宋阿姨(供销社专门负责书柜的营业员)悄悄地告诉我:“来了一套好书,我给你留着呢。”她十分神秘地从一个纸箱里抱出一堆书。红色封面的《十万个为什么》全套。
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感觉,那“一堆红”像电一样击麻了我。
颤抖着手翻开其中一卷,“说梦话,梦游是怎么回事”,“人触电后怎么办”,“狐臭是怎么回事”……
“买,买,买。”急切的声音引得宋阿姨笑了起来:“我知道你会买,那你交钱。”
慢慢镇静下来以后,我开始从头翻到尾。每一本的扉页全是毛主席语录,共有四段,最后一段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全套13卷,每本0.34-0.48元不等,共计人民币5.57元。我呆住了。要知道,当时我们班一个农村同学,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是4块多钱。我父母的工资据说不低,但当时真正每个月能拿到手的钱也多不到哪里去(因为是降职使用,工资自然也降了许多)。
“你一定要帮我留着书,我回家去要钱。”我郑重地说。
“那你要快点,时间长了别人要买我就没办法啦。”
父亲是一位南下干部,一辈子勤劳节俭,虽然自己也十分爱学习,但听说一下子要拿出全家人一个月伙食费的三分之一,只说了一句:“再等等吧。”
这一等就是三天,这三天让一个十来岁的少年知道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
第三天下午,宋阿姨严肃地通知:“明天还不买,就被别人买走了!”
母亲是位知识女性,对子女的学习最是支持。关键时候她说了话:“只要是学了知识,少吃点菜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是怎样地飞跑着到的“书店”,在书柜被锁上,要下班的最后一分钟,我抱到了那“一堆红”。
后来的故事简单但有趣。
每天读十来页书,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我的屁股后面就跟了一群同学。开始还只是同班的,后来是不同年级的。一路上就听见一个文弱少年在问:“知道吗,xxxx是为什么?”一群跟屁虫就问:“为什么?”这少年就洋洋得意地解答。
如果说文革开始时我的童年一片黑暗,那么这个时候,我少年时代的这一刻,则是一地阳光。此后的三十多年,我从嗜书、著书到讲书、评书;由一个普通工人到研究生,由一个习作者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八部文学艺术作品集,与这一套今天在某些学者看来颇为“不上档次”的《十万个为什么》,实在是息息相关。也许可以说,是年少无知时的好奇和虚荣把我引入了书籍王国。但这一引入,却是功德无量。
现在,我把这“一堆红”(虽然早已发黄),放置在四面皆书的架子中颇为醒目的地方,它的对面,是早已在天国的母亲的像片。在我内心深处,母亲是我的上帝,过去是,现在还是,将来永远是;她像明灯一样在如白天的黑夜和如黑夜的白天照耀着我。她的目光永远护佑着我,更督促着我。
现在,当我坐拥万卷书畔,我思考着,最简单的最不容易。
大家都不读书,有人却在挖掘书中的“黄金屋”;不读书最容易,读书最简单,却是大不易。
吃饭是天大的事,买书是可有可无的事;把买菜的钱去买书,也简单,但一般人做不到。
我总是怀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氛围和人与人之间的感觉。那是一种简单。求学,探讨,不论高下,不分彼此;多么幸福的简单,但今天似乎做不到了。房子越住越好,车子越开越高档,酒席越吃越稀奇,读书越来越不时髦,人与人之间越来越说不清楚。这是复杂。让人无所适从。
其实也简单,佛祖有言:“别胡思乱想。”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取有所不取。
尽管不易,我还是坚持简单。在唐诗宋词里,我沐浴春风;在老庄东坡里,我畅饮甘露。
在那发黄的“一堆红”里,沉浸着我的亲情我的温暖。
二、想起了那些书目
早些年,我曾经对佛经发生了兴趣。每到一名山大寺,必“请”一堆经卷回家。开始,似乎能登高望远,读得多了、杂了,却“迷糊”起来。一次在某名寺拜访一位僧人,聊及此状,僧人曰:泛舟无定所,入山惟一径。这位师傅是皈依净土宗的,他打开自己的书柜,上百册经卷通是净土经。
茅塞顿开。其实又何止是读经,哪一门学问不是如此?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若不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罗马未必能走到。
所谓“学海无涯苦作舟”,说的只是一种态度。真正要想尽快抵达一个“好岸”,还必须要讲究方法。比方读一点好的书目。
曾经在读书界颇为时髦的一本书目是法国人贝尔纳·皮沃和皮埃尔·蓬塞纳二人编选的《理想藏书》(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30多年前,法国《读书》杂志为帮助读者选择值得个人阅读的书并建立个人的藏书架,从茫茫书海中拟定了以文学作品为主的49个专题,每一专题推出49种图书,并将49本书分为三个等级(前10本,前25本,前49本),以便读者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喜好来选择。
于是,一本49×49的书目成立了,2401篇书目和综合信息洋洋洒洒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感兴趣的是此书的分类,除了文学大类按地区、体裁分成30类,很方便查询以外,它还列出了科学、美食、礼仪、风俗和传说、战争、连环画以及造反、革命和反革命等19个较为别致的类目。
时间再往前推40多年,美国《吉斯周刊》的主笔兼发行人威廉·尼可尔斯请费迪曼教授 (此人为著名报人、专栏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拟订一张有益于读者的书单。费迪曼教授于是以《一生的读书计划》为题,采取与读者作100个简短对话的形式,每次以500—1000字勾勒作品、作者的轮廓,引导读者去读他介绍的书,总共约100余本文学名著。后来这张书单成了同名书籍。1981年花城出版社翻译推出此书。
这两本书目我都读过,除了收获以外,也有些遗憾。《一生的读书计划》没有收入一本中国名著。而《理想藏书》中,中国文学只在“亚洲文学”一类里,收入了《红楼梦》、《阿 Q 正传》、《狂人日记》、《唐诗选》、《骆驼样子》、《家》、《浮生六记》、《水浒传》、陈若曦的《尹县长》、《寒山诗》、郭沫若的《自传》、《拍案惊奇》、《聊斋志异》、袁宏道的《云石集》、《格萨尔王传》等十余种。而其他类别中,几乎见不到中国人的踪迹。
除了时代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东方封闭因素可能是造成这类格局的主要原因吧。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两本书目视为“佳侣”的。
读中国书,近代张之洞有《书目答问》,独树一帜。
有一年,我迷上了《鲁迅日记》,并非对先生“晴。无事。”之类的笔墨感兴趣,而是以为先生的“每日书账”颇耐人寻味。一日一日串下来,就等于鲁迅先生读书书目。从大师的“目迹”之中似可以得到一些明示。
曾有文学青年命我介绍书目,我很快(但不是敷衍)地向他们推荐两本“大路书目”。
一是《书林》杂志编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文科书目概览》。此书介绍文科10个科目的必读书和参考书千余种,是系统地打基础的向导。
另有季羡林先生主编(时为80年代初,不能完全体现季先生完整的治学特点)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外文学书目答问》(上下册)。这是一本普及型读本,推荐了中外文学及理论书目266种,亦属入门书。
而真正为我喜爱并循之渐进的书目是蔡尚思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史要论》(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高度浓缩而又画龙点睛的中国文化书目。
我倒不完全同意蔡老的每一个观点,但是老人家理出的“提纲”及其治学方法则着实给了我实在的帮助。
将近30年的业余读书生涯,由各种书目导引至自我消化,方才感悟“尽信书不如无书”、“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真谛。无系统不成方圆,无重点不出效应,无个性不得正果。
新近又买了两本好书目。
《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49—199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1994)
两家名牌老店的目录,可以当作中国现、当代文化及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虽说它们不能与《四库全书总目》(此书上下两大卷,我有幸于16年前搜藏了一部)比肩,毕竟是值得收藏的好书。
在书海徜徉日久,越发感觉书目之重要之可爱,由是,我视之为佳侣,引为终生之福。
三、那几个说真话的人
在早春一个阴冷阴冷的夜晚,我轻松地翻看着一堆史藉,感慨中国历史之不轻松,也庆幸秦始皇的时代已堆放于昨天,否则的话,二三人聚谈于街巷便要被砍去脑袋,实在是吓人。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大谈“今天天气”以外的许多事情和观点,尽管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毕竟脑袋不会轻易“搬家”了(而且自己的居室里目前还没有监视探头)。这个时候,捧着自己不欺骗自己的脑袋,回味一下关于真话,关于不该忘记的人临终前的真话,并不是多余的事情。比干、屈原、司马迁等老老前辈不提了,现当代的人物随手便可以牵上一串。
1974年11月,彭德怀已经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然而临终前,他却异常清醒:“我顶得住。我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他对侄女梅魁说,“我死后,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上一棵苹果树,让我报答家乡的土地……”
一代元勋,就这样含冤而去。但时间老人是公正的,彭德怀的真话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然而就那个历史的断层而言,将永远刻下悲剧的名字。以至今天的庐山上,依旧乌鸦常鸣,或许是历史的某种鸣示?
应当感谢巴金老人,在他的《真话集》中不仅秉笔直言世间事,而且留下了不少珍贵史料。比如赵丹临终前的那句话:“‘最高指示’、‘英雄形象’至今还在我的噩梦中出现,那么只有逼近死亡,我才可以说:‘没什么可怕的了’。”作为著名艺术家的赵丹先生,以真话为他的一生划上了令人信服的句号,虽然划得那样惨淡。
我们厌恶“面具”,我们憎恨虚伪,但在“面具”时髦,虚伪“价”高,真言遭忌的空间里,人又如何免“俗”?面对死神而能愤然无畏。“没什么可怕的了”……让人由衷起敬。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有一个小小的惊人的相似之处:蒋中正的高级秘书陈布雷和毛泽东的高级秘书田家英均以自杀了结生命。田生前很爱读史,他对历史的博学足够他学着随风就势把握自己的“历史”,然而他放弃了这一“优越”的“背景”,选择了真实的孤寂直至永远的沉默。他为真话所“误”,也为真话而留名。
与田家英悄然自尽相同,老舍先生也选择了默然而去的方式。我们今天读《骆驼 祥子》、《四世同堂》、《茶馆》是否能读出历史的某种关联呢?在太平湖畔,人们找到一些抄有毛泽东诗词的纸片,系老舍先生十分工整的毛笔字。猜测老先生告别这世界前,有过多么大的痛苦的心理过程,并且是一种扭曲了的真实在他的灵魂深处,该有怎样的真实要留下来呢?但却没有!这才是更大的悲哀。
我又想起周恩来临终前对邓颖超所说的话:“我有许多事情没跟你说……”邓也对周说:“我也有许多事情没跟你说……”现在,两位政治家都已远去,他们之间没有挑明的事情以及他们与更多的人没有说透的话,只有由历史去说了。但至少这也是一句“最后的真话”。站在我们民族的伤口上,透视我们自己,不能不承认对真实的掩盖和对真话的恐惧已经使我们的灵魂缺乏生动的魅力。而这一切,源于“左”祸的幽灵,源于小农经济与封建观念及大面积的混凝土般的结合。不妙的是,我们许多“过来人”逐渐在淡忘乃至掩饰历史的黑洞,而960万平方公里的“肌体”上,仍然四处可见假之花生机盎然地在“混凝土”上盛开着。尽管已经有了“信息高速公路”,有了摩天大厦和与国际“接轨”的标牌,还有种种“国际流行”的玩意儿,但我还是在某种“几十年如一日”的运转中,在喇叭、标语、新闻和宣传口号中,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员中,感受到那个幽灵的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是两亿文盲,一亿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再对应一下,则是难以准确统计的暴发户及其豪奢的生活。这是一个旋转舞台,所有的人都被历史赋予了某种角色。喜怒哀乐注定了高下雅俗。救世主从来就不存在,但社会要维持广泛的平衡和和谐绝对少不了真话、真实。惟有真话可以确认真实,惟有真实可以确认民主,惟有民主可以促成进步。这应当是现代人最起码的常识。但愿这个常识比汉字的学习更容易一点。那样,真话方不致成为“珍稀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