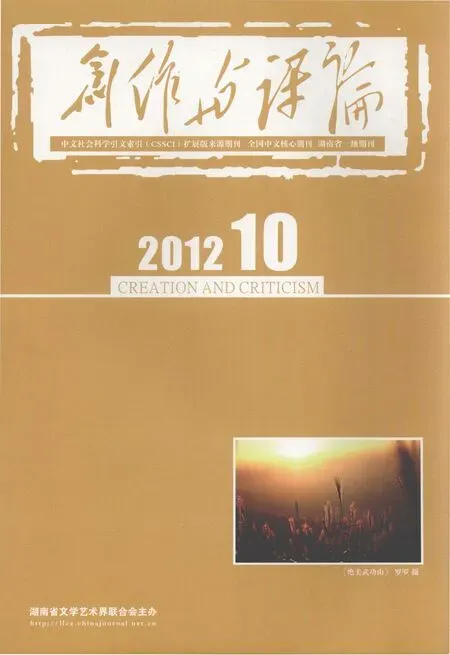蛮 荒(短篇小说)
■ 郑小驴
爷爷罗能国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和他儿子关系最为紧张的一年。中间自然少不了儿媳谭桂英的挑拨离间。事实上,即使这位大屁股女人不去添油加醋,这对父子间也早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爷爷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已经极少出去走动,他活动的半径一天一天地缩短着。漫长的一天,他坐在橘树下的老藤椅上,用一杆老烟枪拨弄着脚下的小黄猫,弄得它蹑足弓腰喵喵地叫;或者对着并不存在的远方——那面苍老的土墙产生诸多的遐想,有天他宣称墙上有影子在动,吓得不轻的谭桂英好几天对他都耿耿于怀。直到有一天,家里那只红冠大公鸡跳起来,往他脑门狠狠地啄了一口,它大概认为他老坐在那儿挡住了它的威风——罗能国一个激灵跳了起来,手中的老烟枪直追公鸡而去,我听见一声哎呦声,便看到扭伤了腰跌倒在地的爷爷。他气得直发抖,生平第一次遭到一只公鸡欺负,发誓要宰了它熬汤。他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也没能喝到鸡汤,鸡毛都没见到一片,那只公鸡得到谭桂英的庇护,毫发无损,在窗外发出响亮的叫声,像在向罗能国示威。那会儿,在床上动弹不得的罗能国只能无力地拍打着床板,“死了好,人老了不如早死的好!”
他似乎想通过追忆来挽回他逐渐老去的年华。“我年轻的时候,挑个两百多斤的担子卵事都没有,从石门到青花滩,肩都不用换。”
这种口气是意犹未尽的,变幻莫测的,如他脸上纵横密布的皱纹,猜不出哪天就会多一条。“现在连公鸡都欺负我了。”他长吁短叹一番,将老烟枪往门槛上磕一磕,从腰间掏出一个漆黑的烟丝盒,窸窣地捏一小把,填塞进铜烟筒嘴里,再摸出一盒洪江牌火柴,颤巍巍地划燃,吧嗒吧嗒地大口的呛人的烟雾开始从那张干瘪的嘴巴冒将出来。那杆老烟枪比我个头还要高,老竹鞭黄得发黑,磨得油光水滑,比大拇指还粗,可以当拐杖了。每次见到那只大公鸡,他便会高举着烟枪去打它。迟来的报复直到冬天才到来,它终于变成了一锅肉汤,伴奏着哀乐,成了守灵者的晚餐。
这位光头道士有着长达近三十年之久的鳏夫时光。不管在青花滩还是石门,都流传着罗能国的那些风流往事。这些各种版本的传说给罗能国戴上了一顶风流道士的帽子。这位口齿伶俐的道士,年轻时没少做出过风流快活的事来。自然,谭桂英也是知晓的,在罗能国中风不起的最后时光里,这位儿媳没少带着嘲笑和奚落的口气,给嘴角流着口水的罗能国更换恶臭冲天的衣裤时说:“怎么就没有那些老相好过来伺候呢?”
我五岁的那年,当时我们依旧居住在石门。一个炎热的天气里,罗能国牵着我的手说,我带你去青花滩玩吧!我兴高采烈地答应了。黄褐色的乡村小径两旁盛开着各种小野花,野薄荷的清香也夹杂在上午热烈的空气中,那种植物泡茶喝特别解暑,清冽甘甜。远处水塘里的鸭子拍打着翅膀,嘎嘎地欢叫着,水波荡漾着,漂浮的几片羽毛渐渐散开。尽管太阳炙热,我依然一路蹦蹦跳跳,扛着他的那杆大烟枪,拒绝了他的黑布伞的遮挡,一路冲在前头。
似乎还要坐船,摆渡过后,船就到了青花滩的码头。可惜后来我对青花滩的记忆完全一片模糊,就好像我从未踏足过这片土地一样。上了码头,罗能国就好像到了自己家一样熟悉,到处都有他认识的人,他不停地和人打着招呼,我记得他们都叫罗师傅。很多人问他这么长时间不见,来青花滩有何贵干,我的爷爷此行的目的一直显得高深莫测。所以对于那些问他来干什么的,他一直含糊着应答,支吾着便过去了。
整个下午,罗能国带着我转悠了很多户人家。除了喝茶就是胡扯乱谈,不着边际,他们的谈话让我感到寡味。这样持续了几家,他终于带我走入了寡妇的家里。寡妇的家是独户,四周都没邻居。穿着白色褂子的女人故意板着脸说,“还记得来啊,我以为你早死了呢!”她低头抚摸我的头,捏了捏我的脸蛋,然后从竹篮子里抓了一把花生给我并夸我乖巧、懂事。于是我坐在地上开始剥花生,我看到罗能国在这位比谭桂英年龄还要大的老女人身上捏了一把,她发出母鸡一样格格的笑声,拍落了他的手。
“乖乖,你就待在这耍,别走远了。”他们进了另外一扇门叮嘱我道。门砰的一声关闭了。我坐在地上专心致志地剥花生吃,煮熟的花生香甜可口,吃完一把,我就站起来往竹篮里再去抓一把。地面上落满了花生壳,有一只脏兮兮的小狗摇着小尾巴来乞怜,我于是扔给它一粒花生米,它当宝贝似的扑过去,朝我放出乞怜的光芒,那条没有尊严的小尾巴一摆一摆地摇动着。
我终于吃腻了花生米。太阳渐渐往西偏斜而去,一寸寸地逼近了堂屋。小狗也不知跑到哪去了,那扇门紧闭着,里面有罗能国与那个老女人,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我坚信他们已经消失了,将我遗弃在这座陌生的房子里。我拍拍屁股站起来,走到那扇漆黑的满是缝隙的门前,用力拍打着。薄薄的门很快对我做出响应,里面传来慌乱的声响,透过筷子宽的缝隙,我惊讶地看到那堆赤黄色的肉身……那女人的皮肤已经松弛不堪,肚皮上堆着一圈圈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赘肉。他们惊愕地发现了门后的我。罗能国最先反应过来,“出去!”他呵斥道。
不一会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他们重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和蔼地摸着我的小脑袋笑了笑问,“这里好玩吗?”老女人近乎谄媚地不停夸赞我的乖巧与懂事。我看到黄昏的大门口,数不清的灰尘在夕照的光柱中跳跃飞舞,那就是我们必须得呼吸的空气吗?我突然对这些看不清的尘埃产生出深深的恐慌。她不知怎样才能讨好我,于是抓了一大把花生,但被我摇头拒绝了。那个寡妇难为情地笑着,脸上满是难看的皱纹。她很想找点零食来哄住我,但她寻遍了家里也没能找出一丁点糖果之类的东西。最后眼前一亮,她从箩筐里挑出来一个红皮马铃薯:
“你瞧,那么大的马铃薯,而且是红皮的哦!”
似乎那只马铃薯弥足珍贵,它被塞进我的手心,让我感到烫手。在回石门的路上,我一直紧握着它,而事实上,我不知道这只马铃薯能给我带来什么愉悦,除了丑陋和生涩的味道,毫无美感可言。即将到家的时候,我扔掉了那只红色马铃薯。但是我也很快就把罗能国光着身子在寡妇床上的事情忘掉了。
我只知道他每隔一段,会悄悄去一趟青花滩,直到再也走不动为止。
那年石门的秋天闹了虫灾,稻飞虱在稻子即将金黄饱满之际,铺天盖地落满了稻田,无数只细得看不清的小飞虱们报复性地孵化着,扑虱灵已经不再产生效果。秋天的收成锐减至三成,有些人家甚至颗粒无收。坐在藤椅上腾云驾雾的罗能国眯着小眼睛,预言人类又将回到1960年。那个蛮荒之年,石门大半的人口像收割稻子似的收走了。从饥荒之年挣扎着活过来的罗能国晚年依旧未能消除蛮荒之年带来的恐惧,他费力挪了挪屁股,痛苦地睁开眼说,“文文,不要再浪费一粒粮食了,不然会活活饿死的。”
“浪费一粒也会饿死吗?”我故意反问道,跑出去和小伙伴们玩跳房子去了。
孤独的石门,他坐在那张早已该退休的破藤椅上,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只有这杆老烟枪是他最忠实可靠的朋友。在公鸡也不足为信的时候,他坚决不再允许我碰他的烟枪,摸一下也不可以。我曾趁他睡着的时候,学着他的样子装模作样地抽过一回,差点醉晕过去。当我摇摇晃晃将烟枪归还原处时,鼾声戛然而止,他睁开小眼睛,严厉地逼视了我一眼,“小兔崽子!你竟敢偷用我的家伙!”他将烟枪紧紧地抱在怀里,从此睡觉也不松手。
他曾说,解放前有人曾出三块光洋,他也没卖。那是他的防身武器,救命的东西。这人烟瘾大得很,至死也没有戒掉。一天不抽就像掉了魂。他伸过手,摸了摸我的眼皮,夸我睫毛长,长得好看,目光突然慈祥起来。“你不要出去乱耍,听爷爷给你讲白话。从前……”我直直地望着那双浑浊的眼球,慈祥的部分逐渐被哀求与怜悯所取代。他想方设法抓住我,在我围着院子奔跑、滚铁环、捉迷藏的时候,那双枯干的大手伸了过来,“文文,别乱耍了,来,听爷爷给你讲白话……”
他千方百计地哄我过去陪他说话聊天。说的却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讲1960年的大饥荒,啃树皮草根,吃棕树上的果粒皮——那种可做弹丸的坚硬的黑色果粒,实心,他们吃外表那层薄薄的皮。三四月份,野草莓漫山遍野都是,有人吃多了得痢疾死去。多么蛮荒的景象。
我宁肯一个人跑到河边,也不愿意待在这个被孤独折磨得发疯的老人面前,分享他恐怖的回忆——哪怕一分钟也不。他一脸不安地盯着我,你要走吗?你要去哪里?每次当我即将离开的时候,他就急迫地朝我说道。
我说我要出去耍耍。
“你去耍,我就要死了!”
那是第一次他用死亡来威胁我,浑浊的目光背后隐含着莫大的悲凉,我被这种目光镇住了。
……如果我走开,他就会死去。于是我只好乖乖地待在他身边,他让我跪坐在他的藤椅旁,用那双满是皱纹的手抚摸着我的脑袋。我的脑袋像个西瓜一样被他摸来摸去,他有些得意地朝我说道:
“小奴隶!你是我的小奴隶!”说完豁嘴笑了起来。
我别扭地听着这种称呼,我怎么能容忍别人当我是奴隶般任凭使唤呢,我不再搭理他,决心用时间去疏远他。好几天,他叫我都不应,离得他远远的。即便是我的爷爷,他也不能这样。我的赌气很快收到了效果,这个老头子可怜巴巴地望着我,目光一直跟着我转,堂屋、庭院、杨梅树上,我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他在那边开始喊我,“文文,别乱耍了,过来听爷爷给你讲个白话。”
“不!”我翘着小嘴回应道。
“过来。”
“不过来!”
他一脸的落寞,抱着那只旱烟管,吧嗒吧嗒几口之后,竟然抽噎了。
我胆怯地走了过去,叫了他一声。他低着头,不看我。我再唤他,他终于抬头了,嘶哑着说:
“小兔崽子。”
他生前唯一的老朋友,叫陈大晨。大家都说,他是罗能国结交最深的朋友。他比罗能国要小三四岁,常年穿一件黑色的中山装,连夏天也不曾见脱下来过。灰白的头发和胡须,一口牙快掉光了,说话有些漏风。他也有杆旱烟管,可没罗能国的长。他常提着来看看老伙计,和他下盘棋,或者扯乱谈。
这两位出了名的鳏夫臭味相投了几十年,相互之间还拜了把子。晚年的罗能国最为快活的事情,便是盼这位浑身臭烘烘的老伙计来看望他。陈大晨是位个子高挑和单薄的人,中山装套在他消瘦的身躯上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比方联想到他平日里的小偷小摸行为。他常选择靠柴灶的厨房长凳落座,等母鸡在放柴禾的地方下完蛋,神不知鬼不觉地顺走。他的这些小把戏终于有一天被我的继母谭桂英识破,在陈大晨走后,她开始破口大骂:
“老不要脸的,刚下的两只蛋又给顺走了!”
罗能国涨红着脸,无法还老伙计的清白之身。事实上,我也亲眼见过一回,那时母鸡刚下完蛋,咯咯咯地唱着歌出来了,我看到那只乌黑的手悄悄地伸了过去,温热的鸡蛋飞快地塞进了他的裤兜。他若无其事般继续和罗能国东南西北地闲谈着。
“等你死了,这杆烟枪给我吧。”
“那就不晓得阎王爷和咱俩谁关系好了,说不定你还比我早走一步呢!”每次谈到大烟枪时,他们都会相互嘲谑,然后哈哈大笑不止。陈大晨是罗能国唯一允许使用他的大烟枪的人。一锅烟抽完,他将烟锅细细地敲打着凳子脚,一副迷醉的表情说,“老罗,你早点死吧,留着它给我多用几年啊。”罗能国一连串呸呸呸地回应着。
腊月里,他坐在那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保持着固定的坐姿,一天也难得挪动一次。他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常叫我唤来,指了指窗户说,“那儿有条缝隙呢,老灌冷风进来,你看到了没?”
我用手指在他说的地方试了试,一点冷风也没有。他不信,第二天又继续埋怨,“冷风进来了,冷死了。”
天气再冷点的时候,他索性不再起床。有一次竟然将一泡尿屙在床上,臊气冲天,谭桂英勃然大怒地诅咒他早点死去。他的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这样的小把戏当然没能得到谭桂英的原谅。她逢人便对人说,罗能国已经老糊涂了,不认得人了。
他让我帮他装烟,点燃后,再将铜管烟嘴凑到他面前,吸了几口,人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元气,他望着我说,“文文,我可能快要死了,昨天我给自己占了一卦,可能熬不过今年冬天了。”透过那一团团烟雾,我感到有些不自在,心里便有些难过起来。
“我的好孙儿,你以后想做什么呢?”
我沉静了很久,告诉他我还不知道。他抿着铜烟嘴说,“我死了,会保佑你考上大学的。”他说得很沉缓,似乎考上大学的事,只要他肯保佑,那就是一定能实现的。顿时,我的内心洋溢着一股力量。我想那么长大以后的梦想便是考上大学了。
北风呼啸的上午,陈大晨过来了。两人坐在火塘边零星地说着闲话。那是一个阴霾天,非常寒冷,火塘不断有噼里啪啦的火星一跃而起,往房梁而去。
他破天荒地让陈大晨先用大烟枪。陈大晨还不适应这种盛情的礼让,咧嘴一笑说,“老罗,你这是……真舍得把烟枪给我吗?”
“身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说有啥舍不得的?”
他甚至吩咐谭桂英去给老伙计下一碗荷包蛋汤。陈大晨颤巍巍地立起来连连摆手说不要。谭桂英意味深长地望了他一眼,肥大的屁股一扭一扭地进了厨房。那碗蛋汤喝得陈大晨感慨万分,就差没流泪了。
临走时,下起了小雪,天色渐渐暗淡了下来,应该到午后时光了。陈大晨走到门口时,罗能国把大烟枪递到了他手上。他疑惑地望了老伙计一眼,坚决地摇摇头说,“这个我现在还不能要!”
“那要等什么时候要!”罗能国仿佛生气了。
“不能要的……不能……”两个人于是来回推拉着。
他缩了缩脖子,耷拉着脑袋,一步一步地消失于茫茫的小雪中,最后化作一个黑点。罗能国怅然地望着那个远去的黑点,无限感概地说,“一天天地看他老去了。”
三天后的下午,坐在火塘旁打盹的罗能国突然身子一歪,一头栽倒在地上。
那年冬天的河面结了很厚的冰层,有胆大的孩子竟然能在冰面上行走。寒风夹杂着雨雪,天气格外寒冷,罗能国卧床不起的几天里,这样的坏天气一直陪伴着他。直觉告诉我,罗能国可能快要死了。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一直心照不宣地这么认为。赤脚医生请过来,打了几针说不清名字的药剂,然后就走了。他对父亲说:
“如果这针没让他挺住,那就赶紧准备后事吧!”
当时躺在床上的罗能国大小便失禁,一股恶臭久久地在逼仄的房间里飘荡。他神志不清,昏天暗地地沉睡着。这是分外窒息的几天。雨雪没日没夜地下着,天冷得几乎让人不敢出门。
第四天的下午,陈大晨竟然来了,拄着拐杖,他的到来让我们吃了一惊。谭桂英用少有的真诚去感谢他的探望。可惜那个时候他的老伙计已经昏睡,闭着眼睛,不能言语。
他坐在床沿上,大声地喊了声,“老伙计,过来看你来啦!”
罗能国的嘴唇嗫嚅了一下,仿佛听见了。好一会儿,那双小眼睛打开了一条小缝隙,很激动地望着老伙计,嘴唇一直颤抖着,大家凑向前,听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听清。只见他的眼光一个劲地往床边努,那儿摆着大烟枪。
陈大晨拿走烟枪后,罗能国再也没有睁开过眼,他陷入了深度的昏迷。
第二天是个久违的晴天,寒冷的冬阳使得残雪开始渐渐融化掉。早餐的时候,一股神秘的力量驱使我跑去西厢房,我预感到床上的人可能已经不行了。
我很快跑了回来,对他们说:
“爷爷可能已经死了。”
他们纷纷放下碗筷,一阵慌乱,一起挤进那间空气混浊恶臭冲天的房间,果然如我说的,罗能国不知道在哪个时段里,悄悄地离去了。
“听说人临死的时候都会有个把时辰的回光返照时间的,可惜没有看到。”我听见有个堂叔这样说。
所有人都很沮丧,阴沉着脸,什么话也没有说。无疑,在罗能国回光返照的时光里,我们没有一个人陪伴在他身边。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无从得知,他们的沮丧是不是来源于此。
那个寒冷的冬天,我趿拉着罗能国那双过于宽大的棉布鞋,冰凉的小脚像伸进了一只大船。奔丧的人群闹哄哄的,乱成了一片。我的目光从那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身上穿过,没有发现陈大晨的影子。隆冬大地白茫茫的一片,了无生气,寒鸦立在结了冰的松树上,一声比一声凄厉,一点春天的影子都看不到。
一天后,寒风中传来了陈大晨去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