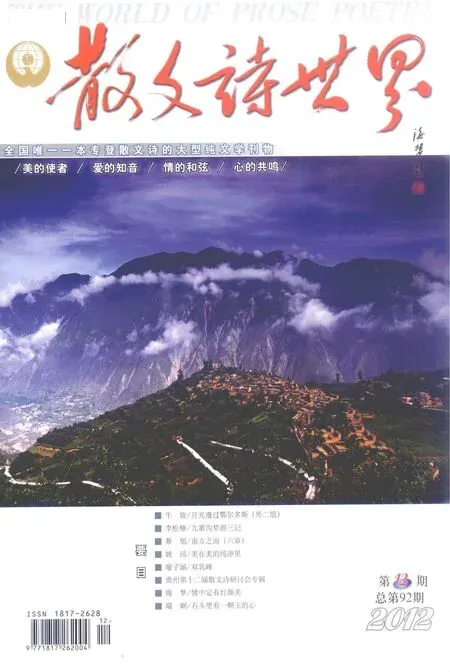江界河大桥(外二章)
杨昌瑞
我想驾一片云,攀登于江界河的悬崖绝壁,找寻那位在云彩上修路的人。
思想的跟踪器一直闪着信号灯。从桥墩到桥面;从桥头到桥尾;从河底到鱼鳞,在崇山峻岭里,在万丈沟壑中,在滔滔乌江上,他的脚印重叠了又重叠。
就在一片树叶拽着生命的句号谢幕时,修路人已去,衣衫飘然,如仙。他的风骨镌刻在叶脉之上。在火花四溅的石头上,在汗水挥洒的露尖,在刀耕火种的岁月里他的影子凝成雄健的江界河大桥。
我和风携手,站在13.4米宽度的桥面,如一个舞者登上梦寐的舞台。柔美的风最终决定以身相许,于是桥站成男人的姿势,风躺在他铜色胸肌的怀里,膨胀对未来的希望。
桥的根深深扎在坚硬的石头上,等待着历史的扉页一页页翻阅,就像雄健的男人张开双臂等待爱流入怀。
山在我的脚下行走,一山一山描着阳光的色彩,眼睛走过的地方,画幅都贴着货真价实的标签。263米的高度被阳光镀成金黄的肌体,在云彩间,桥若隐若现。
461米的长度,不仅仅穿越他体下的河。咆哮的浪花在硬邦邦的石头上磨成锋利的宝剑,同样挡不住他前行的脚步。他举着天下第一悬臂大跨度桁式组合桥的头衔,飞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把所有的惊叹都镶嵌自己的体内,在青山绿水间,一跃而起,如虹。
江界河大桥是一个大山的男人,用如钩的手紧紧抓住隔河相望的两座大山。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在严寒酷暑里他依然挺直胸膛坚守,只为人们能从他肩上渡河。
鲜花和掌声如雷,在人的心里响彻一生。
其实他什么也不要,他只是人的脚步的延伸。
瓮安城之夜
行走在瓮水长歌之都,踩着满地星光。我在现实中体验了一次梦游。
我和这城市最亲密的相拥发生在午夜时分,就算我还有些清醒,我已经跌落在她怀里。
月光和灯光在追逐嬉戏,从渡江广场到瓮安河畔,她们扬起浓烈的油彩,泼向你,泼向我,泼向他。我的身上已经洒满了绚丽的色彩,只要我轻轻一抖,五彩缤纷会滴落一地。
站在这高楼林立间,我仿佛踩着一个繁华大都市的影子。
我是第一次被诱惑进这座城池,没有理由不把自己交给她,让她在我身上自由宣泄。她滚烫的身体,把我推向火尖之上燃烧,连同我的五脏六腑一起燃烧!燃烧!燃烧!我想,就算我融化了,也要将狂热从骨头里涌出。
霓红灯在麦克风里推杯换盏。灯光和陶瓷碰杯,清脆的声音从这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声音如叮咚跳跃的山泉,从林间穿过,从透明的鹅卵中穿过,在黔山深处,过滤成一丝琴弦。
一杯啤酒,泡沫倾泄而出,在玻璃的光中一枝艳丽的花在悄然绽放!当脸被花瓣的色彩亲吻时,举着摇晃酒杯,为你灿烂的容颜喝醉。
扶着我回宾馆的街道,一直在喧嚣和奔跑。
这个城市注定要丰满,一些欲望还不断在肌肤的下面孕育。
明天,城市一阵疼痛后,一个崭新的未来在灼热的土地上丰满隆起。
注:《瓮水长歌》是循着瓮安历史长河中的一部戏,展现的是瓮安历史。
和海梦先生握手
海梦先生是一位寻梦者,在他的名字里,梦有了宽度。
八十岁的老人,如一个孩童行走在诗行里,每一个脚印都那么真切快乐。
我仰视他,仰视他对诗的种植、培育和护理。在我的仰视里没有名利存活的土壤,我只想把肥沃的土壤放在散文诗里,让梦发芽。
大海的梦正在绽放。浪花盛开为他献礼。
他勤劳的身影耕耘在诗行里,八十页诗行,八十个掌声,八十声喝彩。
《散文诗世界》里,他为八十个春天买单,却存入了一个沉甸甸的秋天。
走进他,与他握手,与每一个动情的汉字握手。
在贵州省第十二届散文诗研讨会上,海梦先生的手圆了我的梦。
不,我不是握的他的手,我是握住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