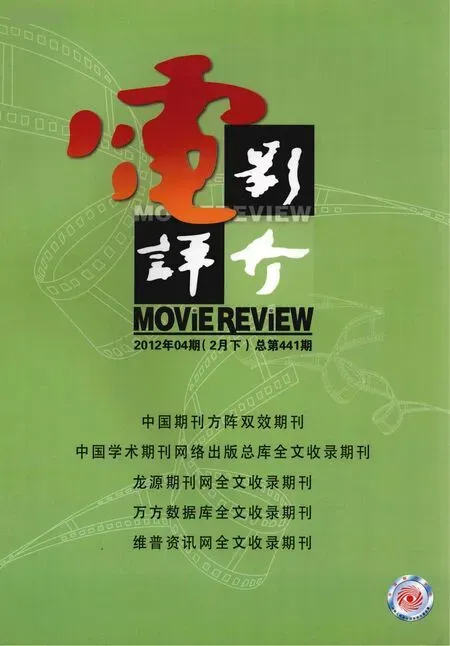影像的想象——1949-1979中国革命电影中母亲形象与民族国家想象
詹姆逊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由此我们也可以说电影这种表达机制同样负有民族国家想象的重任,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是如何与民族国家想象联系在一起的呢?而电影对于新的民主主义国家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必须获得其国民的普遍认同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动员广大的国民认同新中国的合法性就成为新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卢卡契说过:“胜利的无产阶级十分明显地面临着一个任务,即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完善迄今为止能使它在阶级斗争中,掌握自己的思想武器。当然,在这些武器中,历史唯物主义是最精良的武器。”[2]
在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就解放区文艺运动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人民的战争,它取得了人民的全力支援和他们在各方面斗争的配合。”[3]他所说这些战争是解放区乃至新中国建立的历史起点,因而对这些战争的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新生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的确认。接下来将从革命电影文本中的母亲形象入手,来论述这些革命文本是如何完成民族国家想象过程的。认同和想象是这个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而且认同是进行想象的基础。
一、认同
革命文本,更确切地说是革命母亲形象,之所以能够担负起民族国家想象的功能,首先所要做的是取得认同,而且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观众的这种认同感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对直观影像的认同来实现的。
(一)身份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观影主体。同时为适应国家对新中国电影的要求和“为工农兵服务”口号的提出都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影片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上不会超出对中国革命战斗历史的讲述和对新中国现实的赞美这两个方面。与此同时,影片的表现对象也发生了变化。革命母亲形象的变化也是其中之一,而这种形象的变化首先使人民大众产生了身份认同。
“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是‘身份’的概念。人们如何理解他们是谁?他们又是怎样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这也是一个人们怎样把自己认同于地域或者自己怎样被别人认同的问题。”[4]这里所说的“身份”更趋于抽象性的表述,而我们要分析的“身份”则是比较具体的。革命母亲形象在革命文本中都是以无产阶级的身份呈现的,而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大众的身份是一致的,这种身份上的一致性无疑会使人民大众对影片中的形象产生认同感。
(二)形象认同
革命文本进行民族国家想象的方式是多方面的,那么在取得认同的时候也不是单方面的。除了身份认同之外,形象认同也是另外一种比较直观的认同方式。
革命文本呈现给观众的革命母亲形象首先符合劳动人民的形象,与三、四十年代电影文本中的传统母亲形象从发型到衣着都有很大的区别,烫发和旗袍在革命母亲身上是看不到的,而是变成了头上挽一个发髻、身着粗布衣服,一副劳动妇女的形象。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电影文本中也有表现社会下层家庭中的母亲形象,跟革命母亲形象相似,但我们这里的比较仅限于本文所涉及到的文本。同时,新中国成立以后母亲形象的这种表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不像之前母亲形象呈现的多样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电影文本中的母亲形象已经是模式化了的。“模式化”并不是贬低这一时期对革命母亲形象的表现,这种“模式化”反而带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因为革命母亲形象的这种模式化呈现符合当时电影观众的审美诉求。也正是观众审美诉求的满足,使观众认同了电影文本中的革命母亲形象。
(三)对革命的认同
革命文本要完成对新生国家合法性的论证,首要任务就是确立使新生国家获得独立的革命的合法性。这种革命合法性在我们分析的文本中,主要是通过对革命的认同来完成的。
这种认同首先表现在对革命母亲的满足。母亲参加革命是一个双向满足的过程,母亲为革命斗争做出贡献的同时,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母亲的某种需要。影片《翠岗红旗》的结尾有一个向五儿走向革命的暗示性的画面,他们一家人站在翠岗上。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对于向五儿而言参加革命也意味着一种个人利比多的达成,那就是她对家庭团圆的向往,唯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在革命之前他们一家不得不分开,正是革命使他们的家庭获得了团圆。与此相似的表达在我们分析的文本中比比皆是:《革命家庭》中梅嫂从监狱中出来的时候也安排了家庭团聚的场景,最后表现的儿孙满堂的画面也是革命对梅嫂个人的一种满足;还有《苦菜花》结尾八路军战士对仁义嫂说:“今天你们一家算是团圆了”。另外,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能够见到毛主席应该是莫大的荣耀,这也可以说是对参加革命的一种回报。《槐树庄》的最后郭大娘要到北京参加群英会,在那里她能见到毛主席。同样梅嫂在出狱以后也要被送到延安,可以说这是对她所受磨难的最高奖赏。
另外母亲对革命的认同,还表现在将母亲身份置换成了革命者的身份。在影片《苦菜花》结尾,仁义嫂用猎枪将汉奸王柬芝打死。这是影片给了仁义嫂一个中近景,我们看到母亲手中所持的不是针线抑或锄头,而是成了代表阶级斗争的枪,由此母亲的身份被想象性地置换成了革命者的身份,这也可以说是母亲在革命语境中对自身的想象。
二、想象
得到广大人民观众的认同,只是新中国电影在完成民族国家想象的第一步,也只有在认同直观影像的基础上,才能诱发观众产生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从而完成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肩负的责任。
(一)从个体到“群体”的想象
正如安德森所说,民族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5]通过这一想象过程,个体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想象的群体之中,而这一想象的方式通过革命文本表达了出来。
《革命家庭》中大儿子江立群就义之后给母亲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妈妈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是悲痛的,但是你只要想想,这不过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妈妈和孩子的幸福。”将个人的牺牲和痛苦放置在千千万万妈妈和孩子的群体中就显得微不足道,而且非常值得。《槐树庄》中,郭大娘再一次当选合作社长的时候说:“咱们的社会主义真成了大伙自己的事……”,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对银幕前面的观众说的,促使观影个体将自己想象成大伙中的一员。《闪闪的红星》中冬子妈和冬子搬到新的地方,冬子说:“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冬子妈说:“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6]对安德森这句话最好的体现就是《闪闪的红星》中吴修竹对群众所说的一段话:“……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正是由于个体将自己想象成群体中的一员,而使这些个体不会觉得孤单,能够顽强地坚持斗争,因为他们始终感觉到自己背后有“千百个战士”。
正是通过这种个体的自我想象实现了革命的合理性,也使人民大众将自己看作革命的一分子。但同时,参与的革命必须要有领导者,这个领导者很多时候并不是在革命大众身边的,也是被想象的。而这一想象过程与宗教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二)宗教式想象
在宗教世界中,神是中心,因为“人创造宗教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对自然界的恐惧,达到对自然的认识和控制,当然,这必须通过神来实现自己的目的。”[7]通过这种以神为中心的世界,在信仰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群体间的共同意识,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群体化了的宗教情感。
在宗教中,神的确立与传播是通过一定的宗教礼仪或者仪式来获得的,宗教总是和仪式联系在一起的。仪式的意义在于,通过一定程序、规则的操演,来表明神的存在;而在这种操演过程中,神的观念被所有参与者与目击者所接受。[8]那么在革命文本中,革命的神圣化主要是通过对参与革命的过程的仪式化操演来实现的。影片《母亲》和《闪闪的红星》中母亲入党宣誓被明显地仪式化了。如果这个仪式相当于一个宗教仪式,那么入党宣言就可以看作是宗教教义。《党的女儿》中李玉梅和秀英、惠珍一起背党的十大政纲也可以看作是“教徒”通过“教义”实现了“神”的确立。
革命个体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来,将自己看作革命的一部分,并且紧跟“神”一样领导者,在这样一个想象出来的“群体”中确立自身的价值,与此同时,革命也通过人民大众的认同来确立自身的合理性。
[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见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523页
[2][匈]乔治•卢卡契.《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239页.
[3]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周扬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15页.
[4][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62页.
[5][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页
[7]马德邻、吾淳、汪晓鲁.《宗教,一种文化现象》[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页.
[8]参见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