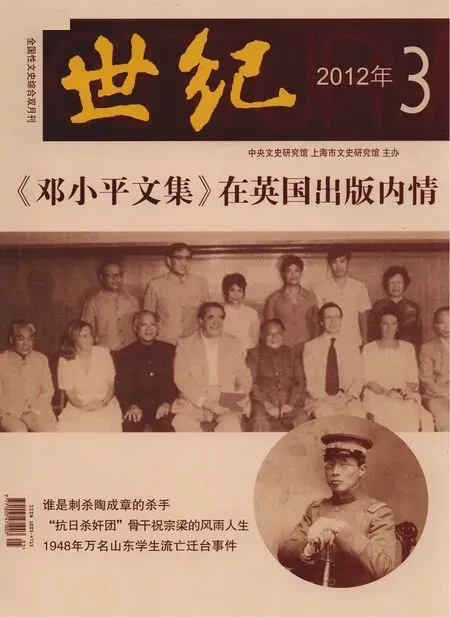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
金大陆 李逊 金光耀/采访 林升宝/整理
(采访人金大陆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光耀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采访者按:包炮,1940年出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曾参与毛泽东纪念堂、中国抗战纪念馆的雕塑创作。1966年11月,作为来沪串联的北京红卫兵,促成了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建立。有人说:中国“文革”看上海,上海“文革”看工人,工人“文革”看“工总司”,“工总司”则看王洪文。一个人的一段经历,甚或是偶然的,却在历史舞台的天幕上,刻划下了重重的一笔。
一、从抚顺到北京到上海
我家从山东历城搬到辽宁,我爷爷是个赶大车的。当时可算是开个“运输公司”,共有三辆车,日俄战争期间从长白山到奉天运人参。后来等我母亲嫁到我家里时,我家破产了,家里坐的都是讨债的。我母亲是从抚顺城边上的一个村嫁到山里去的。伪满的时候我父亲到长春去开车,当时我家有个亲戚在长春当司机,1940年我出生在长春。说到长春,这里先插一句话: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是长春的,王秀珍是长春的,我们见面就有熟悉感。1966年年底,上海工总司人员第一次到北京来,他们是第一次坐飞机,一下飞机坐车到隆福寺那里,我就领他们去喝豆汁,他们那几个就说:“怎么坏的,是泔水。”我和工总司的人就是天然的熟悉。后来我父亲到沈阳工业大学当司机,又从沈阳回到抚顺老家。我父亲这一代是见过城市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还买了什么养鸡的书、种菜的书。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在抚顺第一小学上学,从农村进入了城市生活,对学校的暖气、高楼都很新鲜。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我是乡下来的,说话、办事都觉得特别土。同学里有工人的孩子、知识分子的孩子、商人的孩子,但没有显得差别很大。在抚顺,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抚顺的新华书店。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61年秋天离开抚顺。

包炮
1961年我到北京来考大学,过程还挺戏剧的。因为家里不同意,好像也没打招呼,就给家里写了个条子,自己积攒了点钱就到北京来了。当时也不知道北京是什么天气,来了以后就感冒了,住在前门一个小客店,到王府井来考的。当时我是报的油画系,后来听说王临之教授看我素描画的挺结实,给我改成雕塑系,其实我不知道雕塑的。这样我就进了中央美术学院。
那年我们班只招了5个。一个是和毛远新一个幼儿园长大的干部子弟,后来又变成7个。实际上,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只专不红的样子,政治概念没有的,我没有想过去入团。在大学时,我记得1962年到塘沽农村去体验生活,我对这很感兴趣。1963年还到西柏坡去过,对那里的古迹现在还不忘。我那时读书家里算比较困难,每月的生活费是11.5元,这里包括吃饭、买本子。我记得一件事情,有次还到街上做了件鲁迅的那种立领的衣服。那时和平里开始建设,我们正在学解剖,就到那里去挖坟盗墓,大学的同学那时太天真了,非常的执着。那时同学之间就存在我脱了你画我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大学生活就是下乡农垦。我参加过两次“四清”政治运动,一次是到平谷,后来就到邢台。当时大学的同学、老师、教授都去了,非常投入,我父亲死的时候我都没有回去,所以说对毛泽东很忠诚的。
邢台回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我记得学校第一件大事就是高干子弟红卫兵到学校砸教具。同学就给他们一些不好的让他们砸,让他们欢呼去,同学还是保护了一些。我的老师司徒杰教授跟着我到上海。
解放后我们家身份是中农,我父亲是工人。我是这样一个出身,所以红卫兵的时候我加入的是北京一司。我到上海去带的袖章是北京一司的。当时到上海还没有一司、三司的概念区别,都算作北京来的红卫兵。我当时在美院附中带两个学生,一个叫李永存,还有一个叫武晋安,我带他们两个到上海去的。在去上海之前我还去过一次唐山,其他地方没有去串联过。我当时去上海没有想到会出什么事,要办什么事。

上海工总司袖章
二、工总司筹备会
我到上海第一天是不是住在上海音乐学院不记得了,但是在上海我最大的落脚点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在愚园路首都三司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我认识了江涛等。那里有接待站,我负责接待了几拨人,记得有叶昌明、王洪文。这里最关键就是谢鹏飞他们。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人叫曹慧琴,是她把谢鹏飞等人介绍给我的。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是在第一医学院的解剖室里面,他们那时被打成反革命了。工总司成立时第一个来控诉的就是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工人,控诉他们被关铁房子。
当时,我们在联络站每天接待很多红卫兵,他们对我们北京来的红卫兵比较信任,就来我们这里上访,我接待的最重要、最典型的代表的就是以上这几个人。他们提出要到北京去,我就说:“你们不要去北京上访了,我们就地闹革命。”接待了这么多上海的工人来访之后,我认为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准备开一个筹备会议。这我跟江涛讲过的,江涛不同意。准备开会时,不止是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人,还包括王洪文,王洪文是黄金海通知他的。
那天的会是在愚园路311号北京红卫兵接待站开的,铁路局装卸机械修配厂的工人最多。那天王洪文、潘国平他们都在。当时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过程是我先念语录,接着报出身,大家都报出身。我说:“学生运动起来了,工人运动也该起来,我们不要上访去了,我们就地闹革命,成立一个组织。”基本上就是这样展开会议的。选举的时候大家报成份,这个大主意我是拿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大学生,另外一个就是那时除了工人就是学生,即使有,那学生也是年轻的。当时“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时候要报出身。当时条件最好的就是潘国平,既是复员大兵又年轻。另外王洪文是复员军人,党员,扛过枪,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当保卫科干部,年龄比较大。所以那天的倾向性,我觉得应选王洪文当工总司的头。因为这个会是我拉起来的,我总要找一个可靠一点的。当时会上也出了点意外,岑麒麟竟然先拿出一个什么图章,大家马上就要把他抓出来。至于王洪文是东北人那是另外的概念,他说话始终是东北腔。
从工总司筹备的那天晚上到后来权利之争就没有停过。矛盾最大的就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当时没有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是在后来。但是,当时表现得最好的应该是潘国平,在筹备会上,成立大会上站出来敢说话,而且会说话,头脑清楚。安亭事件的时候我们俩来往的多,王洪文那时不表态,因为他怕事情闹大了,这点我和潘国平显得年轻,所以那五条起草都是潘国平,而且我都在场。筹备会那天选王洪文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年龄、出身、经历,没有其他的。
三、我与安亭事件
工总司开成立大会是在文化广场。那天有几个事。一个是保守派去了,会场乱糟糟,后张宝林出来控制会场。那天会场很乱,发生抢话筒的情况。王洪文基本没有动静。主持会的是潘国平。会议闹到最后的时候,曾经全体去过市委,在市委待了一会,结果没有人出来接待,那么就往火车站去了。这个决定我和王洪文,还有潘国平都是一致的。
到了火车站我们三个人都上火车了,但不是一个车厢。到了安亭之后,因为大家已经一天一夜了,没有水,没有吃的,我记得后来送去的面包都是长条形的。结果火车一停大家就气愤,所以我觉得安亭事件我要负责。火车一停里里外外都是人,而且大家在煤堆那边辩论,我一看辩论就跑过去了,朝煤堆跑的时候我就摔倒了,结果把膝盖给摔破了,缝了几针。当时我跟张春桥见面的时候,我是拄着一根拐棍,穿着棉大衣。不久,第一封电报来了,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王洪文也没有反对。王洪文拿着电报来问我,我说:“现在不能回去。”他们打了两份电报。我还咬文嚼字,分析这份电报的口气,现在想起来那时胆有点太大了。其实,我爸给我起名叫包常甲,“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同学们说我好说好动,结果大家就给我改名叫“包炮”,谁知弄假成真。我现在的身份证上就是包炮了,1966年改的。第二封电报也没有回去,不回去的态度,我和潘国平、王洪文三个人都是一样的。
江涛陪着张春桥到安亭,就把我、王洪文、潘国平找去。江涛没说什么话。第一次和张春桥是在安亭的无线电厂谈的,我们积极地和他辩论。我记得是在楼上,那时吃着包子,这我记得。主谈的我认为是潘国平,一切主事当时是潘国平。我是拿主意,这点我自己清楚。潘国平起草了五条,我肯定是明确这个态度,而且支持这五条。张春桥到安亭是半夜,谈到第二天早晨。第二天下雨了。那时我和潘国平、王洪文、张春桥在车上对话,内容就是要承认那五条,不能回去。这点潘国平是很有条理的,因为当时你要是不承认这是个革命组织、革命行动,那你要回去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当时赤卫队还在的,回去之后工厂里肯定是打成反革命了。我记得陈伯达电报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点。张春桥当时基本同意了这五条。在这点上,我同意张春桥的,叫他们先回去。王洪文在整个安亭事件里是不抛头露面的,很小心。从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到安亭事件,潘国平起着主要作用,再到签下这五条。当然,后来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王洪文。
至于拦火车的事,绝对不是我们组织的,也根本不存在组织不组织的事。文化广场签字时我在场。我不在工总司时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柴油机厂事件,整个活动我没有在场。解放日报事件我也不在,康平路事件我在。康平路事件完了以后有那么一件事,上海人给我一件军大衣。我说:“你们该给我一件军大衣。”后来一兵团、二兵团不是北上嘛,我去劝了,和张春桥一起去的苏州。那时天冷,一人给了一件军大衣。后来我在美术公司上班的时候,上海调查组来跟我要衣服。
四、炮打张春桥
“炮打张春桥”对我说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和劳元一的来往。这个在徐景贤的电话记录里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这都是公开的。炮打之后,我正式离开上海时,我已经感受到了王洪文的态度变化。安亭事件回来之后,除了与红革会的矛盾,还有我们的内部矛盾。内部矛盾,我基本是站在工总司王洪文这一边。其他的人对我都比较尊重,因为我不存在夺权的事,我在工总司没有工作证,没有头衔,始终是这样一个身份。工总司筹备那天晚上我是起了作用,以后谁干什么我就都不介入了。炮打那天对我来说,实际上我还是一个红卫兵。劳元一给我打电话,我一听那些事也特简单。就是说张春桥用军队来围困学生。当时我很激动,你不能对学生这个态度,这个不可以的。这个事影响也很大,我就把十个区、十个县的头,包括工总司的头王洪文等全拉去复旦大学看大字报。
为什么要去复旦?是因为学生冒犯了张春桥,张春桥要王洪文表态站在张春桥一边。后来劳元一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事以后,我就觉得不能只听张春桥的,还应该听一下学生的。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也是我和王洪文走不到一起的关键。后来红革会打倒之后,张春桥在上海就开始站稳了。这个时候王洪文对我的态度开始转变了。我们平常见面少了,我也不到工总司那儿去了,红革会倒了之后我也被抓起来了,是被江涛抓起来的。那是一天晚上,突然几个人把我扔到车上,弄到三司联络站一个小屋里关起来。但是关的也不严,我半夜跳窗就逃了。跑掉了以后我就去音乐学院,不久我就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后,再一次去上海,是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时。当时大家都很激动,那几天也都很高兴。我在上海只呆了几天,那时我的心情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当时给我发了一个袖章,是第1000001号,谁发的忘了,不是在主席台上发的。
我回到学校之后,也当了学校的头。关健时候我是反对两派武斗的,所以,大联合的时候,军宣队、工宣队一来,我就是大联合的主要成员。分配时我没有被分配,我当时红的发紫,后来我就直接被分配到美术公司。我分配到美术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揪斗“5.16”分子,在单位被隔离审查,监狱一天没住过。所以在1968年底,关于上海的事我就交代得一清二楚了。
第二次宣布审查是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工地上,我正在纪念堂雕塑组做雕塑,当时国内一百多个雕塑家都集中来了,专门做毛主席纪念堂的四组大型雕塑。那时候我的雕塑还没做完,单位就叫我回去,说“四人帮”抓出来了,我也该逮起来了。这次我也有思想准备了。当时我老师盛扬说:“做完雕塑再说吧。”做好以后,我就有准备,我就带着我3岁的女儿去动物园玩了一天,第二天我爱人就把我送到公司。那时是77年端午的时候。我那时是二十四小时顶着灯泡,六个人看着,三班倒。年底就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就两星期回趟家,一个月以后就一个星期回趟家。再一个月以后就天天回家。我有媳妇,就天天有人给我送饭,我那3岁闺女就站在大门口就哭啊叫啊的。其实,我和王洪文没有来往,唯一的一次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坐白牌照的部队的车到我家来过一次,那是因为我结婚了。当时还在审查反张春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