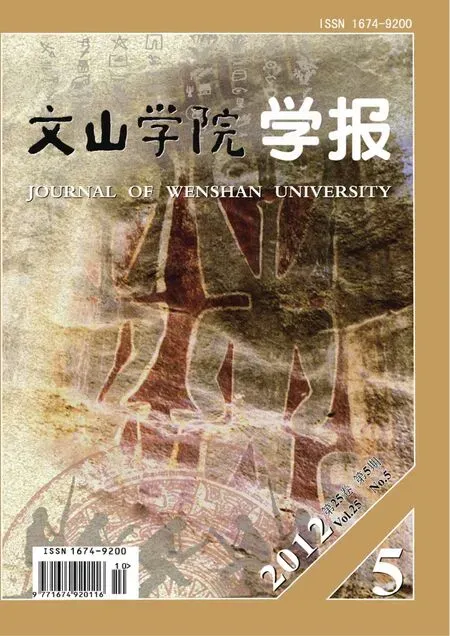论华企云的边疆研究
蒋正虎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一、华企云及其边疆论述
华企云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边疆研究出力最多、劳绩最大的学者之一,用时人的话说,是“国内对边疆问题最有研究的人”[1],其著作《中国边疆》,亦被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从整体上研究中国边疆的著述[2]。然而对于华企云的生平,目前却所知甚少。时下的边疆研究人员固未论及,时人亦语焉不详。如戴季陶称:“华君企云,向习史地,留意研究中国边疆问题者垂六七年”[3];《新亚细亚》月刊中,一署名“英”的人说:“企云同志精研史地,专心致志于边疆问题之研究者垂六七年,……所草边疆问题之稿件,自满蒙而至云贵,盖已将中国之边疆问题网罗无遗。”[4]而在《中国边疆》一书的出版预告里则说:“本书作者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有年,曾在上海大东书局发刊边疆问题专著数种,早已脍炙人口。”[5]《边事研究》杂志也仅称“华企云君,关于边疆著述,甚为丰富”[6]而已。笔者经多方查找,所得不过如此。其他比如其籍贯、生卒年份、学习经历、人际交往等,几乎一无所获。
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华企云边疆研究之生涯,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而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学界热衷边疆问题之探讨,华反而似未曾参与。30年代末至40年代有代表性的边疆研究期刊如《西南边疆》、《边政公论》、《边疆研究通讯》、《中国边疆》等,其中并无华企云的文章。华惯常发文的《边事研究》,自1938年移渝出版之后,亦再无华企云踪影。1944年《新亚细亚》复刊后,原先作为其资深撰稿人的华企云也没有出现。经笔者多方搜检,署名“华企云”最晚公开发表的文章,系刊于1941年《永安》月刊之《台湾琉球越南识小录》、《姓名与避讳》和《常言俗语辑》,均系短篇小文,且未审其作者与著《中国边疆》之华企云是否为同一人。《永安》月刊系1939年在沦陷区上海出版之刊物,如果上述《台湾琉球越南识小录》之作者确系本文所言之华企云,那么可以肯定,抗战爆发之后,华企云并未内迁。而如华企云未内迁,则其没有参与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抗战胜利之后,华企云没有出现,边疆研究界亦再没有提及,然则他很可能卒于抗战期间。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华企云之边疆研究相当活跃。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31年至1937年间,除《东方漫游记》、《马来搜奇录》、《亚洲之再生》等译著外,华企云于《新亚细亚》等期刊发表文章共计四十余篇,其中多有万言以上长文,而1938年之后,华企云竟似突然消失了。
以1931年为界,大致可将华氏之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体现在边疆论著的编辑上。自1929-1932年间,华企云所编辑之边疆论著见表1。

表1 1929-1932年间华企云所编辑之边疆论著
其中,由大东书局所出版者,以“边疆问题丛书”为名刊行,而《中国边疆》一书,大抵系将刊发于《新亚细亚》前四卷之文章组合而成。此外,在《新亚细亚》第一卷第三期《华企云同志边疆问题之著作》及氏著《中国边疆》“本书著者之其他著译”中,提到尚有《边疆游记》、《边疆探险记》和《边疆风土记》等书或在“集稿中”,或在“编辑中”,华本人也说“异日有闲,更当从事编译中西人士所著边疆游记,或风土考察记等书籍,以饷阅者”[7](P2),但笔者未见,或并未出版,或即后来在《新亚细亚》所连载之《天方历险记》等书。另外,夏威在1941年出版的《中国疆域拓展史》中,提到他参考了华企云著《西北边疆》一书,但该书笔者亦未见。
自1932年开始,华企云关于边疆之著述,均以论文形式出现,其中刊发于《新亚细亚》和《边事研究》的有28篇(连载以1篇计),另外《平等杂志》、《浙江青年》、《东方杂志》以及《申报》、《民国日报》、《新闻报》等报刊,也刊发过零星文章。此外,笔者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钱业月报》上发现亦有署名“华企云”的一批文章。虽然该刊并未对其作者做介绍,但从这些文章的内容和风格来看,当为本文所称之华企云无疑。如《日俄与满蒙》(第八卷第五号)、《论满洲之天然富源》(第八卷第十二号,1929年1月)、《满洲之盐与日本之需要》(第十卷第三号,1930年3月)等,均不失“边疆”之旨。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华企云曾对边疆做过实地调查,华本人的著述中也从未提及,王明珂说华企云在江心坡做过 “调查”①,未知其所据为何。
纵观华企云的边疆论述,前期主要为介绍性质,内容不外乎边疆各地之地理、交通、物产、经济与外交关系等,而尤重外交。如《满蒙问题》“分三编,首述满蒙之地理,次述满蒙之经济,末述满蒙之外交”[8](P1);《新疆问题》“分三编,曰从史地经济上观察新疆,曰从种族庞杂上观察新疆,曰从外交关系上观察新疆”[7](P1),其余几部著作亦如是。从内容上来看,华企云前期的著作,恐怕不能算是精深的学术研究,而更像是当时的畅销书,但是,这些著述主要的价值恐怕也就在于其通俗性。或者说,华企云前期的边疆研究,其首要的贡献并非在于其研究之具体内容,而在于其眼光之敏锐。在主流学界关注并投入边疆研究之前的差不多十年,即“已将中国之边疆问题网罗无遗”,实属难能可贵。
华企云后期的研究,内容则愈见精审,尤其是《新亚细亚》第七卷以后所载之一组论文,其学术价值恐远在华氏前期的一系列著作之上。分别是:七卷六期《中国近代边疆失地史》、八卷三期《中国近代边疆经略史》、八卷四期《中国近代边疆政教史》、八卷五期《中国近代边疆民族志》、九卷二期《中国近代边疆界务志》、九卷三期《中国近代边疆外侮志》、九卷四期《中国近代边疆沿革史》、十卷四期《中国近代边疆藩属志》。不过,华氏这里所说的“近代”,大致系指17世纪或者明末清初以来。这一组论文,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其理论内核,已经初步将“三民主义”理论与具体的边疆研究结合起来,显示了华企云在边疆研究体系性建设方面的努力。而《总理遗教中边疆建设之研究》一文,则是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边疆研究在理论方面的标志性论述。而这可以说是华企云边疆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二、华企云边疆研究之主旨
20世纪30年代,不论国民政府 “开发西北”的政策也好,还是社会上对于边疆问题的热衷也好,其核心实在于国防问题,其他诸如边疆政教问题、民族问题、开发建设问题等,均以此为鹄的。但华企云则更进一步,将边疆视为整个中华民族生存之基础。用华企云自己的话说:“中国民族便要不能生存在世界之上,我们不要求生存则已,倘使要想生存的话,那末便首先要来研究边疆和怎样巩固国防,怎样从事开发建设。”[9]华企云之边疆研究,以此为起点,亦以此为终点。以边疆为中国立国之基点,可将华氏研究之主旨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移民实边,巩固国防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上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似乎都有一种担忧。这种担忧的核心,就在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如20年代中期,冯玉祥即于西北“提倡垦务,各省争先恐后,均愿受之一尘,耕于其地”[10],并办有“中华垦殖公司”及“垦殖学社”,以达实边之效。30年代之后,人口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进一步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如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就说,“中国人口是集中在狠(很)少数的几个地方”,“百分之八十三强”的人口集中于“百分之十七弱”的土地上,认为“人口集中太密故生活低下”。[11]有杂志也称西北“为中国沿海各省过剩人口之唯一出路”[12]。而华企云对于边疆问题的关注,其主旨之一,也是因为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对于国防稳定的影响问题。在1929年的《满蒙问题》中,他说:“无论本部各省有人口过剩之患,藉曰过庶矣,亦可移植满蒙以救济之。此则吾人当竭力鼓吹本部人口移植前往者矣。”[8](P13)而在 1931 年的《新疆问题》中,他更进一步认为,要“筹边固圉”,首先即是“移民殖边”[7](P167)。在 1932 年的《岌岌可危的中国边疆》一文里,他也认为,就“开发建设和固圉”而言,“先要移植一批闲散军民前往办理兵民屯垦”[9]。而到1937年,他对于“筹边固圉”又有了新的认识。他将“将来的边防系统”作如下之归纳:“筹边”中的行殖边、举屯田、立镇守和重谍报等四项举措组成了边防系统中的交通和政治方面,而“固圉”中的筑城池、置塞徼、遣戍守和制要地等四项措施则构成了边防系统中的设防和堡垒方面。显然,在这一“系统”中,首先就是“行殖边、举屯田”。
因此,“边疆正是人口稀少而地大物博的疆土。正维这地广人稀的现象,弄得比邻的帝国主义者无时无刻不是乘机窥隙,狡焉思启”[9]。中华民族想要生存,务须求国防之稳固,而国防之稳固,首要在于移民殖边。
其二,团结各族,共谋发展
诚为华企云所见,边疆各民族所居处之土地面积,“要占到全中国二分之一强一些”,广大的边疆地区既为立国之基,则团结边疆满、回、藏、蒙、苗等“五族”,就成为必须。而民族团结之观念,亦贯穿于华企云整个边疆研究生涯。该观念之核心,则是以各民族之起源来论证民族团结之基础。
华企云的民族观念,其先依梁启超与西方学者,较为支持“多元混血论”。认为中华民族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族组成,而边疆各民族也是混血而来。如说蒙族,“它的来源是东胡、突厥、氐羌,三大族的北方混血种,但是它总不失其为中华民族中大族之一。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族构成的中国之中,它也是基本各族啊”[13]。说藏族,则认为“今日之西藏族,其源流上实为土著与外来混血民族者,当可断定无讹矣”[14]。后则折中于孙中山,认为中华各民族中,蒙族和满族与汉族实为同源之民族。他说,匈奴与蒙古同源,据《史记》所载,匈奴系夏后氏之苗裔,“然则汉蒙两族,显出同源可知,只于匈奴一支居于大漠,汉族一支居于内部,……则同族之渊源,固可自信弗疑焉。”[15]又说:“满族……实出于古帝少昊,与汉族有同源异地之关系。蒙族……亦为夏后氏之苗裔”,回族之先祖匈奴,“与汉族之关系最称密切”,藏族“与汉族亦息息相关”,苗族“则当汉族未盛以前,原为中原土著”[16]。这是从历史上论证民族团结之根据,也可以说是对“三民主义”中民族观念的发挥。在这些表述中,有的前后并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如关于蒙族与回族之先祖问题),但这恰可以说明华企云在论证民族团结方面的努力。
在具体论述中,华也处处以民族团结为念。如说到新疆回民,则说:“新疆之民众既同为中国之国民,则吾人对于新疆之利益,应当予以保障。……将来欲求国民革命之完成,则当非中国境内各民族之努力不可,新疆回民革命性素极丰富,更为实行国民革命之重要份子。”[17]说到蒙族,则认为:“汉族之与蒙族,同是中华民族,汉族应以蒙族的力量来捍卫祖国,……盖惟有在蒙汉和衷共济的合作条件之下,才可以应付当前的国难!”[17]又说:“集汉满蒙回藏苗六族之净化于一家,尤为中华民族复兴之根基,全国人士其勿忽视焉。”[18]还说:“中山先生领导之革命光复汉族后,不再主张传统之攘夷思想,而以各民族之互相提携为国是,故今日无论汉、满、蒙、回、藏、苗,均为中华民族之一份子,均应以中华民族为团结合力之标准。”[16]
其三,细叙原委,以明国耻
正如华企云所说:“自从最近一百年以来,国土逐渐逐渐的减少下来,边疆上大好土地,一步一步经邻国宰割了去。”[19]因此在他的论述里面,有关边疆沿革与土地丧失之经过,是其叙述的一个中心环节。每述一地,则征引合约或“密约”原文,务使读者明了帝国主义之侵略与我丧地之原委。如在《满蒙问题》中,他叙述中俄外交关系之演变,先叙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开疆拓土,危及英法等国的利益,导致上述国家在东欧、小亚细亚和中亚对俄国的围堵,以至于“俄国其不能不别图发展矣,若论别图发展,当以中国为最佳”[8](P83)。以俄国针对中国东北与西北两个方向的“发展”为线索,华企云先后引用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界约、恰克图市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勘分东界约记、塔城界约、科布多界约、乌里雅苏台界约、中俄改定条约、喀希尼密约、巴布罗福条约之原文,将中国丧失于俄国的土地之经过原原本本的叙述出来;而《云南问题》一书中,则叙英法窥我西南的动机:法国是垂涎于我西南之“丰饶矿产”,而英国则冀借云南而“径入长江”,“溯流而往,更可遍达川、鄂、湘、赣、苏、皖、浙等省”,以达“争通商之利”的目的[20](P3-4),是以“举凡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之历史,与夫对华所订关于云南之种种不平等条约,无不作扼要之说明”[20]。因此,华企云著述的核心之一,就是“考见晚清以来之边患,且可以兴民族国防安危之思”[21]。
对于已经被“宰割了去”的土地,华企云不时流露出一种激愤与无奈的情绪,所以对于“未定界”的云南边界,华企云尤其关注。他先后写有《云南界务问题之研究》(《新亚细亚》五卷四期,1933年4月)、《重勘滇缅南段界务的认识》(《东方杂志》三十二卷十一期,1935年6月)、《滇缅界务之实况》(《边事研究》二卷一期,1935年6月)、《滇缅北段界务的检讨》(《新亚细亚》十卷一期,1935年7月)、《滇缅南段界务之现状》(《新亚细亚》十三卷二期,1937年2月)等文章,力表寸土必争之念。在地理上要实地调查,“把滇缅南段的一丘一壑,一村一寨,都要调查个详详细细,作为将来交涉上惟一有力的证据”[22],“要找出滇缅旧界的所在”,“在历史上,要找出滇省的旧管证据,来维中国的旧有疆土”[23];在民族上,“举凡已属中国之明证,或自愿内属之部落,均需列入版图”,“已奉正朔如崇祀孔明、王骥等先贤之卡瓦民族,早已自认为与汉族一家,亦不容忽其边氓,视为化外”[24]。
总之,边疆与内地实为一个整体,边疆事关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无论在中国人口问题上,在经济问题上,或是国防问题上,都可以靠解决边疆问题来得到一个总解决,边疆问题一经解决,那末三个联带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边疆问题一日不解,那末三个联带问题也便一日不决”[9]。
三、华企云对于边疆研究的理论建设
华企云后期的边疆研究,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对于边疆研究理论方面的重视。华的这种转变,与新亚细亚学会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在新亚细亚学会历届的董事会、监事会、“评议员”中,均无华企云,且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华企云为新亚细亚学会会员,但种种迹象表明,华本人应该是新亚细亚学会的资深会员。其一,自《新亚细亚》1930年创刊,至1937年第十三卷休刊,不算译作,华于该杂志上发表文章共计二十余篇,数量之多与持续时间之长,除新亚细亚学会精神领袖戴季陶之外,少有其匹;其二,华1932年出版的《满洲与蒙古》之“小序”,系作于新亚细亚月刊社;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从他本人后期研究的方向和兴趣可以看出,华企云本人坚定支持新亚细亚学会的主张,或者说,华后期的著述,根本就是新亚细亚学会主张的具体体现。
新亚细亚学会的主张,可分理论和具体研究两个方面:在理论上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根基;在具体研究中,则“专门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与东方民族问题”[25]。而自新亚细亚学会成立后,华企云的关注重点也随之从专门关注中国边疆问题转为国内与国外并重。在其《中国边疆》中,第三章与第四章即是关注“东方民族问题”②。这也直接导致了华后期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翻译西书,在《新亚细亚》中连载(自四卷二期始)。自1932年开始,先后译有《乾竺特探险记》、《岗强岬历险记》、《马来搜奇录》、《天方历险记》、《东方漫游记》等五部,且后三者均系长篇连载,此外还有未刊发而独立成书的《亚洲之再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华企云后期的研究。从这些译著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类书籍均为探险猎奇一类,虽然可能有助于当时的国人了解所谓“东方民族”,但相对而言,其价值与中国边疆研究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对于边疆之研究,其理论实基于“三民主义”。华企云亦不例外。但华企云前期之著述,大抵以介绍边地情形为主,论及边疆研究理论与政策之处极少。如在《西藏问题》中,仅隐约提到要 “本三民主义之精神,按建国大纲之步骤,从事一切建设”[26](P159)。在《新疆问题》中,则引孙中山之原话而鲜有发挥。而且在骨子里,他也仍然将边疆少数民族当做是“异族”,比如在《西藏问题》中,他就将内地称为“我”,而称西藏为“藏番”。但新亚细亚学会成立之后,或者说华企云边疆研究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根本,就在于他在研究中有意识地运用和发挥“三民主义”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三民主义”与边疆及边疆建设之关系。华企云对于边疆建设理论之思考,集中体现于《总理遗教中边疆建设之研究》,刊于《边事研究》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7月)。在这篇文章中,华企云鉴于“自暴日先后攫我东北以来,新疆有俄国之觊觎,康藏受英国之窥伺。偌大边疆,已成朝不保夕,长此以往,因循苟且,则非惟建国方略有失却建设之效,而三民主义之理论,亦且根本动摇”,故“从遗教中研究建设中国边疆,立论一本三民主义之真谛”,认为“民族主义扶助中国民族之独立”,“民权主义扶助中国民族之发展”,“民生主义扶助中国民族之生存”[27],将“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各民族独立、生存和发展之纲领。该文以“三民主义”为体,以“建国方略”为用,以边疆为体用之结合与核心,从而将“三民主义”与“建国方略”的根本建立于边疆之上。
第二,边疆民族与中华民族之关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大率讲求将“已经失去了几百年”的民族主义“恢复”过来,而因“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五项因素,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实际上已经融合为“一个民族”,认为“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完全是一个民族”[28](P183-188)。这是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核心,也是华企云在边疆研究中就“民族主义”进行理论阐发的根本出发点。华企云说:
关于民族构成之原因,中山先生归纳为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及风俗习惯五项要素,所谓血统者,乃指一个血统或一个人种传下者而言,祖先之血统,可以累世遗传而不失,故黄色人种之子孙,永远为黄色也。所谓生活者,乃指经济状况及谋生方法之一律者而言,故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活之蒙古人,亦可称为一族。所谓语言者,乃指操同一语言之人而言,故自满洲人操汉语而后,满族即与汉族同化成汉满一体也。所谓宗教者,乃指其人之信仰同一宗教而言,故信仰喇嘛教之西藏人,亦成其为一族也。所谓风俗习惯者乃指其人保持道一风同之情习俗而言,故如异教不通婚媾之回人,亦成其为一族也。推而言之,苗族之生活习俗等又复异殊,故苗蛮亦至今成一族也。[16]
又说: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虽十九同化,然“在东北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边陲,则除汉族以外,犹有蒙回藏苗等种族”[16],只不过这些“种族”与汉族是“五位一体”。
孙中山和华企云同样以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作为判断民族的标准,不同的是,孙认定中国人“完全是一个民族”,而华企云则将之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而将中国民族划分为汉、满、蒙、回、藏和苗六个民族。这可以看做是对“民族主义”理论的补充、发挥和完善,也可以看做是将“民族主义”理论与边疆实际之结合。这种发挥、完善与结合,是华企云后期边疆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同时也是华企云在边疆研究理论上的一大突破。故此他说:“要救中国,要建设中国边疆,首要提倡民族主义”,“汉满蒙回藏,只可谓之中国民族种类之成分,又似一件有机体之各个细胞,绝非是此民族主义中所分之民族(笔者按:即“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之“民族”)”,所以中华民族实是“五位一体”,“虽则所处地域或有遐迩之分,在关系上实无畛域之殊”[16]。
华企云对于边疆研究之体系性建设,集中体现在《新亚细亚》所刊发的一组文章之中。这组文章的内容表明了两点,其一,华企云后期的边疆论述,已经超越了早期单纯的介绍性质,而进入了真正的研究阶段。边疆之气候、物产、交通等华前期论述的重点,在这一体系中已经没有位置;其二,边疆研究应该以边疆失地与外侮、边疆经略史、边疆政教民族与藩属、边疆界务与沿革为研究之重点与中心。这实际上说的是华企云所认为的边疆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总之,华企云在边疆研究上的建树,一是与同时期的一大批边疆研究团体与研究者一道,有意识地运用“三民主义”理论研究边疆问题,使边疆研究有了相对明确的理论指导;二是较为系统地发挥了“三民主义”理论,阐述了边疆与内地、边疆与国防、中华民族与边疆民族以及边疆建设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边疆研究之对象与范围,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尽管比起20世纪40年代边疆研究的主流理论“边政学”来,这一体系并不完整,在深度方面也显单薄。
注释:
①王明珂说:“我今天在川大演讲所举的一个例子,早期景颇族中有一个传说,过去华企云在江心坡‘野人’地区做调查时记录下来的。这说法是,当地土人说他们是蚩尤的子孙;但老年土人说,我野人(景颇族那时称野人)跟汉人、摆夷是三个兄弟;野人是老大,摆夷是老二,汉人是老三。因为爸爸特别偏爱老三,就把老大野人赶到山上去了。”见徐杰舜,王明珂:《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四期。按:王氏所言,概出自华企云《中国边疆》第十章“云南之界务问题”之第三节“江心坡问题”。原文为:“江心坡……各族性质风俗及生活状况大致相同。领袖者曰头目(即酋长);无文字,人多居于崇山峻岭间,闭关自守,故其历史世系,非特外人无从考查,即彼等亦不自知也。或谓彼等系蚩尤之子孙,即苗族别类,语涉理想,无从稽考。而年老土人则谓:‘我野人与摆夷汉人同种,野人大哥,摆夷二哥,汉人老三;因父亲痛惜幼子,故将大哥逐居山野,二哥摆夷种田,供给老三;且惧大哥野人为乱,乃又令二哥摆夷居于边界,防野人而保卫老三。后野人以山居甚苦,果然相率起反,打入京内;至永昌遇孔明领兵到来,受慰而返……’”云云。
②《中国边疆》第三章题为“边疆邻接各地之地理概况与最近民族运动之鸟瞰”,第四章题为“边疆邻接各地之对华历史与受制帝国主义之经过”。
[1]华企云.《现在的蒙古》编者按语[J].浙江青年,1934(2):187-203.
[2]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J].历史研究,1996(4):137-152.
[3]戴传贤.中国边疆之实况序言[J].新亚细亚,1931(5):13-14。又见戴季陶:《中国边疆·序》。按:华企云《中国边疆》一书,本拟题为《中国边疆之展望》或《中国边疆之实况》,出版时方改为《中国边疆》。
[4]华企云同志边疆问题之著作[J].新亚细亚,1930(3):129.
[5]《中国边疆之展望》出版预告[J].新亚细亚,1931(3):9.
[6]编后谈话[J].边事研究,1936(5):124.
[7]华企云.新疆问题·凡例[M].上海:大东书局,1931.
[8]华企云.满蒙问题·凡例[M].上海:大东书局,1929.
[9]华企云.岌岌可危的中国边疆[J].平等杂志,1932(11/12):1-8.
[10]松介.西北农垦调查记[J].西北汇刊,1925(1):12.
[11]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J].独立评论,1932(三号):9-11.
[12]原作者不详,颠何 译.西北为中国之生命线[J].社会科学季刊,1934(2):195.
[13]华企云.蒙古民族的检讨[J].边事研究,1935(3):1-8.
[14]华企云.西藏民族之检讨[J].边事研究,1936(5):1-8.
[15]华企云.蒙古问题之回顾与前瞻[J].边事研究,1936(2):51-58.
[16]华企云.中国近代边疆民族志[J].新亚细亚,1934(5):37-48.
[17]华企云.新疆之三大问题[J].新亚细亚,1931(4):25-35.
[18]华企云.一九三四年边疆之回顾[J].新亚细亚,1935(1):17-30.
[19]华企云.一九三三年边疆之回顾[J].新亚细亚,1934(1):47-58.
[20]华企云.云南问题·凡例[M].上海:大东书局,1931.
[21]华企云.中国边疆·自序[M].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2.
[22]华企云.重勘滇缅南段界务的认识[J].东方杂志,1935(11):15-23.
[23]华企云.滇缅北段界务的检讨[J].新亚细亚,1935(1):15-24.
[24]华企云.滇缅南段勘界之现状[J].新亚细亚,1937(2):31-36.
[25]新亚细亚学会总章[J].新亚细亚,1933(1/2):264.
[26]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
[27]华企云.总理遗教中边疆建设之研究[J].边事研究,1935(2):1-22.
[2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