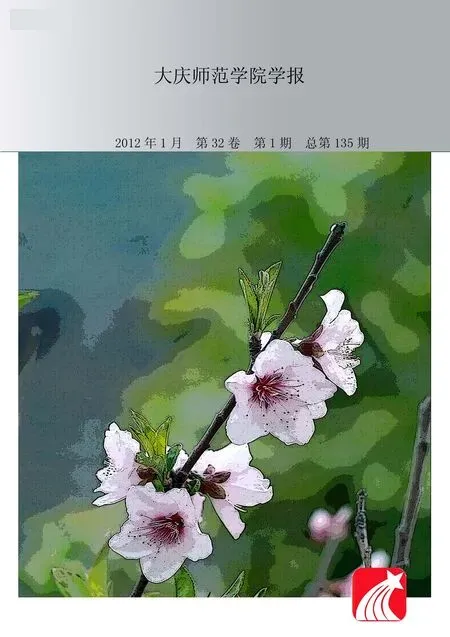杜甫《同谷七歌》的悲剧主题
王睿君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 成县 742500)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以下简称《同谷七歌》)是杜甫寓居同谷(今甘肃成县)时写下的七言组诗。原诗内容如下: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关内大饥,战乱不已,人民饱受灾难。杜甫受到房琯事件牵连被一再贬官,最后贬任华州司功参军,司功参军这一微职实则无所作为,杜甫的政治理想破灭了。为了生计,只好应当时正在秦州(今甘肃天水)郊辅西枝村自建窑洞居住的友人、原京师大云寺主僧人赞上人的相邀,又有其从侄杜佐寓居秦州的东柯谷,他举家投奔。杜甫《秦州杂诗》“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正说明他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依靠亲友流寓秦州。然而诗人在秦州的生计并没有多大改观,“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杜甫《空囊》),“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杜甫《秦州杂诗》),反映了诗人一家当时在秦州的生计状况,依靠亲友的接济和卖药的微薄收入依然无法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困境。此时有同谷县令“佳主人”来书热情相邀,有诗为证,“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妙绝,远客惊深眷”(杜甫《积草岭》),再者听说同谷气候温暖,风景宜人,喜好郊游的诗人颇为动心,更为重要的是诗人认为同谷能解决全家的生计问题,于是充满了向往之情。“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杜甫《发秦州》)即为明证。于是诗人在秦州流寓近四个月后,携家从秦州出发,历经艰难万险,最终到了同谷县。此时县令却嫌诗人已弃官且穷困潦倒便避而不见,诗人只好在距县城十里的凤凰山下、飞龙峡口结茅庐居住了一月左右。然而在寓居同谷的这一个月里却是诗人一生最为凄惨的日子,应“佳主人”热情相邀来到同谷却遭受了冷遇,身居穷山僻壤,人生地疏,全家人饥寒交迫,身陷不幸的诗人于无奈中“长歌当哭”,和着血泪用七古体裁写成了七言组诗《同谷七歌》。
这组诗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诗人一家寓居同谷时艰苦卓绝的生活,真是到了惨绝人寰的境地,其“长歌可以当哭”,冯至认为这组诗是“响彻云霄的悲歌”(冯至《杜甫传》),七歌中唱出了痛彻心肺的悲剧主题。
一、生活凄惨的悲歌
杜甫一生其实并未一直处于生活贫困的境遇,他出生于有着“奉儒守官”的传统家庭,他从小就继承了这一传统,立志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三十五岁以前,诗人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读书、壮游、打猎、饮酒、赋诗,过着他一生最为快意的生活,在他早年的诗歌里很少有嗟穷伤贫的内容。诗人虽然“学而优”,但他后来入仕的道路却颇为艰难。当时入仕的途径有三种:参加科举考试、让达官贵人保荐、向最高统治者献赋。这三种途径诗人都尴尬地尝试过,先后得了左拾遗、参军等几个卑微的官职,却又因为疏救房琯罪逆龙颜遭贬,政治理想破灭后的诗人最终弃官,仕途的坎坷,多少也导致了生活的贫困。诗人于天宝十载(751年)《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一诗中就开始有了明确的记载:“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这还不是诗人最贫困的时候,试看《同谷七歌》中的凄惨处境。
杜甫四十八岁时携家来到同谷,正值天寒地冻之时,一家的生计是此时全家人关*的焦点,诗人在《发秦州》一诗中向往的野蜜、薯蓣在严寒的季节何处可寻?此时诗人自我形象是这样的:“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短衣数挽不掩胫”,穷老困病的诗人饱受了作客的凄楚,潦倒的困境,可以说诗人已到了衣不蔽体的地步。按说同谷界内,杜甫结茅庐处的前面正是青泥河,此河*入嘉陵江,同谷尚属长江流域,冬天虽然严寒却谈不上奇冷,若非诗人缺少衣物,衣衫短小不蔽严寒,也不可能到“手脚冻皴皮肉死”的地步。可是在人地两生的同谷无人接济,诗人为生计役使,不得不困守穷谷,忍受肃杀的寒意和暮色,“岁拾橡栗随狙公”[*]橡栗,是一种野生植物,含有淀粉,果实味涩不可食,当地人称之为“橡子”。若非生活极端贫困,当地百姓决不会以橡子作食物。。橡栗成熟于秋季,即使当地橡子树多,诗人在“汉源十月交”由秦州来到同谷,零落在地上的橡栗已经很少了,就算“随狙公”顶着寒意去找寻,也是难能果腹的。所以诗人只能感叹“悲风为我从天来”之余,亲自手握“长鑱”进到盛雪覆盖的深山去采掘黄独(黄独是一种野生的土芋,也正是诗人在《发秦州》中提到的“薯蓣”)。但是山中大雪覆盖,根本无苗可寻,只好荷鑱而归。寻不到食物已经令诗人很悲痛,归来只见“男呻女吟四壁静”,更加让人觉得惨不忍睹,就连“闾里”也为这一惨相而“色惆怅”,这一个“静”字和“闾里”表情的衬托,可不更加体现了诗人生活贫困的悲剧吗?
曾有人说,杜甫到同谷时,“只有四十八岁,即使早衰,也还不至于就白发垂耳吧”?杜甫“把自己的贫困夸大得太不着边际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试想四十八岁在当时已算得中老年人,相貌容颜发生变化是自然的道理。伍子胥为过昭关一夜可急白头发。诗人常年为贫困所累,再体面的人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也懒理容妆。杜甫此时在人生最为困苦的时期容颜发生些变化,以至于“白头乱发垂过耳”而疏于打理,也应在情理之中。何况杜甫的诗历来被称为“诗史”,诗中记载的情形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二、亲情难舍的悲歌
数千年中国文化底蕴中积淀着一种浓浓的乡土情结,思念家乡,感念亲人的情怀人皆有之,这种极为普遍的思乡情怀也是文学作品中经常抒写的主题。杜甫的感情世界也十分丰富,面对苦难,杜甫毫不掩饰,也不颓废,他把对故土的思念,对亲友的关爱款款写出,从而抒发真情,表达对亲人、对朋友、对故乡、对人生的挚爱与热情。
杜甫有弟四人,颖、观、丰、占,此时只有占跟着杜甫寓居同谷,另有一妹在濠州钟离。[1]兄弟姊妹天各一方,远离故土的杜甫思念远方的亲人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当时大唐王朝的国土上烽烟四起,道路阻隔,以致亲人音讯渺茫,思念之情虽深,团圆之望全无,杜甫只能凭借诗歌诉说衷肠。

梁启超曾称杜甫为“情圣”,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在唐代诗人中,像杜甫那样重亲情并毫不掩饰地在诗歌中表现这一感情的并不多见。[2]他在诗歌中往往会表达对同性朋友的深情厚谊,比如因李白、高适、岑参而作的一些诗篇。杜甫在一些诗篇中也毫不掩饰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对弟妹子女的深切思念,这诸多诗篇展现了诗人健全的感情世界,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同谷七歌》中对弟妹的思念忧虑之情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三、忧国忧民的悲歌
杜甫有着崇高的人生理想,一是“致君尧舜上”,即以臣的身份辅佐国君,使最高统治者成为治国有道的明君;二是“再使风俗淳”,即以儒者身份去完成道德教化的使命,使社会风气变得淳朴美好。可是他一生的理想随着仕途的失败化为泡影,不得已过起了漂泊的生活。
杜甫作为伟大的“诗圣”,除了感叹个人的悲苦外,无论在怎样艰难的境况下,他始终难以割舍忧国忧民的情怀,密切关*着政治时局的变化。“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就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一句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是对同谷县万丈潭的描绘,因为诗人对此景点另有一诗《万丈潭》。然而《同谷七歌》抒写了诗人的身世之感,在组诗中诗人应该不会单单穿插一首状物写景的诗歌,因此,这几句应该联系当时动荡的政治时局有感而发。蒲起龙认为,“七歌总是身世之感,何容无慨世一诗。值乱乃作客之由也。不敢斥言五位,故借南湫之龙为比。……‘枝樛’、‘龙蛰’,干戈森扰也。‘蝮蛇东来’,史孽寇逼也”(浦起龙《读杜心解》)[3]。因为这年九月,史思明攻陷洛阳,横行于河南一带,诗人以“龙蛰”暗射唐王朝君主昏庸,国势衰微,平叛无力。以“蝮蛇”象征叛乱的贼寇。龙潜蛰而蛇反游的现象令杜甫极为痛心。因此,诗人想起国难民困,即使远离战火,身在“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的“穷谷”,仍时刻渴望能够消除战乱,迫切希望“溪壑为我回春姿”。
按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已经脱离了官场,在政治失意之后,在躲避战乱之时,他已融入人民之中。杜甫终身不弃自己崇高的理想,也未效仿陶渊明避世隐居,诗人早年“奉儒守官”的思想影响了他一生。所以诗人常常忧思满怀,义愤填膺,在国难当头之际,却无法报效朝廷,为民除害,使国安昌。只有在悲愤之余发发牢骚,以“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的诗句讥讽李辅国这类新宠权贵们排斥忠良,专权误国的愤懑之情。忠良贤才空有一腔政治抱负,却壮志难酬,无奈之中“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作为一个入世主义者,而今年老无成,“仰视皇天白日速”,迟暮之感顿生,只能在忧国忧民的悲歌中抒发感慨了。
《同谷七歌》抒发了杜甫伤身世之苦,悲离别之痛,感忧患之情,字字充满了血泪,这迷惘、悲凉、忧伤,真乃是千古绝唱,每一歌都隐含着诗人深刻、浓重的人生悲剧。
[参考文献]
[1] 萧涤非.杜甫诗选*[M].1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 丁启阵.论杜甫诗的悲剧主题[J].杜甫研究学刊,1998(1).
[3] 陈子建.杜甫《同谷七歌》的抒情特色[J].杜甫研究学刊,2001(4).
——以清代与民国“秦州志”编纂为例
——评《产品包装设计( 第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