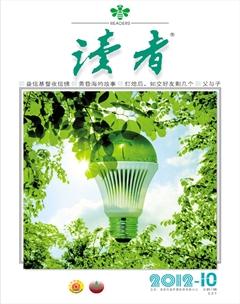家属
邓一光

在西藏听了几个关于家属的故事。
一个故事是有关边防某团政治处主任黄白华的妻子的。边防某团驻守在察禺,那是麦克马洪线的一段,自然条件十分艰苦,交通极为不便。一条破旧的道路在极其危险的山间蜿蜒穿行,冬天大雪封山,天气转暖后又老是下雨,路其实是三天两头不能畅通的。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常有塌方、滑坡和泥石流一类的险情发生。
但那是通往察禺唯一的路,不管你是进察禺,还是从察禺出来,如果你不是鸟儿,就只能从那条路上通过。
团政治处主任黄白华驻守边境,已经好几年没有探过亲了。于是黄白华的妻子就请了探亲假,收拾好东西上路了。
在成都要买到飞往昌都的机票很难,一般情况下得等上一个多星期。如果遇到暑期探亲季节,十天半个月滞留在成都是常有的事。当然也可以走陆路,由路况险恶的川藏线进藏,那样的话,由成都到昌都,也得一个星期。
黄白华的妻子历经千辛万苦到了昌都,然后等去察禺的车。好不容易上了去察禺的车,车颠颠簸簸地往察禺走,走一段,停一下,走一段,停一下。黄白华的妻子抱着带给黄白华的家乡特产,被颠簸的车子不断地抛起来,又摔下去,五脏六腑都差点儿没被颠出来。那一刻她想流泪,不是为自己,是为丈夫和丈夫的同伴,他们真是太难了。
车子终于彻底停下来了。察禺还没到,是遇到了一场大风雪,路被封住了。
司机无可奈何地对黄白华的妻子说:“嫂子,不是我不送你们,路再险,道再难,四个车轮子我管着,但管不住老天,我没法把车开上雪山。咱们还是回昌都吧,你和我大哥在电话里商量商量,明年再约个好时候进来。”
黄白华的妻子把额头上的乱发理了理,拉开车窗,看了看眼前的雪山。雪山美极了。
她转过头来问:“翻过这座雪山要多长时间?”
司机回答:“八公里山路,要是壮小伙,睡足了觉,带上酒和肉干,不遇到雪崩什么的,顺利的话,五六个小时吧。”
黄白华的妻子说:“谢谢你了,兄弟,你请回吧,我就在这儿下车,我自己往前走。”
司机大惊道:“那怎么行?你还要不要命了!”
她微微地笑了笑,平静地说:“怎么不要命,我是来看他的,不要命我怎么进去看他呢。”
司机怎么拦也拦不住,一旁有个探亲返队的战士见状说:“嫂子,我本来打算等等,等路好走了再说。你一定要进去,我陪你。”
他们开始走了,往雪山那一头的察禺走。
她背着带给丈夫的东西,战士背着自己的行李,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他们走了足足十个小时,也许时间更长,谁知道呢?反正他们用光了所有的力气,已经走不动了,几乎就要躺在雪里一睡不起,但他们终于走到了。
黄白华接到消息,说他的妻子蹚着大雪进来了,不顾一切地进来了。黄白华丢下手上的事,没命地朝山下跑去。他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他的妻子和那个可爱的战士。他们在雪山脚下,是两个慢慢蠕动着的小黑点。他咧开嘴傻笑着,揩一把头上的汗,撩起两脚的雪朝他们奔去。
他跑近了。
他站住了。
他像一个真正的傻瓜似的站在那里——那肯定是他的妻子,她一身雪,仰着乌紫色的脸儿,两只手探索着,远远地伸向前方,明亮的眼睛呆滞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害上了雪盲,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叫她。
她听见了他的声音,她能分辨出他的喘息声来,她朝他伸出手去。她也叫他。
黄白华扑上来,紧紧地、紧紧地、害怕再失掉了似的搂住了妻子。
那个汉子,就那么站在雪山脚下,呜呜地哭出声来了。
那个战士没有害雪盲,他在察禺当了两年兵,锻炼出来了。但他因为一直搀扶着黄白华的妻子,用他的身子支撑着她,甚至把她在雪地里一步一步地拖着走,以至于他向着阳光那一边的脸被紫外线严重地灼伤了,成了黑色。
讲这个故事的人告诉我,一年之后,有人看见了那个战士,不知他在和身边的战友说着什么事情,在那里呵呵地笑着,他那张英俊的脸仍然是阴阳分明的。
雪山很美,所有见过雪山的人都这么说。
另一个故事说的仍然是察禺的事,仍然是进察禺探亲的家属的事。
这回不是一个,是二十几个,二十几个在内地做西藏军属的女人,因为自己的丈夫要巴心巴肝地守着边境线,生生死死地守著边境线,不能按预想的那样回内地探亲,就索性约好了时间,结了伴一起进西藏来探亲。
到昌都了,离丈夫近了,丈夫们也知道她们来了,两边都急切着想要早一点见面。包袱一丢下,脸来不及洗,女人们便争先恐后地拥进邮局打电话。电话一通,没说上两句体己话,就知道情况不妙——通往察禺的路因为雨季造成的塌方,断掉了,不是断了一处,也不是断了两处,而是断了好几处,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那怎么办?”女人在电话这一头叫。
“等等吧,也许会修好的。”男人在电话那一头安慰女人。
等吧,那就等。
谁知一个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故事说完了,路却还没有通。
通是通过,但没通两分钟,又断了。西藏这种地方,到了雨季,这是很平常的事,雨季路不断反倒显得不正常。
女人们急了。女人们大老远地赶到西藏,来见自己的丈夫,来和自己的丈夫团聚,却被耽搁在半道上白天黑夜地讲着故事。她们有的请了一个月假,有的请了两个月假,不管假请了多久,大家在成都集中时花去了一个星期,从川藏线进来又花去了一个星期,在昌都等路通再花去十天,眼见一个月时间快要过去了,连丈夫的影子都没见着。还得从川藏线出去呢,还得从成都返回各自的家乡呢,女人们总不能在昌都一直等下去,等到海枯石烂吧?
女人们的丈夫从察禺打电话过来,说:“要不,你们回去?你们回去,等明年,或者后年再进来?”
“不!”女人们喊。
“不!”有女人咬牙切齿地抹开眼泪了。
女人们抹泪的时候,情况再一次出现变化。变化的不是路,路仍然没通,仍然断得不成样子。变化缘于一位西藏军区副司令,那位副司令正在昌都检查工作,听说了察禺的一群军官因为国防重任不能回家探亲,听说了他们的妻子结伴进藏来探亲却被堵在昌都,做着海拔四千米高原上的织女。副司令听说这件事后眼睛红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让女人们就这么离开!不能让她们的丈夫眼巴巴看着她们离开!就算通往察禺的路断得不可收拾了,断成盘古开天地前的样子,就算前往察禺的山全都塌下来,也要把女人们送进察禺,让她们见到她们的丈夫!”
副司令下令:由昌都军分区组织最好的车辆和人员,送女人们进察禺;通知前往察禺路途中所有的部队和武装部,组织精干力量,在每一处断路的地方等着,女人们一到,就把她们背过去、抬过去、扛过去、架过去,再往前一站送,一站一站,一直送到察禺!
在滞留昌都十几天后,女人们再次上路了。
车艰难地往察禺开去。在第一个断路处,她们下车,由等在那里的部队和武装部组织的人员搀着、架着,攀过烂石,蹚过泥浆,送往另一头等待着的车上,再往下一个地方开去。就这样一程又一程,交通工具不断变化——越野车、卡车、吉普车、拖拉机,在接近察禺的地方,一身泥水的女人们已经换成了骑牦牛或者改成了步行。
她们朝察禺走去。
在察禺等候的丈夫们已经接到消息,在最后一个断路处等着了。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人给我讲了最后的那个场面:当女人们出现时,等待在那里的男人们朝她们奔来,她们也朝自己的男人奔去,他们和她们跑近了,紧紧地抱在一起。然后,二十几个来探亲的女人和二十几个边境线上的男人都哭了。
(齐齐格摘自《文汇报》,王小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