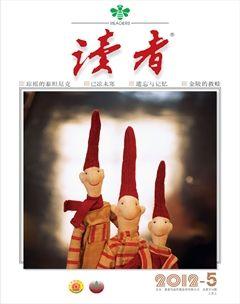说不尽的风景
桑永海

那位年轻诗人的句子,至今仍被人们传来传去——“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
但是,依我看,你真正熟悉的地方更有风景,并且是动你思动你情的风景,是与远方的陌生风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方说故乡的茅屋,屋前那株萧萧白杨。
离开故乡几十年了,我经常忆起这样一个场景:海兰江边,沙滩上,晚霞升起的时候,一帮朝鮮族小朋友看群鸟从林梢飞过,拍手齐声唱起一首朝鲜族童谣,一遍又一遍,直到鸟儿变成小黑点儿,融进绛紫色的夕照。那童谣唱的是:“嘎嘛嘎——嘎嘛嘎,尼林吉皮不日不特大!”(老鸹子啊老鸹子,你家房子着火啦!)从朝鲜族小孩的口中说出来,顺口押韵,抑扬顿挫,特别好听。
这首童谣,就和故乡的晚霞、树林、江流、黄昏,和驮着夕阳匆匆赶路飞回家去的鸦雀,和张着大口鼓腹而歌的朝鲜族小朋友一起,像少时读过的唐诗宋词,铭刻在记忆里了。那境界,大概跟辛弃疾“斜日寒林点暮鸦”的词意有些相近,但又不大确切,因为小孩子心里那时是很快乐的。
类似的人生体验,定是人皆有之的。
比如萧红,黑土地和呼兰河水痛苦的乳汁养育了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流落香港,身心交瘁,却仍对遥远的呼兰河,对故乡的火烧云,对后花园,对园里的蝴蝶、蜻蜓、蚂蚱,对小黄瓜、大倭瓜……总之,对那些再熟识不过的故园风物人情至死不渝,倾注了满腔痴情,所以才有了《呼兰河传》这样“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盾语)。小小的“百草园”,不也是鲁迅童稚时代的乐园吗?
罗莎·卢森堡身陷囹圄,仍对生活充满渴望。墙角一株小草,铁窗外树枝上一只鸟儿的啼鸣,西天一片晚霞,夏季里一阵骤雨,一只飞进牢房里嗡嗡叫的大土蜂,都让她惊喜。她的《狱中书简》,我读了50年,百读不厌。以是观之,不是“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而是正如风景画大师东山魁夷所言:“归根结底,风景到处都有,问题就在于观察者这一方。”
然而,在风景面前,我们的感情和审美心理也并非是简单划一、黑白分明的,有时是很复杂甚至是矛盾着的。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尤其是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期,人们的心灵经受着深层的文化冲撞,更是如此。比如明治维新以后的东京,急速变化着的街道上,唯美派作家永井荷风怀着一颗诗心,苦苦追寻历史上江户文化绚丽的晚景:“时势的变迁,每日都有些往昔的名胜古迹被毁坏,这些都使我的市内散步带有无常悲哀与苦寂的诗趣。”(《晴日木屐》)最富凄寂之美的是那篇《夕阳》——你看荷风先生踏着木屐,携把雨伞,穿过喧闹的东京市区,到郊野遥望富士山。
他面对如血夕阳,临风怀想江户时代古典牧歌般悠远的情味和背景,那是怎样一种无奈和不堪的情怀啊!
我想起我们风景天下独绝的长江三峡。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曾经三次游历这个诗之长峡,还在巫山老城和白帝古城分别盘桓一天一夜。更不会忘记第一次乘船入夔门,蓦然抬头,看见孤崖上沐浴着晨光的白帝城时的心情。
去年一个晚间,我守在电视机前看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三峡大移民纪录片。突然,出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画面:大撤离的前夕,上千名少年学子,着统一校服,整齐列队肃立在江畔山坡上,面向危崖上的白帝古城行注目礼、告别礼。上千的少年齐声诵读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童稚的洪音响彻峡江长空,声声撞击着我的心。只不过几秒钟的镜头吧,我已是泪流满面。我知道,彩云缭绕的白帝诗城将永远悬在中华民族的心坎上。但,她的遗址,毕竟要沉没于江水中了。现代文明,确是一把双刃剑啊!
唉,说也说不尽的风景。
(问水摘自《文汇报》2011年12月18日,张运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