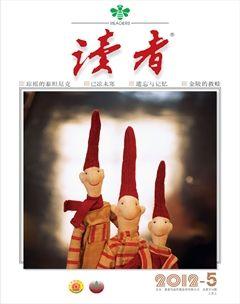看不见的竞争力
蒋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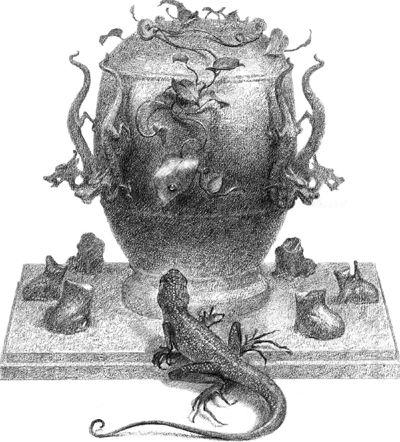
亚洲在市场经济的战场上跟着西方跑了一百年,很急迫地希望能赶快追上去。不是在后面追,而是能超越过去。我多么盼望我站在北京的街头,满眼看到的不是香奈儿、阿玛尼、宝马、奔驰……而是我们自己的品牌。这是我梦想中的北京,这里有过齐白石,有过曹雪芹,有过沈从文,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是最厚的,它一点都不输给巴黎、纽约。
当年我到北京时,沈从文先生刚过世,我很遗憾,但我的反应没有林怀民那么强烈。他是一下子就在沈先生的灵牌前跪下去了,沈夫人很惊讶。她不了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沈先生的书是“禁书”,我们偷偷在底下传,并且觉得,如果有一天能跟沈从文说“你一直是我的老师”,该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
所以你看,美的力量比什么力量都要大,它可以让你把未曾谋面的人认作老师,禁都禁不住。
这个城市有多少被你遗忘的角落?
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官家的轿子出来,前面有人举着“肃静”“回避”的牌子,一个小孩在路中间玩,他妈妈怕他被马踩到,惊惶地把他抱起。如果你受命拍一部关于北京的纪录片,你能不能拍出这样的画面?
还有一个画面出现在画卷快结束的地方。一个做大官的人进城,前有开道者,后有随扈。城门口有一群叫花子,其中有一个没有腿,做官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画家真了不起。我的学生问我:你觉得那个做官的人后来给乞丐钱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画家能画出大官跟乞丐的对视就很了不起了。
好几年前,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个画面:那一定是一个乡下来的妇人,因为只有下田劳动的人才会有那么粗壮的骨骼。她喂孩子吃奶,毫不遮掩,孩子吃饱了,奶汁还很多,她就让奶水滴到长安街上。我觉得这一幕好动人:她跟脚下的土地是在一起的。我问自己:T形台上的美跟这个妇人的美,哪一个能让我记忆更久?
美不仅仅是华服名模,甚至不仅仅是清风明月和巴赫、贝多芬,要看到美,我们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艰难。
唐朝人喜欢画牡丹。我曾在二月间到日本皇宫里看牡丹,它们全部用草围着,上面还撑着一把伞,因为牡丹有一点风吹雨打就会凋零。宋朝以后人们发现牡丹的美不能體现生命顽强的竞争力,就开始画梅花。元代王冕的《南枝春早图》成了传世名作。如果说唐朝创造了牡丹的美,宋朝发现了梅花的美,那么我们这个时代若用花来象征,可以找到什么?
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使用汉朝斗拱的造型,堆砌出一个倒梯形的飞檐式建筑。我看了很心酸。它的强是撑出来的。可是我看到英国馆轻轻松松就做出一个好漂亮的东西。当时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大国崛起,必须有最笃定的自信,不去做场面上的东西,而是回到最小的事情,慢慢做,不一定要那么快。现在的强有一点用力,并且用得好辛苦,我害怕它变成烟火,那么绚烂华丽,可是一下子就没有了。
唐的文化、宋的文化为什么有厚度?因为它看到大的,也关心小的。杜甫根据自己亲眼所见,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变成千古绝唱,我觉得不是因为诗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他看到了人。同样是那捧白骨,很多人走过去没有看到。
(肖成美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11月3日,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