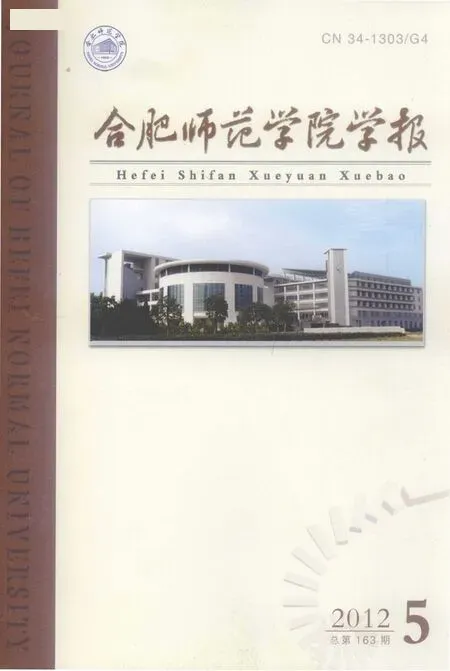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孩形象
苏 婷
(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合肥230061)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孩形象
苏 婷
(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合肥230061)
“女孩形象”是严歌苓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类人物,这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严歌苓笔下的女孩形象一方面折射了作家的创伤性童年经验,另一方面体现出作家细腻而又活泼的女性叙事视角。严歌苓塑造的女孩形象可以分为“文革”与“成长”两大类型,她们均体现出了女性特有的心灵世界和真实丰富的人性内涵。
严歌苓;女孩形象;成长;人性
“女孩/儿童”是严歌苓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早期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中的小点儿,《人寰》中“我”不断回顾中的少女时代的自己,还是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中的同名主人公,亦或是作为配角出现但着力刻画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和《小姨多鹤》中的女儿,均是一群性格各异、活泼灵动、引人注目的女孩形象。这些女孩形象在严氏小说中大量、有的甚至反复出现,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一
我们先对“女孩形象”做一个基本界定。从词语本身来看,“女孩”的含义显而易见,然而它的外延却又不够准确,到底什么年龄段的女性可看作女孩?毫无疑问,女孩是儿童,所以必须厘清“儿童”的年龄段。就心理学、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和目前的儿童文学理论等方面来看,一般将儿童的年龄界限定在18岁。[1]由此,本文所探讨的“女孩”即指18岁左右以下的未成年女性。为了避免对严歌苓小说中的女孩形象选择过于随意,本论文所选择的这些女孩具有一个共通的特征:身体或心灵处在成长变化阶段,未曾定性,而作品对其刻画的主要生活阶段也在18、19岁之前。因此,《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虽然出场时才14岁,但作品主要展现其成年后的一生经历,所以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而《我不是精灵》中的萧穗子虽然已超过18岁(刚满19岁),但小说重点刻画了少女穗子在初恋中对真实心灵的追求与成长蜕变,仍纳入本论题研究。通过以上的界定,我们可以对严歌苓小说中出现的女孩形象做一个统计,如表1:

表1 严歌苓小说中的女孩形象统计
截至2011年6月,严歌苓已公开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14部(《马在吼》作为《磁性的草地》的删节版和《金陵十三钗》的长篇未免重复未计算在内),中短篇小说56篇,而其中主要描写女孩形象的作品占其小说创作总数的43%,比例实在不小。因此,通对严歌苓小说中女孩形象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作品主题,也能从中窥探到严氏小说的独特风格。
从中国新文学的发轫期“五四”开始,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不断有作家关注儿童问题,并塑造出形态各异、鲜明突出的儿童形象。从鲁迅的《故乡》、《孔乙己》,萧红的《呼兰河传》,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再到汪曾祺《受戒》、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迟子建《北极村童话》,以及王安忆的“成长女孩”系列、陈染和林白关注女性童年身体意识的小说,它们均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存在。近二十年来对此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文章、硕博士论文也不在少数。然而,不论是研究单个作家作品,抑或进行群体研究,还是两两作家的比较分析,严歌苓所大量塑造的女孩形象却被排除在外。即便是严歌苓的专项研究,也只涉及了某些单篇作品,或者在硕博士论文中的一个部分论及,并未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产生联系。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和遗憾。
同属女性作家,严歌苓与萧红、林海音、迟子建、王安忆、陈染、林白等一样,不可避免地更加关注女性(包括女孩)的心灵、情感与命运,因此,她们的作品在题材与人物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然而,严歌苓是一位具有特殊人生经历的女作家,这必然导致严氏的女孩形象创作有别于其他作家。严歌苓出生于上海,童年生活在安徽,12岁进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舞蹈演员,入伍后几次进西藏演出,1979年又成为一名战地记者。30岁,严歌苓离婚后赴美留学,一边求学一边打工,艰辛异常,最终获得英文写作硕士学位。1992年,严歌苓与美国外交官Lawrence结婚后,开始专职创作。她还被邀请加入好莱坞编剧家协会,成为该协会唯一的华人编剧。2004年,由于丈夫的工作关系,严歌苓旅居南非。如今,她往来于中国、美国和南非之间,继续着别样的写作和生活。
这样经历丰富的人生,使得严氏小说中的女孩形象类型十分多样,其中有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单纯小姑娘、有活泼青春的女兵、有藏族少女也有外国姑娘,有生活在海外的第二代移民和杂技艺人,有被人贩子买下的内心坚韧的聪慧女童,还有命运坎坷的童养媳。严歌苓丰富的个人经历,也使其小说的叙述风格与内在意蕴不同于当代其他女性作家。
二
严氏小说中那些身份、性格各异的女孩,就其叙述技巧与深层意蕴的指向而言可以划分为“文革”与成长两大类型。
(一)“文革”女孩——来自“文革”的独特体验
这类小说中的女孩都生活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她们的人生、情感均受到特殊年代的影响,故事情节的展开直接与“文革”关联,以《雌性的草地》、《天浴》和“穗子”系列为代表,我们可以对其从叙述视角层面展开进一步细分与研究。
1.“她们”——雌性的群像。《雌性的草地》一直是严歌苓自己非常钟爱的作品,从2007年她将其重新修改删减为《马在吼》出版可见一斑。这个故事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小说刻画了一群“女子牧马班”年轻女性形象,以一位“美丽、淫邪”的16岁少女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叙述。在一个强调“红色”、“理想”、“集体”的时代里,女子牧马班的沈红霞、柯丹,包括小点儿在内,她们年轻的肉体和灵魂都被一种荒诞的庄严扼杀了。作者在一片红色的草地上,展现了人性在不合理的残酷时代一点点被毁灭的过程。与此相似,《天浴》同样描述了一个美好女孩、一份纯净心灵的消亡。小说一开头,作家以一种柔美、诗意的语调描绘了知青女孩儿文秀生活的自然环境:“云摸到草尖尖。草结穗了,草浪稠起来。一波拱一波的。”文秀也如这小草一样纯美而柔弱。为了回城,她只能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然而,一个个手握文秀命运的“关键”男人却只拿她当做玩弄的工具,肆意凌辱。文秀始终无法回城,只能一次次用水擦洗自己被侮辱过的身体,试图洗涤自己的痛楚与人性的罪恶,身处高原的沐浴因此具有了一种浓浓的象征意味。最终文秀在善良的放马人老金的帮助下,与生命永诀,她净白的身体永远地躺在了天上的浅池中,“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在那个时代,无数个青春生命与纯美人性如文秀一样被淹没了。无论是《雌性的草地》还是《天浴》都将至美至纯的女孩作为牺牲品,祭奠在了特殊时代面前,其中透射出作家对纯真生命与人性的追寻和赞美。
2.“我”/“我们”——个人的记忆。《穗子物语》包括了12篇中短篇小说,都是以一个叫做“穗子”的女孩的眼光来书写的“文革”记忆。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以成年后的穗子和女孩穗子两重身份为视角,或有侧重或有交叉。我们通过穗子的观察和讲述,看到了一幕幕女孩的人生:她自私地抛弃了疼爱自己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公”;作为“拖鞋大队”的一员,狠心、不负责任地伤害曾经保护关爱自己的同伴;她眼睁睁看着人们伤害“自尽而未尽”的角儿朱依锦,为此流下屈辱的眼泪;她与一只流浪的黑猫结下友情,黑猫却最终被冷酷的人类害死…女孩儿穗子是弱小的,善良的,但“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2]1。作家在《穗子物语》的自序表明,穗子只是自己少年的“印象版”,“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然而,“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2]1。女孩穗子,通过自己的眼光,呈现了“我”记忆中的“文革”历史。这种个人的记忆丰富了人们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也表明了一种重新审视历史的姿态。
(二)成长中的女孩——对于成长的细腻感悟
成长有两层含义:一是生理层面,人类的身体所经历的自然生命发展过程;二是心理层面,人在社会化的生活过程中个体意识、精神性格、心理气质等方面逐渐成熟、定型。虽然男性也同样有成长问题,但相较而言,女性对成长的体悟更加细腻与深刻。西蒙娜·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详细分析了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面临的巨大困境。她的性别意识、主体意识、理想范式均潜移默化地受到男性社会文化的影响。因此,波伏娃说:“女人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3]309从心理角度来看,一个女孩的成长洽洽意味着她与自己、家庭、环境所进行的艰难而又勇敢的唤醒与对话。所以女性作家更加偏爱“成长”主题,并热衷将描写的笔触放在女孩的情感、心灵、自我意识层面。就严歌苓的女孩成长故事来看,其关注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爱情的萌动。在女孩的成长中,对异性的情感萌动以及对自己身体变化所产生的惊异、不适、期待、好奇与欣喜等是最为重要的心理体验。短篇小说《黑宝哥》在严歌苓女孩形象作品中颇为独特。“黑宝哥大起来头会秃,真是我料不到的事。”小说以这样随意轻松、自然活泼的语调开始了“我”对黑宝哥的回忆。“我”第一次见到黑宝哥,就对他留下了不同凡响的印象:生吃大葱、茄子蘸辣酱,黢黑,很多头发,打败了个儿最大的一个初中生,“那一扑让所有孩子知道来了个叫黑宝的恶棍。”在一个文质彬彬的作协大院儿里,鲁莽生猛的黑宝哥是独特的,他的调皮与倔强赢得了“我”的倾慕。黑宝哥喜欢继母的女儿小璐子,“我”喜欢黑宝哥。小说中对九岁女孩儿“我”的爱情萌动,描写得非常动人:“走了很久,头也晒晕了。黑宝哥便来背我,我和他的汗顿时混得不知谁是谁了。他的脊梁漆黑,脖子上有一颗黑痣。黑宝哥黑得真俊,我想着,幸福着,幸福被他的步子颠得浑身扩散。”女性成长中心理与生理的最初悸动在严歌苓的笔下显得尤为细腻真实。《黑宝哥》同时以一种十分虔诚与敬慕的眼光描绘了女孩成长发育中的身体。夏天,大院儿里的小孩子都在楼顶天台睡觉,一家的席子挨着另一家的。一天凌晨,黑宝哥给“我”揭示了最美的一幕:“小褂儿下面是一对刚刚含苞的乳房。淡青的晨光中,小璐子的皮肤几乎晶亮透明,而那两丘凸起尤其晶亮,我浑身哆嗦起来,自卑得极深,因为我明白小璐子已从我们这些浑顽的孩童中脱离了出去,那具身体不再有孩童的单调。多年后,我还在想,我见过各种艺术家的女性胸像,而黑宝哥揭示给我的,是最美的。那时才九岁的我,突然对面前这个变化了的女童身体产生了类似膜拜的感觉。那感觉使我渐渐战栗起来。”这种对女孩发育中身体的礼赞,在当代其他女性作家笔下是少见的。女孩头一次认识到“性别”的独特涵义,开始迈向成长之门。“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是女性界定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4]208而这种性别意识的自我发现并没有借助外在的社会文化与成年男性的认识,似乎超越于这些之外,因而具有一种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这也间接传递出严歌苓有关“女性”的独特观点:通过对自己生命的丰盈感受来确认自身的存在,爱情与人性是最坦诚也最具有哲思的。女作家通过九岁女孩和女孩成人后的两重感受,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玲珑丰富的女性情感世界。
2.单纯的心灵世界。性格执拗,一根筋,内心单纯得犹如白开水,甚至显得有些傻、有些痴,这是严歌苓偏爱塑造的女性(女孩)形象。已成年的小渔、扶桑、田苏菲、王葡萄、多鹤是这样,未成年的小婵、毛丫和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也是。小婵是个馋丫头,出生后说的头一个字是“吃”,为了吃糖去亲单身的叔叔,贪图糖人主动帮吹糖人扯风箱,甚至因为一串羊肉而失了身。可是这最后的一次是小婵为了不让姥姥挨饿。文革后期,食物短缺,姥姥天天饿着却让小婵吃饱,这位姥姥其实是小婵两个月开始带她的保姆。当真正的姥姥从国外回来要接小婵去和父母享福时,小婵明明可以享受父母的餐馆再也不会馋了,却没跟着走。小婵的外貌、吃相、行为在小说里似乎为同龄人不齿,显得“浑头浑脑”,可人们终于认识了小婵心底里的单纯与美好。小婵虽然馋,馋得好像没了原则,但依旧不自觉地恪守传统的美好品质:知恩图报,穷“姥姥”的养育之恩就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和岁月去报答。12岁的小婵身上已隐约有了小渔、扶桑、王葡萄的影子,她们同为弱者,被欺侮、被贬损(小婵被同龄女孩嘲笑、衣服里被灌沙土、被她们丢弃在黑暗的公厕),却逆来顺受、沉默谦恭、麻木忍耐。然而跳脱于世俗、社会、文化、男性的眼光反观这些女性(女孩),我们却能发现她们身上有一种永恒意味的质朴人性与深沉母性。正如张爱玲所说:“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5]70
3.叛逆与残酷。成长中的青春总是伴随着叛逆与残酷,离家出走、遭遇虐待、反叛父母等成长期的创伤体验在许多描写儿童/女孩形象的当代小说中屡见不鲜,比如方方的《风景》、迟子建的《树下》、苏童的《城北地带》等。严歌苓的女孩形象小说也不乏此类,不同在于,她将描写的笔触漫延到了大洋彼岸。《冤家》中14岁的华裔女孩顾小璐正值叛逆青春,璐的单身母亲南丝一直按照自己的规定打造女儿的一切:戴牙齿矫正器、学芭蕾、优雅得体,让女儿远离她同性恋的父亲。女儿却在对母亲的物质依靠中尽量地反叛:奇装异服、恨芭蕾、以练芭蕾换取母亲的金钱“收买”。母女俩如此相互厮守又相互折磨,最终,顾小璐为了维护父亲的尊严和自己对父亲的爱,与母亲在车厢内撕扯起来,车祸后,“璐从棱形的车窗爬出来,看一眼夜壶形的车,看一眼身前身后冰川般的路,又看一眼母亲草莓状的脸。南丝眼睛睁开,看着璐头朝地脚朝天地沿公路走去。”小说结尾在这样一个异常残酷而又冷静的画面。《风筝歌》中,唐人街14岁的混血女孩英英雅致美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呵护有加。三十岁的鬼佬流浪汉肯特的到来,打破了英英沉静的生活与内心,肯特身上一股流浪和军旅的“生动”、“一种恰到好处的龌龊的俏皮”、“所有动作中的不安分”都使英英“产生一阵陌生的快意。”英英与当年自己16岁的母亲海伦一样,选择了背叛温馨惬意的生活,为了盲目的爱情逃离家庭,与流浪汉肯特私奔。她终于还是被抛弃沦为马戏团的溜冰皇后,未能如母亲一样幸运。《乖乖贝比》里的黄毛丫头贝比,瘦弱乖巧,被卖给旧金山的人贩头子阿鹏。她以自己的聪明、沉默赢得了残暴凶恶的阿鹏唯一的关爱与柔情,使自己在这个黑暗狰狞之地得以安身。贝比日复一日目睹多位同伴被阿鹏及其手下打骂虐待至死,她眼里所见的残酷与血腥已远远超越普通女孩的成长经历,因而她具有不止7岁年龄的早熟。《阿曼达》另辟蹊径,以一个在美国陪读的中国成年男性作为切入点,叙述他所遭遇的一场“阴谋的畸恋”。杨志斌陪博士妻子赴美,妻子已是律师的助手,自己却连英语都说不顺溜,薪水也只有三位数,这位曾经在国内大学的主角慢慢沦落为边缘人。他的失落却被一个14岁的混血女孩阿曼达拯救了。阿曼达在杨志斌的眼里单纯、柔弱,直来直往惹人爱怜,但小说已多次预留伏笔,阿曼达是多么撒谎成性。可在主流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杨志斌在少女阿曼达那里收获了仰慕、尊敬与依靠,一场奇异的恋情在两人之间产生了。结局却峰回路转,阿曼达控告杨志斌“诱奸”。小说并未点明女孩这样做的原因与真相,却展现了阿曼达复杂的生活背景所导致的她的多重样貌:婴儿般单纯的脸孔、早熟的身体、纯粹的孩子式的眼睛、说谎时的不经意和坦白、简单直接的脑筋、自然可爱的少女、成熟老练的小妇人、染发刺青的美丽年轻女人…家庭是女孩最重要的成长环境之一,阿曼达养成在单亲家庭,母亲跟所有人自来熟、爱贪小便宜、泼辣庸俗虚伪,有不同种族、国家的继父,遭遇继父的毒打与责骂,母亲与继父之间经常吵闹。从阿曼达的角度来看,她无疑是一位弱者,也只是一个女孩,惊天的谎言与真实的情感之间也许确实存在着并立的境况。
严歌苓在讲述叛逆与残酷的成长故事时,基本都以成年人作为旁观者或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叙述。字里行间冷静多于苦楚,客观多于控诉。小说要负担起的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穿人与人一切关系中的任何成规,任何恶劣、虚伪的常规。这种成规,包括“日常生活中、道德中、政治中、艺术中等等的成规”[6]359。严歌苓的重点并不在于建构一个无知无邪、干净澄澈的儿童天堂,也并未以展现社会现实、时代历史作为小说主旨,更不作出任何道德伦理的倾向或批判。作家似乎要在一种相对超然的笔调中逐渐剥开生活、人类的层层表面,逐渐触及到其中的深层内核:人性与成长中本无所谓善恶,在那些女孩的生命中,所有的言行不过是出自本质。“儿童曾是连续性和希望的无可争议的象征,是将其他一切价值集于一身的某种价值。”[7]127在错综复杂的人性中,女孩(儿童)的成长只是成人眼光的曲折的复现,本应单纯的儿童世界是由于成人的参与才显得叛逆与残酷。
4.对自我的追寻与反思。两百多年前,西方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家曾经有过一个命题:“儿童是成人之父”。虽然其中内涵广阔复杂,且也并非本文所探讨的重点,但这句话中所蕴含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儿童都会长大,成长影响成年人的一切。意大利著名的教育学家蒙台梭利曾说:“儿童的生活是连接两代成人的分界线。儿童创造的和正在创造的生活总是从一个成人开始又以另一个成人结束。这条航道总是紧紧围绕着成人的生活。”[8]349因此,我们在描写儿童(女孩)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成人的生活轨迹。成长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自我意识的确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不仅仅是哲学命题,更是成长的核心命题。严氏的很多小说展现了成长过程中的女孩不断自觉地追寻自我、反思自我与爱情的关系,体现出这些女孩对自我确证的强烈渴求。比如她早期的两部长篇小说《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两部作品均是第一人称回忆性的叙述视角,主人公同样是年轻的女兵(包括许多同龄的少男少女)。
《绿血》中的乔怡复员后成了一名编辑,偶然得到一部小说稿源,其内容竟是她本人曾经历过的事情,可小说的作者却不知是谁,因此,她踏上了寻访小说作者之路。寻访过程中,她不断地回想往事,与曾经的战友重聚。过去与现实不断交叉、更替,寻访稿源的作者,正象征了乔怡的寻找自我;对往事的追忆,恰穿插着乔怡对自我的反思。在一步步接近小说作者的过程中,乔怡也一步步从对往事的纠结和初恋的遗憾中找到了自我。小说最后写乔怡“豁然开朗”:“小说的作者终于找到,这并不足以使我这样快活。我快活是我感到自己的坚强,不再依赖你的爱生活了!我不再把失去爱看成致命的了!”“她想一个人呆一会。她正式独立。她业已成了一棵独立的树,在偌大的森林中占有一方土地,一顶蓝天。她将有多少事要做,凭什么让爱情伐倒呢?人不光为爱情活着。她不光为杨燹活着。她是坚强的、独立的树,坚强的、独立的女兵。从现在起,她要学会一种军人的爱。”女孩在成长中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坚强品性的女兵。《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仍以回忆展开,年轻女兵陶小童在临死之前对往事细细地追忆,自己怎样由别具一格的个体转变成集体意义上的理想英雄。在接近了所谓的“理想”之后,女孩却发现又失去什么最本真最重要的东西。虽然小说将大的背景放在了文革之中,但主题却是对成长和人性的反思。严歌苓在小说的后记《“悄悄话”余音》中写道:“这些生活在我笔下变得有些奇形怪状,令人发笑又令人不快。十多年前,我们存在于这些生活之中,毫不怀疑它的合情合理,而多年过去,当我的目光几经折射去回望时,当年合情合理的生活就显出了荒诞的意味。于是,我便对同龄人整个青春的作为感到不可思议。十年,我们赤诚而蒙昧。反常的社会生活必产生反常的心态,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便是反常心态的外化。因此‘悄悄话’一眼望去,满目荒唐。为强调一种荒唐效果,使人们透过荒唐去重新审定整个民族的素质”。这种反思发自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出自于一个未成年的女孩,但又不限定在女孩的眼光里,也不被限定在一个家庭、一个部队、甚至一个国家之中。这种反思架起了个人往日经验与当下思想的桥梁,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和所生活的世界。
中篇小说《我不是精灵》从爱情的角度,同样涉及了成长女孩的自我确认主题。小说描述了女孩萧穗子对自我与爱情的追寻,穗子最终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放弃令自己刻骨铭心的初恋爱人,选择了独立、自尊的现实人生。“这种看似意外的放弃实际上意味着成长,纯粹是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的自由选择,人物命运导向的是人性的复杂多变,而不是世俗的压力。”[9]女孩在对爱情的追寻、判断、选择之中,确认了真实的自我存在,完成了意义重大的成长蜕变。
三
综上所述,严歌苓女孩形象小说中的“文革”与“成长”两类意蕴主旨,最终统一为严氏小说的基本内涵——对女性生命体的真实存在和心灵世界的深邃透视与思考。在处理这些形象与主题时,深谙西方叙事学理论和小说创作技巧的严歌苓非常自觉地采用了第一人称回忆性视角和旁观者视角。这两种叙述视角的优点在于,作者可以以一种较为冷静、客观的双重身份——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叙述人和作品中主人公——穿越层层的时空,去揭示潜伏于“文革”或“成长”背后的真实人性。再加上作者移民美国的十几年海外生活经历,使得她在回望故土与过去时有着新鲜奇异的感知与思考。“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10]220这样一来,严氏小说并不凝重却充满理性,细腻感性之余有一种洒脱、跳动的内省。与有些女性作家一味以第一人称叙述现在时态的文本相比,严歌苓塑造女孩形象的回忆性叙事策略避免了“我”直接陈述、展现的尴尬与外露,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自我沉溺的逼仄,从而具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严歌苓女孩形象的塑造与独特叙述手法的运用,确实“提供了认识人自身的新的视角,也提供了表现人的精神现象的新的艺术手段”[11]。
[1] 何卫青.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2] 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M]//严歌苓.穗子物语》,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 萤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合肥安徽文艺出版,1996.
[6]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 蒙特梭利.吸收性心智[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
[8] 蒙台梭利.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M].任代文,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9] 赵跃鸣,黄静.让心里的永远属于心里——从《我不是精灵》谈严歌苓的创作[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
[10] 严歌苓.《少女小渔》台湾版后记[M]//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11] 钱理群.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四十年代小说研究札记[J].文学评论,1997,(3).
(责任编辑 何旺生)
Discussing the Girl Images in Yan Geling’s Novels
SU T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fei Normal University,Hefei 230061,China)
The“girl image”is a category of characters often appears in Yan Geling’s novels,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overlap in the child image in the modern Chinese fictions.The girl image in Yan Geling’s novels on the one hand reflects the writer’s traumatic childhood experience,on the other hand reflects the writer’s delicate and lively female narrative perspective.The girl im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s the“Cultural Revolution”and“growth”,they reflect a woman’s unique spiritual world and the real wealth of the human nature.
Yan Geling;girl image;growth;humanity
I206.7
A
1674-2273(2012)05-0082-06
2012-06-05
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1SQRW101ZD)“女性的传奇与现实——严歌苓小说风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苏婷(1979-),女,安徽合肥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