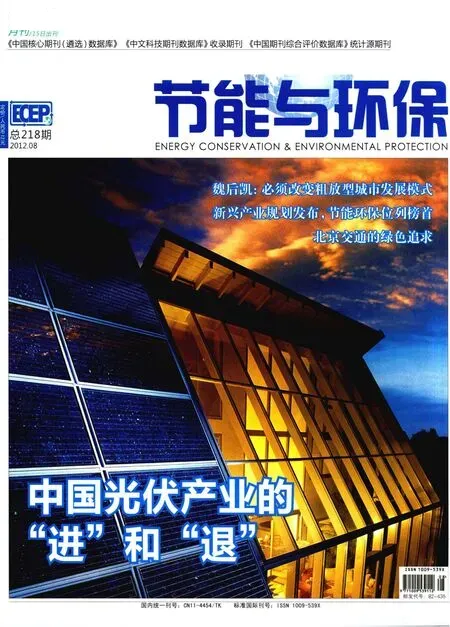魏后凯:必须改变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
本刊记者 陈向国

“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由17.92%迅速提高到51.27%,平均每年提高1.01个百分点,其中1996年到2011年,更是进入了加速推进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目前,城市经济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对本刊记者说。魏后凯以2010年的相关经济数据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地位:“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积占全国的6.5%,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6.3%,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55.1%和66.7%。”由此可见,城市发展方向与城市经济质量直接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质量:最终决定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
“中国城市经济的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消耗、高排放基础之上的。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9.5%,而一次性能源消费占世界的20.3%,其中,煤炭消费量占48.2%,水泥消费量占56.2%,钢铁消费量占44.9%。根据国际能源署2011年发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世界总量的23.6%。尽管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仅相当于OECD国家的52.2%,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9倍,是OECD国家的5.68倍。中国经济的这种高消耗、高排放特征在城市经济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魏后凯如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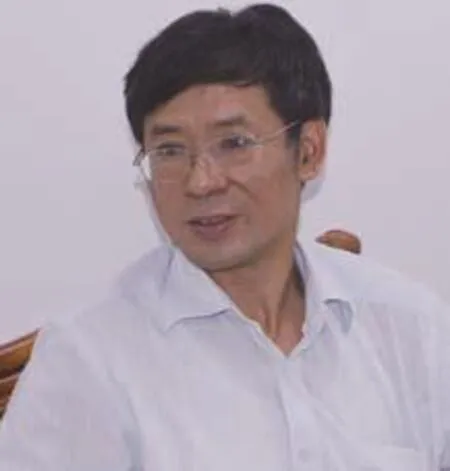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生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资源经济与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全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高能耗、重污染为城市化进程亮红灯
粗放型城市化模式,造成高能耗和城市的环境严重污染。这与城市化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背道而驰。高能耗、重污染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亮起一盏红灯。
相对较低的城市化率却消耗绝大部分能源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的高消耗、高排放特征在城市经济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但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达到51.27%,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您为什么会得出上述结论?
魏后凯:目前,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高,但实际上绝大部分资源都是由城市消费的。以能源消费为例,在2009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中,公交行业和城镇生活消费占85.2%;在生活能源消费中,城镇占61.0%;城镇人均生活用能量是农村地区的1.83倍。根据国际能源署2008年的数据,2005年,中国41%的城镇人口产生了75%的一次能源需求。这与世界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镇人口的比重一般都高于城市一次能源需求的比重,而我国则呈现城镇一次能源需求比重远高于人口比重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高消耗、高排放主要是城市经济的高消耗、高排放,中国节能减排的关键在城市。
记者: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目前加速发展的城市化带来了高消耗、高排放?
魏后凯: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城市化有利于推动新增长极的形成,有利于资源集约利用和产业升级,有利于环境污染的集中治理和创新氛围的形成。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的高消耗、高排放特征是由于城市的发展模式依然延续着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的,而非城市化本身的必然产物。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将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努力做到又好又快推进城市化发展。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城市化发展之所以出现城市化率相对较低,而消耗资源能源却相对较高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强调速度之时,有意无意忽略了发展的质量?
魏后凯:有这样的后果。过去中国的城市化具有“五重五轻”的特点,即重速度、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生产、轻生活,重经济、轻社会,重开发、轻保护。中国的城市化近年来推进很快,但质量却较低,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之间严重不协调。也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高速度、低质量”的城市化。
记者:有何表现?
魏后凯:主要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协调、不和谐、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以城市空间扩张为例。自“十五”以来,中国城市建成区和建设用地规模迅速扩张,其增长的速度远快于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2001年到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分别为5.97%和6.04%,而城镇人口年均增长仅有3.78%。更值得关注的是,“十五”期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分别为7.70%和7.50%,而在此期间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仅为4.13%。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严重不匹配,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由于城市空间高速扩张,不断吞噬着周边的农田和生态空间,因此造成生了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在粗放的发展方式下,资源的高消耗必然带来污染物的高排放。我国城市化粗放型发展模式使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有学者称,中国城市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记者:高消耗带来的高排放对城市环境产生了哪些不利影响?
魏后凯: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城市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严重影响了城镇人居环境质量。比如,2010年底,仅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废水排放量已占到全国的60.0%,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占46.8%,SO2排放量占49.5%,氮氧化物排放量占53.9%,烟尘排放量占43.8%。这些说明,在一些重点城市,污染物排放已经严重影响了城镇人居环境。
记者:在城市环境中,近些年,人们都很关注“垃圾围城”的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魏后凯:虽然人口的城市化赶不上土地城市化的速度,但城市人口的总量还是在快速增长。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镇生活废弃物排放日益增多,“垃圾围城”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蔓延的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全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的城市已经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城市边缘土地沙漠化、城市热岛效应、水资源污染、空气质量堪忧、原生态植物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频繁、噪声和光污染严重等。
2011年,在全国监测的468个市(县)中,有227个出现酸雨,占48.5%;在全国200个城市开展地下水水质监测的4727个监测点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高达55.0%;城市氮氧化物含量、PM2.5浓度普遍偏高,按照2012年2月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国有2/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记者:城市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魏后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工业污染。比如,2010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864.4万吨,是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的5.81倍;同期工业烟尘排放量为603.2万吨,是生活烟尘排放量的2.67倍,可见工业污染远超过生活污染。目前,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工业污染排放呈现强相关性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污染排放效应趋于强化。
无序开发和摊大饼式的膨胀面临多重风险
目前,尽管国家对房地产依然执行严格的调控政策,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开发冲动一直没有消失:只要稍有所谓“放松”迹象,地方政府就会“积极”做出大胆的试探性措施,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众所周知,房地产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与象征,地方政府正是紧紧抓住这个基础,“顺应”加快推进城市化的“潮流 ”,不失时机的抓住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创造”条件全力推动城市化进程。而实际上,在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却藏着欲盖弥彰的实际需求。“在现行体制下,各城市政府热衷于依靠卖地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可以说,‘土地财政’是诱使近年来城市空间高速粗放扩张的主要驱动力。”魏后凯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
中国城市空间无序开发现象十分严重
“这种以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带来了无序和低效开发。”魏后凯直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端。
记者:您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无序和低效开发,有哪些具体表现?
魏后凯:主要有5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一些大城市“贪大求全”甚至好高骛远。全国有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40个城市要建CBD,盲目向伦敦、纽约、东京看齐。二是各地开发区建设泛滥。前些年,各地不管有无条件都竞相建设开发区,致使开发区数量多、面积过大,大批不具备条件的开发区“征而不开”、“开而不发”,造成大量耕地闲置撂荒,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针对这种乱象,中央政府经过3年多的清理整顿,到2006年12月,全国各类开发区由6866个核减至1568个,规划面积由3.86万平方千米压缩至9949平方千米。三是沿海一些城市地区开发强度过高,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目前,深圳的开发强度已达到40%,东莞达到38%,这样的强度,远高于香港(19%)、日本三大都市圈(15.6%)、法国巴黎地区(21%)及德国斯图加特(20%)的水平。某些大城市地区有变成大范围水泥地连成一片的“水泥森林”的危险。
无序和低效开发还体现在城市用地不合理上。表现为,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居住和生态用地比重偏低。2010年,全国城市工业用地规模高达8689.49平方千米,占全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21.9%,而生态用地(绿地)比重仅有10.2%,居住用地比重虽然近年来快速提升,但也只有31.2%。最后,无序和低效开发还体现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上。各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多依靠土地的“平面扩张”,土地和空间利用效率较低,尤其是一些城市大建“花园式工厂”,各种形式的“圈地”现象严重。从空间开发角度看,可以认为,过去有些城市的工业化是以牺牲人的福利为代价的,工业用地规模过大、价格偏低、比重过高,利用效率太低。

“摊大饼”式的膨胀面临种种难题
由于各种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高度集聚产生的极化效应,导致近年来一些大城市人口迅速膨胀,用地规模急剧扩张,城市空间不断蔓延,建成区“越摊越大”。
记者:近几年,有关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到底能承载多少人的问题备受关注。您能从我国城市扩张的角度谈谈您的看法吗?
魏后凯:目前,北京、上海、重庆、深圳人口均已超过1000万,广州、武汉、天津已超过600万,此外,还有一批超过400万的城市。从1999年到2010年,这些城市建成面积从3194.24平方千米急剧扩张到9179.9平方千米,增长了1.87倍。其中深圳增长了5.27倍。
记者:人口的膨胀与城市建成面积的增长给大城市带来了哪些问题?
魏后凯:人口和新建成区、建设用地规模的急剧膨胀,甚至“摊大饼”式向外蔓延,造成大城市交通堵塞,住房拥挤,房价昂贵,资源短缺,生态空间减少,环境质量恶化,通勤成本增加,城市贫困加剧,公共安全危机凸显,致使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明显的膨胀病症状。就拿中国远未饱和的家用汽车来说,每百户拥有量不高,如北京29.6辆(2009年),上海、广州和杭州分别为17辆、21辆、23辆(2010年),但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各大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首都北京更是被戏称为“首堵北京”。房价和生活费用高昂,生态空间不足,环境污染突出,各种社会矛盾纠结,是这些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
城市转型有力量
粗放型城市化模式必须改变。改变需要强大动力。中国有这样的强大动力吗?
中国城市发展拥有转型的现实推动力
“中国城市正处于加速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一方面城市转型的速度将加快,另一方面,城市转型将呈现出全面转型的特征。”魏后凯认为。
记者:有哪些因素在推动中国城市加速转型和全面转型?
魏后凯:主要有4种推动因素。一是城市发展理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种观念的重大变革,将引领中国城市的重大转型。近年来,全国各地建设和谐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的热潮方兴未艾,雨后春笋般的建设实践就证明了这种城市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二是中国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定阶段本身具有的推动力。目前,中国相当一部分城市的人均生产总值已经接近或超过1万美元,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他与人均生产总值1万美元还有差距的城市(中西部城市)也正在千方百计地迎头赶上。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今后主要的努力方向是提高工业化的质量;对于超过1万美元的大城市而言,今后的重点是向高端化和服务化转型。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也有能力花更多精力来解决城市民生、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张。
城市面临的资源与环境越来越大的约束力是城市转型的第三个推动因素。近年来,中国城市日益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双重收紧约束。在传统粗放发展模式下,中国城市的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特征,加剧了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承载力有限的窘状,由此带来诸多方面的弊端,这是不可持续的。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传统粗放发展模式的终结,一些沿海城市和中西部资源型城市已经出现相对衰退和竞争力下降的迹象。因此,从提高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角度出发,加快城市的全面转型势在必行。
第四个推动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管理方法的不断进步以及制度创新的不断推进,将为中国城市由以资源和投资为特征的投入驱动,向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为主体的创新驱动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同时,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也在发生变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发展、低碳消费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居民更加重视城市的宜居性,从而推动城市创造更加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
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保证城市发展各种效应合力为正
魏后凯认为,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由此驱动着环境系统的变迁,继而影响环境质量。由城市化引起的各种活动集聚、规模增长、结构变化、知识积累对环境系统的影响分别具有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并同时发挥交互作用。当各种效应的合力为正,城市化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否则,结果正好相反。我们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使合力为正。
记者:应如何使合力为正?
魏后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是一种高速度、低质量的粗放型城市化。要减少城市化的环境负效应,就必须在努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增强环保能力建设,通过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城市发展和城镇化的双重转型。
记者:请从城市发展和城镇化双重转型的角度分别阐述。
魏后凯:从城市发展转型看,关键是从根本上改变以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低效率、不协调为特征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加快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和谐有序的新型科学发展模式转变,全面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从城镇化转型看,必须尽可能减少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城镇化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可持续城镇化转变,即未来中国应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融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兼顾,经济高效、资源节约、生活舒适、生态良好,具有可持续性的低成本绿色城镇化道路。
提高城市化质量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改变粗放型城市化模式有了现实的动力。在全力启航之时,必须再次明晰发展与能耗和环保、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在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资源、能源“零增长”
无论如何,中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面临着能源和资源超常规利用的巨大压力。根据相关的规划和要求,到2050年,中国城市要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费速率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根据目前中国城市资源能源的消费状况,完成目标绝不可能轻松。
记者:您觉得资源和能源消费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魏后凯:从我们的判断看,有可能完成,但压力很大。我们应该站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这个国情上看待这个问题。欧美国家有他们的盘算,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在2020年就实现能源消费总量下降,而我们自己则希望在2050年前后实现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要看3个指标的完成情况。第一个指标就是能源消耗和排放强度;第二个指标是人均消耗和排放强度;第三个指标是能源消费和排放总量。这三者的关系是,第一个指标是第二个指标完成的基础,第二个指标和第一个指标是第三个指标完成的基础。现在,我们的第一个指标已经下降了,但第二个指标时降时升,能源消费总量整体上还处在刚性增长的阶段。这种特征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仍在快速推进、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爬升阶段的特征相符合。我们对目标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记者:您所说的“清醒认识”包含哪些含义?
魏后凯:首先从现在国家对节能减排国策的执行力度看,到2050年前后,目标有可能实现。但要注意,实现目标的前提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生态友好的基础之上。第二个含义是立足在较快速度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目标。我们要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但不能以停止发展脚步的代价完成目标,否则国家将面临更大困难;我们也不能因发展而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于不顾,一味求发展,我们要的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协调的发展,而非其他。我们有可能完成目标,但绝不会轻而易举。
记者:从“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完成的结果和过程、以及目前“十二五”分解目标的完成情况看,的确印证了目标的完成绝不会轻而易举。那如何看待我国政府对完成目标的努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魏后凯:我国政府对生态和环境保护,对节能减排高度重视,切实负责,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我们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尽全力予以推进: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采取了可以采取的各种方法,甚至为了完成目标不惜代价。如我们采用的目标层层分解法,配之以一票否决权的严格考核办法,这样的力度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力度是独一无二的。在履行承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意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节能减排的最终目标是要经过三五十年不断推进的过程的,是长期不断努力的结果。在履行承诺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发展权问题。发展权问题既有我国整体的发展权问题,又有我国境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地区的发展权问题。不能拿国外发达国家的标准对我国的发展进行束缚,在国内,不能拿发达地区的标准制约不发达甚至落后地区的发展。当然,不发达地区(落后地区)也不能以发展权为名对资源、能源粗放使用,对环境的承载力不予考虑。
正确处理城市化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事实证明,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型城市化发展之路不可持续。魏后凯告诉记者,“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是提高城市化质量”。
记者: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是怎样的?如何处理速度和质量的关系?
魏后凯: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城市化将进入减速时期,从中长期看,每年的推进速度将减至0.8~1.0个百分点左右。预计到201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5%左右,2020年将达到60%左右。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城市化率并非是越高越好。有学者认为,对于一个大国而言,75%~80%可能是城市化率的天花板。有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至今无法触及这个天花板,我们的邻居日本城市化率2009年也才66.6%,只有像新加坡、比利时等一些小国城市化率才超过90%。一句话,城市化的终极目的是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的核心增长极,是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它只是手段,我们追求的并非城市化率本身。一旦城市化率达到一定的比例,城市化质量达到一个高水平,资源、能源集约利用,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实现了协调发展,甚至农村超过了城市,那么,城市本身对人们的吸引力也就没那么大了。到那个时候,有些人会放弃城市生活,选择在农村生活。
近些年,我国城市化呈现的总体特点就是速度快、质量差。今后,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将有一定程度的减缓,但仍属于快速发展的范畴。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城市化推进的核心就是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以质量为重。
记者:如何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魏后凯:衡量城市化质量高低的标准主要有3个,一是城市本身的发展质量;二是推进城市化的成本,尤其是资源和环境代价;最后一个是城乡协调程度。在推进城市化的成本方面,我们的代价显然是昂贵的,有时甚至以牺牲人们的生活福利为代价,以过度消耗资源、能源为代价,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与推进城市化的目的南辕北辙。提高城市化质量必须降低推进成本,减少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提高城市化质量还要尽力缩小城乡差距,近些年,我国城乡差距虽略有缩小,但仍然很大,尤其在西部落后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我们的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产业、人口通常集聚在城市中心,造成交通拥堵、环境质量下降等现象,这些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