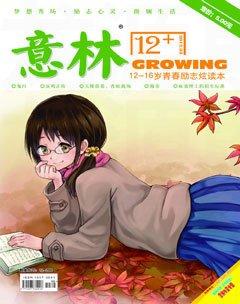柴静对抗柴静
李岩
南都周刊:电视里,和采访对象谈话的你很有特点,和你平常时一样吗,你喜欢那个时候吗?
柴静:谈话的时候,头盖骨就像是掀开的,神经裸露在外面,任何一个响动都会让我痛苦。我的摄像师移动的脚步、喝水的声音,在我耳朵里都会变得特别大,不过我平常不说。那是一种生理反应,你把全部生命都倾注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这样,那两个小时里面,这个世界不存在,只有那一个人。
南都周刊:你电视中的神态总是那么平静,你自己怎么总结你的对话风格?
柴静:我是个小暴脾气,离真正的宁静还远着呢。我觉得对话不太应该有风格的想法,实际上很多记者都是在这个想法驱使下走火入魔的,一旦认为自己的采访能形成风格的话,就会把它推向极端化,最后你的幽默、尖锐,甚至真诚都变成标签,这很危险。对话的第一要求是准确,接近事实,风格往往是阻碍自己通往真实之路的东西,所以反而要卸下。
南都周刊:你小时候学习成绩怎样?
柴静:对课堂没兴趣,反抗的方式就是拿一个本子默写我喜欢的诗句。现在想起来,前18年的自己很没有生活經验,也没有常识,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没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如果小时候我就是语文课代表、考试前十名、作文竞赛一等奖、学生会副主席、天天参加演讲比赛,那你日后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把这些经验忘掉。
南都周刊:都是好的经验,你会想要忘记它们吗?
柴静: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里的这些经验,对现在做记者会成为障碍。
南都周刊:你在中央台报道过很多公共事件,现在它们越来越多,有没有人问过你:中国怎么了?
柴静:“怎么了”这个事情,你要去探究当中的因果,不要放大一件事情的耸动性,耸动当中把它推向极端化,极端化中再用情绪去渲染,结果就全部是惊叹号,没有问号了。新闻是问号的,新闻到最后应该一切是寻常的,现在只给你奇特不给你寻常,你就理解不了世界。比如说,做人物的时候要把自己当成作家而不是新闻记者,记者总想发现最奇特的东西,文学是要写出寻常的东西。
南都周刊:你现在的知名度,你觉得有没有外形的因素?外界也给过你“美女记者”的名号。
柴静:我外形平平吧,中央台有无数的美女。女性化的外表会给人偏柔弱和偏脂粉气的印象,这两项都是新闻的障碍。我刚开始在《新闻调查》干的时候,有次采访穿了个白衬衣,左手上戴了一个非常细的小银镯子。采访前,一个很资深的同事说停一下,然后把我叫到旁边,说“你不戴不会有人不喜欢,戴了可能会有人不高兴”。从那以后我在节目中没有戴过任何首饰,也不会再作任何修饰。新闻应该让一个人越来越朴素,你每天打扮得精巧无比,坐下来的时候两个腿还要拧成麻花,你忘不了自己,你怎么还能够关心对方。
南都周刊:相比之下,你会更喜欢“文艺女青年”?
柴静:这词挺好的,我只是还不够文艺而已。文艺青年应该是有很多生活中的趣味啊,审美上的要求啊,我没有吧,我好像不足以匹配。文艺是两个很好的字,现在很多配不上的人都在消费这个字,更不要说践踏这个字了,这也是对文艺的不敬重吧。
赵红星摘自《南都周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相关内容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