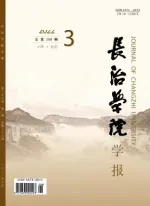古汉诗语言模糊性及其翻译
武 宁
(遵义医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3)
一、引言
语言与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1]语言学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模糊语言学理论已经运用于指导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探讨文学翻译的本质、翻译的策略、方法以及翻译批评等问题。[2-5]运用模糊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文学翻译当然也包括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问题,中国古代诗歌是中国文学的精华,古汉诗讲究模糊美,模糊性是古诗语言的重要特征,中国古诗英译要充分再现原诗语言的模糊性特征,达到与原诗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效果。
二、古汉诗语言的模糊性
“模糊”这一概念是模糊集合论的首创者札德(L.A.Zadeh)提出的,在其代表作《模糊集》中札德认为,我们应将模糊集合论看作探索某种不清晰性的一套概念和方式,这种不清晰性是指我们研究对象构成的类属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所指的并非某个点属于集合的不确定性,而是从不属于到属于变化过程的渐进性。[6]这是对模糊性概念所做的最早描述,这一定义中所提到的“变化过程的渐进性”充分说明了模糊性亦此亦彼的特征。自札德提出“模糊”概念以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致力于语言的模糊性研究,伍铁平教授强调语言模糊的客观性,他认为语言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因为说话者的无知导致的,而是由于说话者的语言特点就是模糊的。[7]而李小明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了语言模糊的客观性,他把模糊性看做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8]至此,语言模糊性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都有所论述,总之,语言模糊性就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在语言中的反映。
模糊性既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也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基本特征。文学是艺术,诗歌更是艺术的艺术。艺术家的思想是“混沌”的,浑融是其生命,如果你试图让这种“混沌”变得清晰,那它的本性就要失落,艺术就会死亡。[9]诗歌是借助语言形象描绘世界,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艺术。诗歌语言具有朦胧的、模糊的美,诗歌常以最少的语言塑造使人产生无限想象力的意象,表达诗人复杂的心绪。诗歌语言凝练、精粹,其内涵却相当丰富,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伸张性和联想性。这就使得诗歌内涵或意境的亦此亦彼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模糊性往往表现为大量的模糊用语如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和叠加意象等,与精确语言相比,诗歌语言有更多的简洁性、暗示性、独创性和音乐性,是音美、形美和意美的完美统一。可以想象诗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所描绘的动静互渗、你中有我、我中融你的模糊意象美。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所追求的“此处无声胜有声”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使得诗歌产生模糊美,而这种模糊性的最大魅力在于其文学空白和不确定性使其呈现开放性和无限的阐释性,给读者留下大量想象的余地。
三、古代汉诗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模糊性是文学翻译不可回避的问题。已有学者就翻译中如何再现源语语言的模糊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翻译中模糊与模糊、精确与模糊之间的转换策略。[5,8]翻译过程也就是理解和表达的过程,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在古汉诗模糊语言的理解过程中,我们应该利用思维的模糊性对纷繁复杂的语言进行分析和综合处理,即模糊理解,从而准确把握全文。在模糊表达阶段,要积极运用目标语中的模糊语言来替代原诗的内涵,跨越语言文化差异,尽量减少原语损失,实现成功交际。同时,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其语言和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因而汉语古诗和英语诗歌在表现模糊美感的价值功能和审美效应都存在差异,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要灵活采用恰当翻译手段对古汉诗模糊语言效果的遗失进行补偿,从而使译诗与原诗在表达效果上达到有机的、模糊的、动态的对等。
(一)语音模糊与翻译
语音模糊性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语音现象。区分语音的主要因素是人的发音器官和发音方式,人的发音器官主要分为发音的动力器官、发音器官和共鸣器官,这几个部分的分割并非泾渭分明;发音方式主要表现为口腔的开合度、舌位、唇形等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没有一个精确的划分标准,因而语音的模糊性也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语音中的双元音、半元音以及语音中的同化、连读、失去爆破等现象都可以说是语音模糊性的表现。汉语古诗语音模糊性主要表现在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这种修辞手法利用语言中的一语多义或同音异义现象,表达双重含义,表面言此,实则及彼,达到一语双关的目的。翻译时,首选方法是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实在没有则选择相近的双关表达方式;最后还可以选择释意的方式。例如:
1)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刘禹锡:《竹枝词》)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My beloved is 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
2)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
The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The candle only when burnt has no tears to shed.[10]
以上诗歌中,“晴”和“情”同音,表面上说天气的阴晴,实则指人的爱情;“丝”和“思”同音,字面上讲春蚕吐丝,却隐含人的相思。古汉诗中的这种语音双关很难在英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取得相当的表达效果。许渊冲的译文将汉语的一语双关转化为英语中的“二语双关”,例1)中,译入语分别用“the day is fine”和“deep in love”来表达原文的双关;例 2)中汉语的“丝”分别译成“silk”和“lovesick”,两个译例将汉语的表面意义和隐含意义都表达了出来。
(二)语法模糊与翻译
语言中的语法模糊性主要涉及语法范畴分类模糊和语法界限不清的现象。语法模糊性以词法和句法两个层面比较明显,就词法层面而言,词的词类归属往往不确定,同一个词可以属于不同的词类;在句法层面,英语的时态就具有模糊性,如现在进行时既可以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也可以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汉语句法模糊也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汉语句法基本特征是“意合”,词与词,句与句之间重意合对接,它们之间不用表示语法关系的结构标记,使汉语的语法范畴高度模糊化。[11]语法模糊性在汉语古诗中比较常见,较之英语,主要表现为代词、连词缺省和单复数不分而引起的模糊现象,如王维《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I hear osmanthus blooms fall unenjoyed;/When night comes,hills dissolve in the void./The rising moon arouses birds to sing;/Their fitful twitters fill the dale with spring.(许渊冲)
Man at leisure.Cassia flowers fall./Quiet night.Spring mountain is empty./Moon rises.Startles a mountain bird./It sings at times in the spring stream.(叶维廉)
诗中没有出现一个人称代词指称人物关系,诗中的“人”究竟指的是“我”自己,还是指的别的什么人,原诗并没有作出明确交代,这就造成汉诗指称的模糊性,不同译者就会有不同的阐释,许渊冲选择第一人称“I”,而叶维廉将其译为第三人称“Man”。原诗也没有连接词表明逻辑关系,对于“夜静春山空”一句,许渊冲的译文增加连词“When”将时间顺序补译出来,而叶维廉则完全直译。原诗中的山鸟没有交代是一只还是一群,指代模糊。许译为复数,而叶译为单数。由于汉语古诗的语法模糊特征,在英译转换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英汉诗歌语法上的差异进行补偿,同时,因原诗语法成分的缺省产生的模糊性导致不同译者的理解差异,从而导致译文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不管补偿方式有多少差异,而表达效果上基本达到动态对等。
(三)语义模糊与翻译
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来讲,语义产生的过程就是概念化的过程,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类属划分是概念形成的基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类属划分的不确定性导致语义模糊性的产生。汉语古诗语义的模糊性使诗歌产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朦胧美。古代诗歌语义的模糊性常常由于指代不明、语法省略、一词多义等现象造成的。下面以《清明》为例说明古汉诗语义模糊性及其翻译策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In the Rainy Season of Spring/It drizzles endles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Travelers along the road look gloomy and miserable./When I ask a shepherd boy where I can find a tavern,/He points at 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杨宪益)
The Mourning Day/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Where can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mid apricot flowers.(许渊冲)
原诗中存在多处语义模糊,给读者留下更多更广的阐释空间。翻译者首先是一名读者,理解原诗是翻译过程的首要环节,不同译者对同一模糊表达会产生不同理解,因而会产生不同的译文。“清明时节”没有指明是清明节这一天还是包括清明节前后,杨译(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指的是清明节期间,许译(the Mourning Day)讲的是清明节当天;“路上行人”不知指的是诗人自己还是泛指出门在外者,杨译(travelers)指的是在外旅行的人,用的是复数人称,许译(mourner)指的是吊唁者,人称为单数;“借问”没有表明是谁问谁;杨译(I ask a shepherd boy)表明的是“我”(作者本人或其他人)问牧童,许译则没表明谁是发问者;“杏花村”是酒店名?还是杏树环绕的村舍?杨译和许译都选取后者。可见,古汉诗语义模糊性给译者留下更大的解读空间,因为译者理解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英译文,语义模糊性为不同译文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语用模糊与翻译
不同学者对语言中的语用模糊现象界说不一,但大致说来,语用模糊(Pragmatic Ambivalence)指的是说话人在特定的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同时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acts or forces)的现象。[12]语用模糊从语言的使用和理解两方面来考察语言使用的不确定性。诗歌中的这种语用模糊手段,大多是出于语言系统内部以外的考虑,使用迂回的策略间接、委婉地表明作者的意图。试看王昌龄《出塞》中前两句的英译: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The moon goes back to the time of Ch'in,the wall to the time of Han./And the road our troops are traveling goes back three hundred miles.(Bynner)
The age-old moon still shines over the ancient Great Wall./But our frontier guardsman have not come back at all.(许渊冲)
原诗中的名词如“秦时明月”和“汉时关”并不是真正写秦朝的明月和汉代的关隘,诗句的用意是想描写战士巡逻边关、仰望月亮而触景生情的心情。Bynner的译文完全照字翻译,令人不知所云,而许译没提原诗中的朝代,却传达出了原诗的真正语用意义。在翻译这类诗歌时,译者应该跨越原诗语言的表面形式,按照诗歌语境揭示其隐含意义或语用意义,从而传达出原诗的真正意图。
四、结语
模糊语言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文学的最高形式,中国古诗尤其注重语言的模糊美,古代诗歌中存在大量的模糊语言。在古诗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充分理解、把握原诗中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不同层级的模糊性,同时照顾到中英语言文化的差异,才能在译语中再现原诗的模糊美,使译诗与原诗实现表达效果的动态等值。
[1]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绪论.
[2]穆雷.用模糊数学评价译文的进一步探讨[J].外国语,1991,(2):66-69.
[3]文旭.语义模糊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6,(2):5-8.
[4]赵彦春.语言模糊性与翻译的模糊对等[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4):9-13.
[5]毛荣贵.语言模糊性与翻译[J].上海翻译,2005(1):11-15.
[6]札德.模糊集[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1,(1):66.
[7]伍铁平.模糊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36.
[8]关海鸥.语义模糊性理解与翻译策略研究[J].外语学刊,2007,(5):111.
[9]徐宏力.模糊文艺学概要[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74.
[10]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70.
[11]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69.
[12]俞东明.语法歧义和语用模糊对比研究[J].外国语,1997,(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