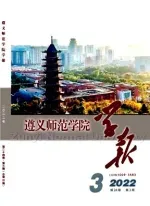解释人类学:论格尔兹及其《文化的解释》
张胜洪,刘晓静
(遵义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贵州遵义563002)
“文化的解释”作为《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中的一讲,在当前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研究范式。《文化的解释》的诞生不仅仅是源于时代的需要,还与其作者格尔兹息息相关;“文化的解释”并非一种突然出现的研究方式,而是有其历史的缘起(在格尔兹之前,斯特劳斯已有符号的解释)。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阐释:一是对格尔兹及其著作《文化的解释》的概要介绍,以期呈现著作的大致轮廓;二是对《文化的解释》一书主要内容的解读,以期对“文化的解释”展开进一步的理解;三是对格尔兹及其《文化的解释》进行评议,并阐述其对文化理解的启示。
一、《文化的解释》及其作者
说到《文化的解释》首先需论及的是其作者。因为一个人的成长史可能是其作品的一个预备,一部作品也必然带有作者的气质、性格及其成长的痕迹。如果我们对作者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对其作品的深入理解可能颇有裨益。
(一 )格尔兹简介
克里福德·格尔兹 (Clifford·Geertz,1926—2006),美国解释人类学创始人、象征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主张将社会当成意义体系来研究(而象征是意义的“浓缩形式”(condensed form),是多种意义的联想)。格尔兹在1950年获得俄亥俄州的安帝奥克学院的哲学学士学位。求学期间,深受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经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后于1956年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接触到社会学家帕森斯,这使他对克拉克洪的文化理论产生了批判。
有人称,格尔兹是当代美国人类学的代言人。实际上,他与列维·斯特劳斯一度获得的地位一样,是国际人类学界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最高代表人物。“据近年统计,国际社会科学论文中对格尔兹作品的引用远远超过所有的人类学家。在人类学杂志《美国人类学家》和《当代人类学》中,几乎每篇论文都要提及他的作品,就连较为保守的《英国皇家人类学院院刊》(旧称《人类》),格尔兹的论文也保持相当高的引用率。”[1]P3这虽与他的天资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来自他那种潜心于人类生活基本面貌的态度以及他的卓越领悟能力。
格尔兹在爪哇、巴厘岛和摩洛哥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毕生致力于对世界文化做“深”的解释。“‘深’意味着力图以这种文化自身的方式理解它的符号、象征和习俗,而不是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假定地球上所有的人类经验均可还原成结构。事实恰恰是,其他文化跟我们自己的文化一样‘深’,一样成熟,一样意义丰富,只不过可能有些‘陌生’,不太符合我们的思维方式罢了”。[2]P785这正像人类学传统研究方式——“离我远去”,进入“远方文化的迷恋”,以“他人的眼光”,入乡随俗地进行实地观察,进而迈入人文世界,进行主位研究,进行沟通、解释、对话、理解、交流,在理解他人的同时明白自己。而任何真正的人类学研究都是“像他人看我们一样审视自身”。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的解释》就是有这样追求与期望的著作。
(二 )《文化的解释》
《文化的解释》以具有地方浓厚文化色彩的爪哇、巴厘岛等地的实践研究与对文化进行解释的理论普遍性的结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类学研究的世界,为20世纪晚期以来的人类学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诠释学”(hermeniutics)道路。“诠释学”意味着:“其一,人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符号的和解释的;其二,作为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也是解释的。”[1]P117《文化的解释》正是将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作为一种符号体系而“深描”,探索符号意义的表达。文化首先是一种符号,而这种符号有其涵义、意义,是生活于其中的人给予的赋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就是通过这种对意义的解读、理解来进行;在互动中同时形成这种文化“气场”中的人的心理、观念、情感、道德、价值观。而这些又处于一个循环网络中对文化、社会互动、心理进行影响。格尔兹通过对爪哇、巴厘岛的实地观察对“文化概念对于人的观念的影响”、“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作为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了符号解读,来理解文化——社会——心理之间的互动、生成与沉淀。
二、文化的解释
(一 )文化解释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清晰文化是什么,文化为何需要解释,文化怎么解释,文化是由谁来解释,文化的解释是为了什么等基本问题,而后才会对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有真正的理解。
第一,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说是根本的:文化不可能定义,但可以有操作性定义。这是缘于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是不可穷尽与不可抽象的。在《文化的解释》中,格尔兹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3]P11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格尔兹对文化的操作性定义是将文化看作一种意义模式(meaning pattern),而这种意义模式又有其时间历程,是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共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可能是一种观念,但它还要表现于各种象征形式之中,在书中这种象征形式更多的是宗教。文化的符号(symbol)——象征是人与人之间即社会互动得以进行的基础。就在社会互动中,个人实现了社会化进程,并进而形成了个人的心理、人格、精神、价值观等。
第二,文化为何需要解释。文化的解释除因对文化的定义不同而不同外,还与对文化进行研究的方式不同而不同。文化人类学传统的研究方式一般是实地观察,而且是“离我远去”,到“他者”那里的研究。正是因为有了距离,才有了不同、陌生与惊奇。如果研究者还是带着自己的眼光,还是带着自己的眼镜去看另一个丰富的世界,那他就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他还是在以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文化去“评价”他人,从而忽视了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历史,根基及成长路径。研究者不能以所谓的“进步观”进行人类学研究,这样的研究是空洞的,是假惺惺的,也是缺失人类伦理道德的。
第三,文化如何解释。文化人类学研究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尊重:尊重他者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习俗,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当研究者将自己与他人放平的时候,研究即将开始。研究者的研究其实是一种“理解”,一种深度理解。理解就需要有一个换位和进入的过程,也即所谓的“入乡随俗”(和他人一起行动)。而通过什么来理解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答案是“符号”。为何符号是理解文化的关键?这与人的本性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有人的本性的话)。人不是客观存在的物,不是可实证的存在,而是一种意义的存在。当人面对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句话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这个人、这件事、这句话本身(尽管他首先是关心其本身),他总是会想“他(她、它)意味着什么?”这个时候,A总是意味着除A以外的其他的什么。这时候A就是一种符号,它所意味的就是A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不是A自己的,而是生活于其中的人所赋予的。研究者就是要理解他们所赋予的A的意义是什么,通过解读这些意义来理解他们的个体的心理、社会互动和文化。就像抽动眼皮这个动作,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他的眼皮在抽动,但我们并不就此停住思考,而是继续深思,他眼皮抽动说明了什么,意味着什么?是眼睛里有东西,还是做出某个示意动作,还是模仿另一个人,还是在练习这个动作……。这一动作已经不仅是这个动作本身,还有社会、文化对这个动作赋予的公共意义,人们根据这个赋义来理解这一动作,同时理解动作人的心理过程。而这就是文化的解释。
第四,文化由谁解释。文化、意义对处于某个场中的人来说,可能已将其自然化(成为第二自然)而失去了对它的敏感,但也可能更清晰它的微妙之意,而处于场之外的研究者也许更有理解这种符号的敏感性,亦有可能不能清晰、深入地感受到其精妙之意,故而,这可能是文化人类学“田野”(进入)研究的两难之处。这就需要不仅仅研究者有研究的声音,还需要被研究者(暂且这样表述)自己的声音,不是一种声音代替另一种声音,而是在这种声音的融合、碰撞中更深切地理解他者、理解自己,感受人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与世界的精彩。
可能整个过程给人的感觉是这不是科学研究,不是实证研究。格尔兹已经明确说明“主观性是任何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研究的现象”。[2]P785这种主观性不是指与客观性相对立的那种主观臆造,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主观“意向性”。现象的本质就是意向性。任何的研究(不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学科研究都是研究者——人在做)都是带有研究者的意向性。就中国的文化来说,并没有割裂自然与人的关系,本身就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状态,是天人合一的状态。而西方自然科学虽说研究对象是自然,是客体,但是谁在解读客体?是人。而任何的研究其最终的关注点还是人,是对人的理解(人是人的研究主体和客体,是主客体同一)。特别是对文化的研究,虽然我们面对的是语言、宗教、仪式,但最根本的落脚点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文化的解释》正是通过将文化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在宗教领域中进行解释的著作。
(二 )《文化的解释》——文化概念对人的概念的影响
1.让他独处一会儿吧
让他独处一会儿吧
“让他独处一会儿吧,
你就会看到他低下头来
沉思,沉思,
凝视着某个碎屑,
某种石头,某种普通植物,
再普通不过的事物,
仿佛它就是线索。
从对真实无华的沉思
抬起烦恼不安的眼睛,
偷偷摸摸地、沮丧地、不满地。”[3]P62
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对罗伯特·洛厄尔写的“让他独处一会儿吧”的理解是“人类学家俯视着碎屑、石头和普通植物,也在沉思着那真实无华的东西,从中短暂地、局促不安地瞥见(或他自以为瞥见)自己那烦恼多变的形象。”[3]P62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读出格尔兹对文化、对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研究的主题的一个基本轮廓。碎屑、石头、植物这些朴实、平常与普遍的事物其实都蕴含着某种值得沉思的文化意义,是在某种文化中沉淀下来的独特的意义,而对这些符号意义的追踪却是如此令人局促不安,因为文化是多元的,人本身又是多么奇怪和多样的存在,而“我”(研究者)也是那样的复杂。可就是这样的几句话似乎就将那种“局促不安”、“烦恼多变”埋没了,我们还是需要在一条通向可怕的复杂性之路上走一遭,认识文化、文化概念对人的观念的影响。
2.几种文化概念
首先要区分文化与文化概念的理解。一般讲来,文化概念是将文化作为一个对象(如果可以这样称谓的话)进行研究,文化即是一种存在。这样文化概念因为有不同的研究方式而有了对文化这种存在的理解,而不同的文化概念又对人有了不同的认识。文中提到几种对文化进行研究的概念:地层学、“人类同见”、类型学。
地层学的基本预设是将人看作是分层的合成物,是生物、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之间关系的分层。这种地层学的特点是每一个分层都有自足的对人的理论解释;基础层支撑着上面的那个层面;某个层面的解释可以在这下面的层面中找到化约的解释。
“人类同见”相信人有普遍的、共同的东西(这个是必然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文化某些方面的独特性是一种偶然,是可以通过“普遍性理论的剪裁”的。它可能的走向是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折中,一种是走向普遍的共性的文化概念。
类型学“淹没了活生生的细节,使之成为僵死的模式:我们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存在,即大写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牺牲了我们实际遇到的经验的存在,即小写的人。”[3]59类型学方法是将人看作种的存在,而忽视了个体的人的独特性与特殊性;同时也忽视了群体之间的差异。个性成了一个古怪的、偶然的、变态的东西。
从以上三种文化概念的研究中,我们既能看出其价值也能发现其各自的荒谬之处。地层学给我们呈现了人存在的现实与可能的将来:人是有生物基础,人有自己的心理动力学的过程,生活于现实社会生活中,这些都是非文化的因素;人还生活于文化中。但人岂是如此的层次的存在!当爪哇人说“成为人类就是要成为爪哇人”时,你的生物基础是不算数的。但当你是爪哇人时,你的行为、心理,乃至神经系统的工作都会有爪哇人的特点。我们在其中更看到因素与因素,层面与层面之间的互动、制约、影响。人类学者在实地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寻求人类之间的共性,“人类同见”。这可能是理解的基础,是交流的条件,但从本质上说,“人的属性是多样性”,文化是多元的。并“不是说不存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例外的是,他是一种极端多样性的动物),也不是说文化的研究对解释这种普遍性没有任何贡献。”[3]47而是要充分正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普遍性不是通过对文化普遍原则的培根式的调查来发现的,不是通过对世界各民族的民意测验,以寻求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人类同见’。”[3]P47类型学看到的是人的“种”性,而忽视了人的“个”性,独特性,群体的独特性。类型学更多地是在作“化约”,将某个群体或是个人置于某个模型之中,个人只是这个模型的“镜像”,甚至是“畸象”。就像在我们的教育中,把人进行“优秀学生”与非优秀学生的区分。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算是优秀,什么标准是优秀的时候就给学生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进行定位与评价。试想,哪个人真的是属于某个类型?世间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我们在思考人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一个人存在的具体情境,将其抽离其存在的“背景”进行归类,而归类的“类”其实是已经形成的评价的标准。这样,人类学研究并不是“他人的眼光”的研究,而是以我的眼光、价值去套你的文化。我们忘记了文化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现实”。
3.文化概念对人的概念的影响
人总是在某种文化中成长起来,带有那种文化特征的人。“我们坚信,不被特定地区的风俗改变的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也永远不曾存在过,最重要的是,事情的本质也不可能存在。……他们永远在演戏。”[3]P42演戏需要背景,需要舞台,需要戏服,需要角色和他者,需要语言……所有这些都不是自己创设的,而是文化。“文化是一套控制机制,用以控制行为;人类恰恰是极端依赖这种超遗传的、身体以外的控制机制和这种文化程序来指导自身行为的动物”[3]P52
且不论这种控制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之意,还是管理学上的含义,将其放置在“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的即深描的脉络”中来考察可能更合适。从一个人的发生、成长、死亡的过程看,他人生中经历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特殊的节点,总是要带有这种“控制”(控制也是一种表演)。在哪里出生,出生的各种象征仪式,成年礼,死亡的殡葬等都是超越遗传性质的文化的结果。这种外化的行为表现的“控制机制”是源于人类思想是社会的和文化的。社会原意是几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互动和在相应的语境、空间中的展开。社会互动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一个图式,打破一个图式的时候就是交往不成功或是无效的时候。人与人、个人行为都是在这个结构中展开、互动。而人与人的互动表现是行为,而行为背后是一个人的心理。心理没有独立的存在。人格、自我、个性从构成上来说,就有社会文化存在于其中。一个人的心智也在文化之中得以成长。社会互动与心理交流的有效性又缘于文化模式——符号的有意义组织系统的指导。石头意味着什么,碎屑意味着什么,出生意味着什么……这些意味着的所指并不是个人赋义的,而是一个群体,处于同一时空的人共同赋予的。当一种赋义在时空的穿梭中沉淀下来的时候,就成为一种仪式、一种象征,一种“控制机制”。每一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处于这个机制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不存在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人。“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
“如果我们想要直面人性的话,我们就必须关注细节,抛弃误导的标签、形而上学的类型和空洞的相似性,紧紧把握住各种文化以及每个文化中不同种类的个人。”[3]P61这可能是更深度的个体深描,而这条道路要通向可怕的复杂性。
三、《文化的解释》的启示与评议
《文化的解释》这部格尔兹的重要研究文集,将“具体的‘田野’和抽象的理论如此恰到好处地糅合在一起,每一段议论都有实在的根据,每一段描述都有深远的寓意,这实在是方家所为。书斋理论家和田野实践者都会在《文化的解释》中体会文化,跟随作者去阐释文化,运用文化,想象文化。”[3]P522不论是对宗教、意识形态还是对巴厘岛上的斗鸡,都是一种“文化表演”,在文化中,通过文化意义来表达。这种表达得益于格尔兹文化阐释的“深描”。
(一 )“深”与“浅”的理解
浅描是行为本身(抽动眼皮),深描则是行为后面的意味(传递信息、模仿、恶作剧等)。格尔兹所说的深描正是深度挖掘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文化意义具有意义结构,意义层次。这些意义说明文化是共有的,是成熟的。文化人类学者就是研究、考察本已成熟的文化如何塑造、改变、成就了人、群体、社会。
将意义结构呈现出来的过程就是一种深描。深描,不是对行为、话语的描述,而是对行为、语言的阐释。深描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解释,而要达到解释的理解就需要深描而不是浅描。从这个角度讲,浅描仅仅是描写,而深描是在描写中的解释。深描是对文化的解释。文化的解释不是对文化进行解释,而是对文化的解释的解释(say something of something)。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而且是他者的意义(对人类学研究来说),人类学者对文化的解释,其实是对其进行再解释。
虽说文化是观念性的,但它并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虽然它是非物质性的,但也并非是超自然的存在。文化总是渗透到社会互动中,自我的构成中。深描、解释就是进入到文化的非观念、物质的层面,在人际互动中,心智过程中的考察。
在深度描写中,文化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形成、产生的脉络。一种社会现象比如说斗鸡,法律禁止而依然盛行,特别是在特殊的场合(建造庙宇等)它本身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活动,一种人们非日常化的精心准备的活动,其中的深意足以将巴厘岛的文化揭露无遗。小事件之所以说明大问题,是因为它们是被(文化)这样设计的:通过斗鸡这一男性活动,男人、动物性、群体归属、血、赌博、面子、地位、道德、声誉都显现出来。“它是巴厘岛人对自己心理经验的解读,是一个他们讲给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3]P506
(二 )文化人类学研究价值
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面对当今社会的种种全球化问题,文化多元问题,人与人之间需要的可能是基本的了解、理解和对话。伽德默尔说解释不是为了自我理解,而是为了对话、沟通。在当今这个现实背景下,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可能更需要做到彼此倾听、听到别人的声音。“人类学的目的在于扩大人类话语的空间。”[3]P16对话不是为了改变别人,对话的过程不仅仅是为了达成一定的共识(尽管有时达成共识是必需的),对话的前提本身就需要多元,对话的过程可能是产生更多问题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沟通的过程。文化人类学正是给我们呈现了人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人的复杂。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能仅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他人,不能以所谓的进步观去审视一个文化,也不能以客位的方式解读一种文化。每一种文化总是有其历史的积淀,也有滋养的土壤,这些人为与自然交融的结果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文化只能尊重,只能倾听,只能理解。
在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度理解、解释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有清醒的批判和反思我们自身文化的精神。这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不断地认识我们文化的特点、并对自身文化的局限展开深刻的批判性反思,从而寻找到新的生长点的需要。
[1]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英]彼得·沃森.20 世纪思想史[M].朱进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