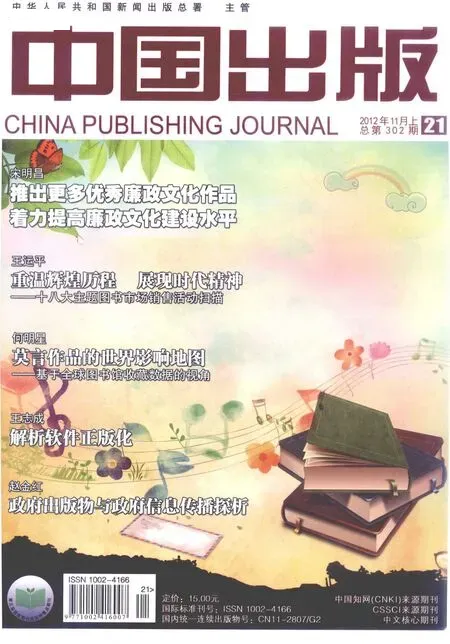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的特征分析——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文/朱鸿军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者非常偏爱的制度分析理论工具,它从时间的维度,剖析制度的历史演变进程,既有助于了解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及存在的不足,又能更清晰地把脉制度的发展方向。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谁,制度变迁的动因何在,制度变迁的模式,制度变迁的绩效,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如何,构成了该理论五大方面内容。本文将分别从这五大方面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的特征。
一、制度变迁主体分析
“任何制度都由人设计或选择,即使非正式规则,也由人加以选择并内化到人们的意识中。制度变迁无非是人否定、扬弃某些规则,制订或选择新的规则,因此制度变迁总是有主体的”。[1]在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看来,只要是有意识地推动制度变迁或者对制度变迁实施影响的单位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它可以是政府、一个阶级、一个企业或别的组织,也可以是一个自愿组成的、或紧密或松散的团体,当然也可以是个人。[2]单位是否会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关键在于制度变迁能否让其获益,且获益的大小也决定着其推动制度变迁动力的强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那么谁是最直接获益者?很显然是权利人。正因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和20世纪80年代,面对大量作品的版权被侵害,一批学者、文人,如冯友兰、巴金、王世襄、蒋子龙等作品权利人,首先成为要求版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最坚定支持者,竭力为版权的立法工作鼓与呼。
其次,我国版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另一直接获益者是与我国进行贸易往来的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贸易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份额。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对外出口仅有10%依赖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到了90年代末期,则有近50%的对外出口额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3]因此,为实现本国知识产权相关企业从贸易对象国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督促贸易对象国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最后,正是在内外两大制度变迁主体的推动下,作为制度变迁实施者的政府成为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的另一制度变迁主体。从下文的制度变迁动因和制度变迁模式分析中还可发现,政府还是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中的最主要制度变迁主体。
二、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按照一般理论,制度变迁的主体都是财富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者,他们从事制度创新与变迁都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无论政府、团体、个人,其制度变迁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如此”。[4]上文可知,国内权利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是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的三大制度变迁主体,前两者要求完善版权法律制度的动机非常明了:只有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完善了,自身的利益才能最大化。那对我国政府而言完善版权法律制度益处何在?
首先,完善版权法律制度能满足国内民众的制度需求。1988年11月2日,国家版权局上呈给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批示的《关于加强版权法起草工作的报告》中,这样陈述版权法起草工作的理由:“目前的情况是,各方面对制订版权法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民法、继承法都对版权作了相应规定,使依法保护版权不能再拖延。国内各种版权纠纷不断发生,报刊常有报道,引起社会各方关注。法院受理版权案件日益增多,急需版权法作为审理依据。行政机关仅靠行政法规处理版权纠纷,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广大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和使用者迫切呼唤版权法,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并且作为处理彼此关系的规范……总之,国内国外,方方面面,都清楚表明,我国版权立法已刻不容缓。”[5]
其次,完善版权法律制度有助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最主要目的,简单说来,即实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正常经济贸易,将先进的技术、设备、经验和大量的资金引进来,将国内有竞争力的产品输出去。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与西方发达国家展开正常的经济贸易,就必须对国内游戏规则进行国际化改造,实现本国游戏规则与国际游戏规则的接轨。
然而,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一部世界近现代国际贸易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霸权史:世界主要经济组织由西方发达国家把持,世界绝大多数国际贸易规则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游戏规则的国际接轨,某种程度上讲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而在诸多的游戏规则中,已有几百年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拿知识产权保护说事,已成为他们惯用的手段。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国际政策方面,始终把知识产权保护与它的对外贸易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美国主要是凭借其国内法、综合贸易法的特别301条款和关联法的337条款,每年把全球的贸易伙伴进行分类排队,凡是不保护、不完全保护、不充分保护的贸易伙伴,分别列为重点国家、重点观察国家和观察国家”。[6]可以这样说,知识产权保护成了美国“敲打”发展中国家的一根大棒,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遭到过它的敲打,如“泰国版权实施案”“泰国药品案”“印度知识产权案”“巴西知识产权案”等。

国际力量的推动与中国版权保护法律制度的调整
知识产权保护,同样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经贸往来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筹码。在中国国门打开的30多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对于还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中国要求过于苛刻。他们忘记了自己在知识产权保护道路上,也曾经历了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缓慢变迁的过程。[7]面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没有生硬对抗,而是尽可能据理力争更多利益的同时,做出适当的让步。这些适当的让步,虽短期内会损失部分利益,会让知识产权制度看似与实际国情相脱节,但能为国家的对外开放大局创造有利条件,且从另一角度来看,也能借机加快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步伐,相对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正是现代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具备的制度保障。如此一来,中国政府实际上将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国际压力变为了国际推动力。从上表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版权法律制度每次重大调整也都与国际推动力紧密相连。
三、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制度主体差异为标准将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种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之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10]从变迁的程序来看,诱致性制度变迁先有基层行为人的制度需求,然后再有政府的制度(法律)供给;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先有政府的制度(法律)供给,然后再有民众的制度需求。
这两种制度变迁模式各有优势。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是根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如果它能克服外部效果和‘搭便车’之类的问题,那么它在制度变迁中将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之一”[11];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它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它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12]。一般而言,前者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概率比较多,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与分散型决策体制相适应,与西方传统的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传统比较适应。后者在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概率较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借用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和经过历史检验的制度安排,充分利用这种“后发优势”,积极主动地进行制度变迁,最大程度地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实现“跨越式”发展。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模式的划分,可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模式总体上应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这30多年我国版权保护法律制度变迁的程序来看,绝大部分情况下,总是先有政府颁布新的制度(版权法),再通过政府种种手段的引导,最后才慢慢有民众对新制度(版权法)的接收和运用。当然,由政府主导供给的新版权法律制度,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制订中就没有民众的声音,就没有考虑到民众的制度需求,而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新制度需求的民众的声音过弱(如仅是少部分民众),不足以促使新制度(版权法)的诞生,而政府则从更全面、更长远、更理性的角度促成了看似与广大民众需求相脱节的新制度(版权法)的诞生。
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优点是,实现了我国版权立法上的跨越式发展,仅用30年的时间便与国际接轨;而且从当前实现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迫切需要完善的版权保护制度的现实形势来看,这种“跨越式”发展,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是版权立法领域的“大跃进”,而是更有前瞻性、更有预见性的制度设计。
当然,这种制度变迁模式的不足也很明显。由于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发展得太快,民众的版权保护意识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很难跟上其变迁的速度,这很容易使法律制度实施的成本增加和法律实施机制的“软化”,从而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影响法律的权威。
四、制度变迁绩效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版权法律制度的绩效如何呢?评价制度变迁的绩效如何,最主要标准是看对制度的设计者而言,是否达到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对我国政府而言,实施版权法律制度变迁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与国际接轨,为我国对外开放铺平道路;二是促进我国版权产业的发展。首先,现今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已很好地与国际接轨,“在版权保护领域方面,中国与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没有法律障碍。”[13]其次,我国版权法律制度的健全带来了版权产业飞速发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调研”结果显示,2009年我国版权相关产业行业增加值为22297.98亿元人民币,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6.55%,对就业贡献率为6.8%,两数字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6%和5.8%。纵向看,2004年,我国版权相关产业行业增加值仅为7884.18亿元人民币,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4.94%。[14]因此,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版权法律制度的绩效同样值得肯定。
五、制度变迁发展方向分析
(一)国际化
国际化是当今世界主流国家版权法律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18世纪初至19世纪后期,版权法还基本上属于国内法。19世纪中后期《巴黎公约》与《伯尔尼公约》等知识产权公约的签订,将知识产权保护从国内导向国际,开创了版权法律制度国际化时代。[15]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颁布,更是逐步把版权法律制度的国际化程度推向极致,即一体化,截至2006年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有134个成员国,占全世界195个主权国数量的68.7%,这意味着全世界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得遵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国际化,同样是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发展的趋势。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在他的南巡过程中,就多次提到知识产权问题,并指出在这方面要向国际标准看齐。[16]目前,我国已加入世界所有主要知识产权组织,加入国际组织就得遵守国际游戏规则。这意味着,今后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如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际因素,国际版权法律规则发生了变化,国内版权法律规则也应相应做出调整。
(二)市场化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版权产业的发展规模却与经济大国的地位严重不相符。2009年我国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虽已达6.55%,但美国已达33%。[17]从版权产品的影响力来看,“我们仍然缺乏有影响力、有竞争力的精品力作”[18]。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士这样说道,“中国出口电视机,我们出口思想”。虽然观点偏颇,但也提醒我们,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就必须实现以版权产业为基础资源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如何才能实现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解放思想,推进文化事业的体制改革,走市场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文化事业的市场化决定着我国版权法律制度必须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三)加强化
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第一要素的崭新时代,知识产权一跃从财产权领域的“配角”成为“主角”。对此,达沃豪斯指出,就知识产权的大部分历史而言,知识产权在我们广阔的知识传统里仅仅是一个附带事件。然而,当社会变迁为信息社会之时,这种情况慢慢在变。进一步说,社会和政治的关系,还有权利的有意义实行,正逐渐关键性地依赖于信息的流动。[19]知识产权在知识经济社会如此重要的地位,自然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对其高度重视。对于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我国而言,知识产权保护被重视的程度也越来越高。2006年4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成果展览时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尊重知识、鼓励创新、保护生产力”[20],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立场;2008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更是将保护知识产权提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加以推进;今年,《著作权法》的修改草案中也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可以想见,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断强化,必将成为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主导取向。
注释:
[1]程恩富,胡乐明主编.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194
[2]程恩富,胡乐明主编.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193
[3]ATOLL.R.Policy and Proper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R) WIP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P and Knowledge- Based Economy.Beijing, October 13-15, 1999.
[4]程恩富,胡乐明主编.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194~195
[5]国家版权局.关于加快版权法起草工作的报告[R].[(88)权字第48号]
[6]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政策科学分析[EB/OL].“民商法律网”系列讲座现场实录第308期,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750
[7]19世纪的时候每当欧洲的游轮到达了旧金山和波士顿的港口,美国的出版商就驾着马车高速地跑到港口抢购最新欧洲出版的书籍,堂而皇之地进行印刷,然后在美国的书店销售。迪金斯曾经痛心疾首地批评美国的这种海盗行为,当欧洲1886年签订了一个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的时候,美国人不参加,他们认为,这种保护水平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后来一直到1992年,由美国牵头搞了一个较低水平的《世界版权公约》,美国一直到1988年才宣布参加《伯尔尼公约》。——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政策科学分析[EB/OL].“民商法律网”系列讲座现场实录第308期,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750
[8]备忘录包括:中国有关部门将向国务院提交一份考虑了国际惯例的著作权法草案,国务院将在1989年年底完成该草案的审议,并提交全国人大,中方将尽最大努力,促进全国人大尽快审议该草案。在著作权法中,将计算机软件作为作品进行保护,除非另有规定,著作权法有关文字作品的所有规定都将适用于计算机软件。中方表示,正在起草的著作权法实施细则,包括计算机软件条例,将考虑国际上的观点和看法。著作权法通过后,中国政府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将版权保护及于起源于各个国家的作品,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推进加入世界公约的进程,中国政府将在其权力范围内实施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法律,包括认真努力地教育官员和大众,使之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美国政府承诺当年不把中国政府确定为“重点国家”。——李雨峰著.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74
[9]在该备忘录中,我国政府同意在1992年年底以前加入《伯尔尼公约》,在1993年1月1日前加入《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
[10]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84
[11][12]卢现祥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118
[13]赖名芳.柳斌杰:中国与国际版权交流无法律障碍[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3-01
[14]刘仁,姜旭.版权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N].中国知识产权报,2012-07-03
[15]张梅著.中国版权保护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75
[16]李明山,常青等著.中国当代版权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258
[17][18]冯文礼.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做客央视谈新闻出版改革[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4-20
[19]Peter Draho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9), Introdution, at Xxiii.
[20]张旭东,赵雪花.温家宝总理参观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成果展侧记[N].中国知识产权报,2006-04-26
--评《版权法之困境与出路:以文化多样性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