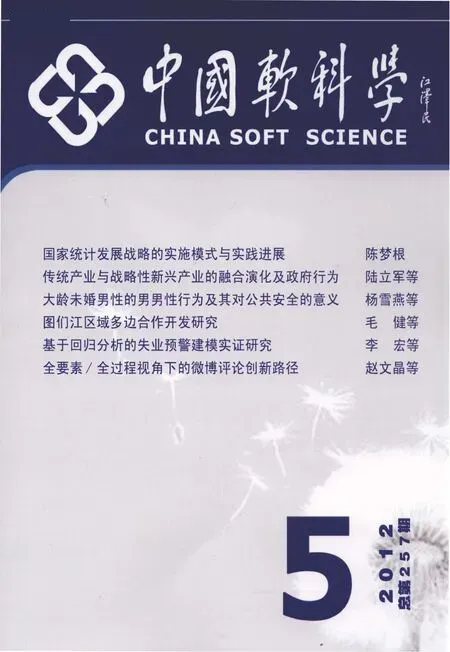市场化程度对自主创新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Cost-Malmquist指数的高技术产业行业面板数据分析
成力为,孙 玮
(1.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连116024;2.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一、引言
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对现有(既定)的生产要素,市场机制的作用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1]。从这一角度方军雄(2006,2007)利用1997-2003年我国工业的统计数据研究市场化进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资本配置的效率有所改善[2-3]。成力为等(2009)利用2001-2006年我国制造业月度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内部市场化和引进外资对中国制造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出产业内部市场化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正向影响[4-5]。但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不包含创新的理论缺陷[1],对市场机制在创造新的生产要素或变革生产要素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围绕着市场力量与创新激励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显示出二者呈正向关系与负向关系的结论都存在。如Gayle以1976-1995年间美国4800多家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市场集中度对技术创新的关系得出显著正向影响[6];Blundell等利用英国制造业数据发现垄断企业在对行业状况的深入了解上存在优势,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成功概率较高[7];朱有为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13个细分行业研发效率的分析中发现市场结构与产业研发效率也具有正相关关系[8]。而垄断使垄断企业以限价方式阻止新企业进入、缺乏创新动力、进入壁垒高则带来创新的低效率[9-10];冯根福等对中国35个工业行业企业资产规模与研发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为负相关关系[11]。但这些市场控制力与创新活动关系的研究隐含一个重要假设——在资源配置的初始阶段要素市场是完善的、存在合理的定价机制和流动机制。因此,在自主创新效率的研究上仅仅注重创新生产过程效率的测算和评价,将自主创新效率等同于研发的生产效率,忽略了市场不完全竞争和要素配置受限使得资本、劳动无法完全按照其边际产出获得报酬所产生的效率损失,即没有考虑到市场机制不完全对产业创新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许多制度特征都可能导致市场的不完全。例如内外开放的不均衡(不同产业、地区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和引进FDI在时间上存在差异)、不对称性(对外资企业开放程度与对民营企业开放程度)特征所产生的不同所有制企业社会经济地位不对等;金融等要素市场发育的不完善、被认为普遍存在的地区市场分割、政府对行业政策性倾斜保护等。这些转轨过程中制度特征所引发的市场不完全改变了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从而影响了创新资源在产业范围内的配置。根据我们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效率主要受制于低配置效率、自主创新研发效率主要受制于低规模效率,而且与要素市场不完全密切相关[13]。严成樑等(2010)在经济增长框架内考察研发投资的回报率也认为我国知识生产中没有规模效应[12]。进一步要考虑的问题是:这种自主创新资源低配置效率的特征是什么?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市场不完全对自主创新资源低配置效率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恰恰是解决目前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内在激励问题的关键。全文将依照如下结构展开研究:首先对创新资源配置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进行阐述,从创新结构红利的成本视角将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以下简称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分解为分配效率(企业家要素组合的效率)和价格因素(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探寻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特征;其次,从行业层面构建市场不完全特征,即市场化程度变量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分解影响的面板数据模型,并对模型进行计量;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二、市场机制决定的自主创新资源配置及效率的分解
(一)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分解的依据
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是好的,同时也是成本昂贵的。微观主体创新的直接动机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希望用一般资源替代更稀缺的资源以获得超额的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自主创新效率从来就面临着“技术最优”和“成本最小”两个维度。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微观主体而言,采用何种技术、以什么样的方式采用技术,完全取决于企业家对市场的判断和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权衡。在企业内部多个利益相关者(股东、雇员、研发人员和中间管理者)中,创新和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企业家推动的,企业家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优势在配置资源的组织优势和信息优势上,合理的配置生产要素、实现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是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也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企业家对自主创新的推动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参与约束,即企业家推动自主创新所获得的收益应不低于其放弃自主创新所获的收益;二是激励相容约束,即企业家推动自主创新不仅收益大于其采取其他行动的收益,而且委托人的收益也可以得到有效保证,会符合其收益最大化的预期目标[14]。一方面,创新资源配置即创造新的生产要素配置或变革生产要素新组合较既定的生产要素配置在资源配置的初始阶段相同,即二者都面临在组合生产要素中的“技术最优”和“成本最小”二维评价,如果要素市场不健全,缺乏合理的定价机制和要素流动机制,企业家基于“成本最小”维度就可能过度使用低价要素(廉价资源、劳动力)而不进行创新投入。所以,从宏观角度看,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以节省物质资源、环境资源和创造优质的人力资本为特征,其基本前提是这些资源的合理定价。另一方面,创新资源配置较既定的生产要素配置不同:第一,在企业家做出配置决定后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从新思想产生——中试成果——形成新技术——形成新产品的过程中,越往前端面临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就越大。越是核心技术的创新,失败的可能性越大;第二,从企业家开始将资源配置到新技术开发、特别是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到最后创造出新的生产要素、实现生产条件的“新组合”需要经过漫长的研发周期,每一个研发阶段都可能面临失败。所以,自主创新需要市场制度提供创新的动力和压力,也需要一定范围的垄断对创新者激励以提升企业家对要素组合的能力。但问题是处于转轨过程中的我国大企业,其垄断地位的确立不是内生于市场竞争、靠先前不断创新提高效率的结果,在垄断地位形成后要素流动限制(政府投资审批和市场准入)又消除了其他企业进入市场的竞争压力,自然不会把资源组合到根本性核心技术的创新上,表现为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这些在高技术产业尤为突出,因为,作为知识和资本双密集的行业,高技术产业所涵盖的领域多为技术进步非常迅速的领域,技术机会更多,创新速度更快,对关键性核心技术创新依赖更大、创新成果独占性也更强、巨大的“沉没成本”和“锁定效应”,使得高技术产业在技术进步上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特征,表现为新技术和原有技术之间更强的互补性和逐步替代性,因此对创新过程中的技术选择、研发生产对市场的依赖比一般产业大的多。
(二)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变化的分解
1.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变化的分解思路
在上小节思想的指导下,本文在Nikolaos Maniadakis和 Emmanuel Thanassoulis所提出的成本Malmquist指数法(简称 CM 指数)基础上[15],结合Malmquist指数计算思路,将创新配置效率变化分解为价格影响变化和要素组合能力变化两部分。具体过程为,一方面,首先将自主创新效率变化分解为成本追赶效应OEC和包含技术进步的成本边界变化CTC两部分,接着,将成本追赶效应分解为技术追赶Tch和要素组合能力追赶Aec两部分,将成本边界变化分解为技术边界Tech和价格影响变化Pe。

另一方面,考虑到价格因素以后的自主创新效率变化还可以被分解为生产性Malmquist指数(研发效率变化)Malmquist和配置效率变化Aech两部分,其中生产Malmquist指数还可以被分解为技术追赶Tch和技术边界Tech的乘积。由此,得到公式(2):

对比公式(1)和(2)可得出配置效率变化的分解:

公式(3)右侧第一项的具体计算表达式为:

其中 yt为产出向量,ωt为投入价格,xt为投入向量,P(yt)为投入集,可以看出 Ct(yt,ωt)表示在产出、投入价格和生产可能集给定条件下的最小成本,()为Malmqui指数法中的定向距离函数。可以看出分配效率Aec的含义为t期与t+1期之间要素组合能力的变化,即已知每期投入价格后,投入组合与最优投入组合之间的差距变化。
公式(3)右侧第二项的具体计算表达式为:

可以看出,Pe反映投入价格相对变动对成本边界变动产生的影响,即在特定产出下,投入价格相对变动对最小成本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被称为价格前沿移动。由于在理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的市场价格可以完全反映它的边际价值,因此价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由分配效率变动和价格前沿移动的表达式可知,分配效率变化反映了要素配置能力对特定条件下最优配置能力的追赶,价格前沿移动反映了最优配置水平的变化,即要素定价合理程度的变化。
2.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变化的实证分解结果
本文采用DEA的扩展模型Cost-Malmquist指数法,以行业R&D研发存量、R&D人员全时当量为投入变量,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申请量为产出变量,以R&D新增存量变动与当年存量之比表示R&D存量价格,以科研经费中劳务支出占科研总经费支出的比例替代表示R&D人员价格;以新产品销售收入在产品总产值中占比表示新产品销售收入价格,以当年专利申请量占专利拥有量的比值近似表示专利的价格,估算出高技术产业整体、内资和外资部门1996-2008年的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增长率(Aech)、分配效率变化率(Aec)和价格前沿变化率(Pe)(其平均值见表1,由于本文是从成本角度构建的创新效率模型,其效率指标Aech、Aec、Pe大于1表示效率变化率下降,反之上升)。把每年的上述创新效率值定义为短期创新效率,把累计(各年创新效率值的乘积)定义为长期的创新效率。
本文选择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创新的产出变量主要依据是,产业的技术创新在本质上具有生产性特征,而新产品销售收入是研发——生产性创新的结果。选择专利申请作为产出变量的主要依据是相对于授权量,专利申请更能直观反映微观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而专利授权更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且滞后性更为突出。
由表1可知,除外资外,高技术产业整体和内资部门自主创新配置能力对成本的作用是负的,即所谓的创新“结构红利”在这两个部门并不存在①结构红利起源于Lewis的二元经济古典模型,正式术语由Timmer和Szirmai提出,是指要素不断的从低生产率行业配置到高生产率行业对总体生产率增长所产生的正向影响,反应行业结构调整和改革对生产率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结构调整和改革对效率增长产生的影响。(见:张军,陈诗一,Gary H.Jefferson.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经济研究,2009(7):4-20.)本文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构红利”不存在是指由于要素定价不合理,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资源并没有由低效行业往高效行业配置的现象。。这意味着样本期间在高技术产业所进行的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仅仅促进了外资部门的创新效率的提升,降低了外资创新的成本,但却以高技术产业整体和内资部门创新成本的提升和效率降低为代价。更进一步分析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变化的路径发现,无论是高技术产业整体还是内资部门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增长率的下降(Aech>1)主要来源于扭曲要素价格的成本效应(Pe>1)。即不考虑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因素,在样本期间内,我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和内资部门企业家组合科技资源效率的提高(Aec<1)是比较快的,企业家组合科技资源的效率的提高,促进了自主创新配置效率(Aech)提高。这一方面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我国高科技产业企业家组合科技资源能力的基础比较差;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产品市场的开放和“干中学”,我国高科技产业企业家的核心能力得到了提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内资部门自主创新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受到不合理要素定价机制的制约,其扭曲价格的成本效应越来越大(Pe>1)。由于资源和劳动力定价过低,高科技产业的企业家理性的选择了过度使用这些低价资源,从而减少核心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因为,工资是研发融资的来源,工资又与生产力成正比,所以技术越落后,工资收入越低,研发的融资成本也就越高,企业家越不愿进行研发[16]),导致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增长率下降而具有明显的“水平效应”,无法分享自主创新带来的“结构红利”。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配置的外资,受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其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增长率总体上上升的(Aech=0.993<1)。其变化的路径表现为价格前沿的推进(Pe=0.914<1),即外资一方面利用我国的低价物资资源获得绝对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利用质优价廉人力资本(同水平研发人员较国外工资低)获得相对成本优势。尽管受内资部门的竞争和外资部门之间的竞争的影响,
外资企业企业家组合科技资源的效率增长趋于下降(Aec>1),但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增长率总体上是上升的。

表1 1996-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体、内资与外资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增长及路径均值
三、转轨过程中市场不完全特征对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采用了对内(非国有经济)开放和对外(引进FDI)开放两种不同的市场导入机制,由于对内开放的不均衡(不同产业、地区引进市场机制存在时间差异;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改革不同步)、内外开放不对称(对外资企业开放与对民营企业开放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市场不完全特征,市场化程度对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点在高技术产业尤为突出,为了反映转轨过程中市场化程度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影响,本文建立市场不完全特征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影响的面板数据模型为: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后续模型中i,t含义相同);左侧因变量P分别表示相关行业和年份的整体或内资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变量: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增长率(Aech)、分配能力变化率(Aec)、价格前沿变化率(pe)。包括短期的自主创新变量(每年Aech、Aec和Pe)和长期累计自主创新效率变量(LAech、Laec、LPe,分别用 Aech、Aec和Pe各自的连乘积计算)(后续模型变量定义相同)。Pi,t-1为前一期的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变量。Zit为市场化程度变量。
(二)市场化特征变量的选取和定义
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16],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3个方面分析市场化特征变量,具体有:
1.政府对行业创新干预度
市场化改革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由政府分配经济资源逐步转向由市场分配资源,政府对行业创新干预度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越完善。而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主要由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变化反映,为此,本文分别选取以下指标反应政府对行业的创新干预度。
利税占比TP:表示t年i行业企业利税总额占其总产值的比例,
政府资助创新力度GG:表示t年i行业政府对国有部门科技经费资助占对内资科技经费资助的比例,GG值越大表明政府对国有部门的扶持力度越大,政府干预度也越高。
2.行业开放程度
黄亚生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包括了内部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向其他国家的外部开放两个内容[17]。其中内部的经济结构改革反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由于非国有部门是内资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称之为对内开放;外部开放反映为引进外资的程度。简言之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在对内和对外开放中进行的,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发育越完善。本文用以下两项基础指标进行衡量: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Non:表示t年i行业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内资总产值的比例表示,Non值越大表示该行业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好,内部开放度也就越高。
行业创新对外开放程度FDI:表示t年i行业FDI产值占整个行业总产值的比例,FDI值越大表明行业创新对外开放程度越大。
3.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要素市场是行业产品市场发展的基础。然而,相比于产品市场,中国要素市场的发育明显滞后,还存在较为明显的非市场强制力量。主要表现金融市场对行业创新要素的信贷配给程度和中介组织的不完善。本文用以下基础指标进行衡量:
金融与信贷市场的发育FM:在市场合理的调节下,不同所有指企业使用的银行贷款比例应与其产出贡献相一致。信贷资金分配结构与产出结构偏离越大,越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即金融信贷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考虑到本文衡量的是创新,因此此处用表示t年i行业科技经费筹集额中金融机构信贷分配结构与创新产出结构的关联系数FM反映。FM值越大表明金融与信贷市场化程度也越高。
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IM:知识产权保护的状况是反映技术市场发育的重要指标。相对于专利授权情况,申请量更能反映企业在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进而反映技术市场的活跃度。为此本文使用以下指标反映这方面的状况:t年i行业专利申请量与R&D从业人员的比重,比率越大表明IM创新服务中介越发达,技术市场发育越完善①其他如劳动力流动性等指标由于数据不全,本文不予以考量。。
(三)数据来源和计量方法
除特殊说明外,本文的计算数据均源于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2-2008)中我国17个四位码高技术产业大中型企业的统计数据,包括:1-化学药品制造、2-中药材及中成药加工、3-生物制品制造、4-飞机制造、5-航天器制造、6-通信设备制造、7-雷达及配套设备、8-广播电视设备制造、9-电子器件制造、10-电子元件制造、11-家用视听设备制造、12-其它电子设备制造、13-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14-电子及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15-办公设备制造、16-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17-仪器仪表制造。内资的相应指标均由相应的分行业数据减去分行业三资相应指标得到。对R&D投入存量、新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不同物价指数剔除了价格的影响[18]。
为避免因不同行业差异可能造成的截面异方差,本文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同时为解决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引发“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而导致估计偏差的问题,本文采用近年发展起来的能较好地克服内生性问题的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进行估计。具体为:首先以正交离差技术(orthogonal deviation technique)消除截面固定效应,并以White period方式进行截面加权;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效率变量的滞后项为内生变量,市场化程度变量为外生变量。选择Sargan检验验证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此外,为验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还对模型的残差项进行了序列自相关性检验(Arellano和Bond)。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结果说明
表2各种因变量的回归结果都取得了较好的显著度,同时针对GMM的Sargan也表明了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即所选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此外,为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我们还对模型的残差项进行了自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残差表现为明显的一阶自相关和显著的二阶不相关,因此和序列相关检验验证了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以及残差并不存在的自相关性。因此估计结果可信(后续相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成本越小越好,因此对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及其分解的系数需要反向解释,即负向的表示促进,正向的表示抑制。

表2 市场不完全特征对高技术产业整体和内资部门自主创新配置效率影响
由表2可得:(1)政府行业创新干预度对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包括:第一,利税政策。利税占比TP对高技术产业(整体)和内资部门(内资)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相同,均通过政府税收的压力使要素价格逼近边际成本前沿面(市场均衡价,LnPc= -0.093<0,LnLpc= -0.186<0)显著正向影响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税收通过显著降低企业家组合要素的效率(LnAec=0.186>0,LnLaec=0.198>0),显著负向影响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二者的影响均具有长期效应,内资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Aec>0,LAec>0)。第二,政府资助创新力度。政府支持力度GG对高技术产业(整体)与内资部门(内资)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完全不同,它显著正向影响整体长、短期价格前沿变动(要素价格逼近市场均衡价格,LnPc=-0.022>0、Ln-Lpc=-0.017<0)进而对整体长、短期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LnAech、LnLaech)正向影响;显著负向影响内资长、短期价格前沿变动(LnPc=0.470>0,LnLPc=0.733>0),而对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负向影响。这说明如果把外资作为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一部分,不考虑技术的“自主性”和国别属性,政府对行业创新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高技术产业成本边界,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但对内资企业而言,长期政府扶持会使本土企业因获得偏离市场均衡价格的廉价要素而过度使用低价资源影响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政府支持对整体、内资部门企业家组合创新要素效率的提高均无显著影响。
(2)行业的内(非国有经济)、外(FDI)开放程度对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包括:第一,对内开放程度。非国有经济的发展Non对高技术产业(整体)和内资部门(内资)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相同,均通过正向影响价格前沿变动(LnPc、LnLpc)和负向影响企业家组合资源效率提高(LnAec、LnLaec),并由于整体企业家组合资源效率负向影响大于价格前沿变动正向影响导致高技术产业整体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率降低,但对内资部门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对内开放促进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对内资企业价格前沿变动的作用更为显著,其代价是合理价格机制下企业家组合既定资源的效率提升将受到影响,这对外资部门影响更显著。即对内开放形成合理的要素定价机制对内资部门避免过度使用低价资源、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作用更大,也更不利于外资部门的企业家利用中国廉价资源、提高要素组合效率。对于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利于内资部门企业家要素组合效率提升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尽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能会提升某一领域的创新动力,但是由于规模和地位的限制,使得非国有经济的管理者更倾向于家族化和短期获利,进而影响创新资源利用结构调整的重视度和能力[19]。第二,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FDI短期通过正向影响价格前沿变动(LnPc),负向影响企业家组合资源效率的变化率(LnAch),因其价格前沿变动作用大于企业家组合资源效率作用,进而正向影响高技术产业整体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但长期效应不显著;对外开放程度FDI仅仅对内资部门短期企业家组合资源效率变化率正向影响,而其他影响不显著。这说明,较之于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缓解要素价格的扭曲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大,而且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对外开放、引进FDI,对外资部门获得低成本优势、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更大,但对整体和内资部门都没有长期效应。对内、外开放引进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在既定价格下企业家组合资源效率的提高。
(3)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影响。金融与信贷市场的发育程度FM和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IM均通过影响企业家要素组合效率提高和降低成本使价格前沿推进,对高技术产业整体和内资部门的长、短期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金融信贷市场和技术市场越发达,高技术产业整体和内资部门企业家就越能更好地利用技术市场获取新技术,同时利用金融市场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缓解自主创新过程中的技术与资金约束,提高企业家的要素组合能力。另外,技术市场的发展减少新技术的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金融与信贷市场的发展,通过对企业家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事前评估[20],为防止企业家欺骗行为,对投资项目进行监督[21],减少创新项目的风险、降低了研发成本,使投入价格更接近边际成本,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特定的制度环境中,随高技术产业不同行业引进市场机制的时间不同、导入机制不同,市场化程度对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也不同。通过三阶段Cost-Malmquist指数法将中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内资和外资部门的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拆分为分配效率(企业家要素组合的效率)和价格前沿(可能的最小成本)的变化得到:我国内资部门企业家要素组合能力不断提升,却面临更加扭曲的要素价格约束,导致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受限并影响了结构红利的获得。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市场化程度对自主创新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到:第一,政府税收政策显著增强整体和内资部门长、短期的成本约束,使要素价格逼近边际成本前沿面,提高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但以企业家组合资源效率的损失为代价;政府直接资金扶持仅具有短期效应,长期则加大要素价格扭曲、负向影响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第二,较之于对外开放,对内开放程度显著缓解了内资部门要素价格扭曲,使要素价格逼近边际成本前沿面,有利提高自主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并具有长期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只能短期提高企业家的要素组合效率、无长期效应;第三,金融、信贷市场和技术市场发育程度无论长、短期均显著缓解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使要素价格逼近边际成本前沿面,显著提升企业家的要素组合效率,提高了自主创新配置效率。
上述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第一,明确政府定位,建立灵活的政府干预和退出机制,减少创新投入对政府的长期依赖。一是依据产业发展进程及特点合理选择政府干预方式。对于拥有较多市场化企业家的产业,在技术研发阶段应更多采用税收优惠进行创新支持,对于正处在摸索阶段的新兴产业更应选择直接资金资助的方式支持创新。二是,建立完善的政府资金退出机制。政府直接资助创新短期会降低创新者的风险,但是长期容易形成依赖,反而限制了创新配置效率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完善政府资金的退出机制,具体操作可以借鉴风险投资基金的退出方式,如股权转让等。第二,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立生产要素的合理定价机制和流动机制,减少自主创新投入的相对成本。高技术产业企业家自主创新核心技术的投入决策是基于现有生产要素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做出的。现有生产要素成本越低,自主创新核心技术的投入相对成本越高,企业家越不愿意进行自主创新。因此,一是必须加快土地和矿产等稀缺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形成其合理定价机制。在近年世界资源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为了使资源税收入能随资源产品价格和资源企业收益的变化而变化,应该考虑由从量计征资源税的方式改为从量、从价计征,并实行产业从上游到中下游、从开发环节到制造领域的总体税价联动,使稀缺要素定价合理;二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统一、开放、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增强市场利率的联动性;三是完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改变工资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不适应的状况,增加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三,完善和发展金融、技术等要素市场。一是拓宽金融和技术中介服务的功能。在发挥金融中介融资功能的基础上,加深其风险管理和二次融资功能的认识和应用。在发挥技术中介信息、科研功能的基础上,发挥其成果产业化合经营服务平台的作用。二是促进金融、技术市场之间的互动。通过建立技术与金融市场的互动平台,拓宽风险资金来源和退出渠道,缩短资金与技术的距离。
[1]洪银兴.自主创新投入的动力和协调机制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8):15-22.
[2]方军雄.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J].经济研究,2006,(5):50-61.
[3]方军雄.所有制、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J].管理世界,2007,(11):27-35.
[4]成力为,孙 玮.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下的产业资本配置低效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2):41-48.
[5]成力为,孙 玮.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制造业产业资本配置效率视角[J].公共管理学报,2009,(3):29-36.
[6]Gayle P G.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Innovation:New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Schumpeterian Hypothesis[R].Boulder,U.S.:Center for Economic Analysis,University of Colorado,Working Paper No.01-14,2003.
[7]BlundellR,Griffith R,van Reenen J.Market Share,Market Value and Innovation in a Panel of British Manufacturing Firm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9,6(3):529 -554.
[8]朱有为,徐康宁.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11):38-45.
[9]Geroski P A.Innovation,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Market Structure [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0,42(3):586-602.
[10]Hoppe H C,Lee I H.Entry Deterrence and Innovation in Durable-goods Monopol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3,47(6):1011-1036.
[11]冯根福,刘军虎,徐志霖.中国工业部门研发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6,(11):46-51.
[12]严成樑,周铭山,龚六堂.知识生产、创新与研发投资回报[J].经济学(季刊),2010,(4):1051-1070.
[13]孙 玮,成力为,王九云.要素市场不完全视角下的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基于三阶段 DEA -Windows的内外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比较[J].科学学研究,2011,29(6):930-938.
[14]高 帆.什么粘住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翅膀[J].当代经济科学,2008,(3):1-11.
[15]Nikolaos Mnaiadakis,Emmnauel Thnaassoulis.A Cost Malmquist Productiviyt Index[J].European Journal of OPeartional Research,2004,(154):396-409.
[16]樊 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8年度报告[R].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17]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8]吴延兵.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地区工业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8):51-64.
[19]陈 琳,林 珏.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J].管理世界,2009,(9):24-33.
[20]King R G,Levine R.Finance,Entrepreneurship,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3-542.
[21]Blackburn K,Hung V.A Theory of Growth,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rade [J].Economica,1998,65(257):107-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