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就是留着灯留着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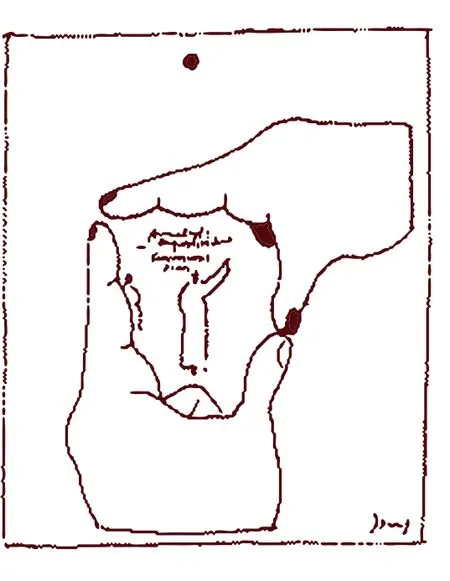
武汉一位高三男生来访。他明显不同于一般来访的客人——完全像在高中课堂听课那样在我面前正襟危坐,神情谦卑而肃然,眼睛像看黑板一样看着我,耳朵肯定是在小心捕捉我的每一句话。他母亲告诉我,儿子看了我对他网上留言的回复后深受鼓舞大有长进。细问之下,原来我半年前引用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走不出的风景》那本书中这样几句话鼓励这位高中生来着:“我们会在这里长久守候。即使夜深了,也会给你留着灯,留着门——只是,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而且,我们相信,你是有出息的孩子!”
他母亲兴奋地介绍说,儿子的学习成绩因此在武汉一所重点高中迅速跃居前列。于是儿子扑奔“灯”来了——参加我校自主招生考试。这次来访,是为了就此向我表示感谢。
送走这对母子,心情一时难以平静,我未能接着爬格子,思绪仍围着“灯”转来转去。是的,关于学校教育和教师的种种说法中,半年多来我只记住了苏力这几句话。的确说得好,质朴,简单,而又独具一格,别有韵味,如父母的叮咛,情深意切,苦口婆心。我想任何人听了,心里都会受到类似的触动。
但作为我,还有相当个人化的原因——它让我想起了那首古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别人如何我不晓得,反正我觉得这首诗里必须有灯,也一定有灯:一灯如豆!荒山僻野,风雪弥漫,贫家寒舍,一灯如豆。而那恰恰是我小时家境和生活的写照。五户人家的小山村,五座小茅屋在风雪中趴在三面荒山坡上瑟瑟发抖。一个少年背着书包朝左侧西山坡亮着微弱煤油灯光的茅屋匆匆赶去。那条瘪着肚子的狗叫了,门“吱扭”一声开了……那个少年就是我,就是从八九里路远的学校赶回家的我。不管我回来多晚,母亲总为我留着灯、留着门。她相信我是有出息的孩子,一定会是有出息的孩子。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去了遥远的广州。时值“文革”结束前后,即使毗邻港澳的广州也破败不堪,二十几个人挤住一间办公室改成的宿舍。我不会讲广州话加之工作不如意,整天在一间小资料室里和几位大姐翻译港口技术资料,而更多的时间是听她们情绪激动地数落某男某女的一大堆不是……这算怎样的工作、怎样的生活呢?难道我就这样终了此生不成?就在我四顾苍茫求告无门的时候,一扇门开了,一盏灯亮了。一位65岁的老教授在我研究生面试成绩不理想而其他考官们面露难色之际,断然表示:“这个人我要定了!”不用说,他相信我是有出息的孩子,一定会有出息的孩子。是他在那里长久守候,为我留着灯、留着门……
现在,是我为孩子们留着灯、留着门的时候了,为了在日暮风雪中背着书包孤零零赶路的少年,为了一时在迷途中左顾右盼不知所措的男生女生。作为我,这谈不上有多么高尚,只不过把我过去得到的拿出一点点罢了。如果说是爱心,有爱心的老师也绝不仅仅是我一个。
记得寒假前在新校区等校车的时候,社科部一位女老师招呼我:“林老师林老师,你看我的学生写得多好啊!”说着她叫我看她的学生刚刚交上来的社会调查报告,“喏,你看,这个男生写他调查流动商贩,同情他们生计的艰难;这个女生写她在乡下见到的留守儿童,想去那里支教……喏,你看这字、这句子写得多漂亮啊,多好的孩子啊……”她的声音是那么兴奋和自豪,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生动和纯真。
记得夏丏尊说过:“没有爱的教育,犹如没有水的湖。”换言之,教育就是爱,就是在这里长久守候,并且留着灯、留着门。
(费月玲摘自《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