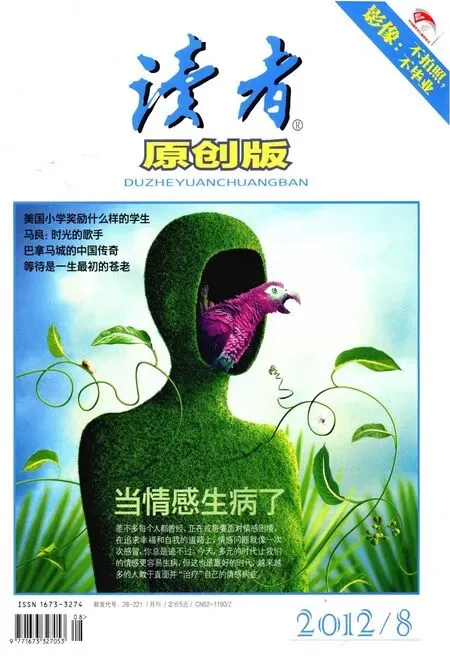马良:时光的歌手
文 _ 本刊记者 王飞
神笔马良
有人说,名字如同一个咒语,会左右人的一生。对于马良而言,名字的确成为他的宿命。
马良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父亲马科是京剧导演,母亲童正维是话剧演员,因为出演《编辑部的故事》中的“牛大姐”一角而为人熟知。出生在艺术家庭,马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也有意无意地想培养他学表演——并非为了成为明星,在那样一个“有序”的年代,子承父业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儿。马良被送去电视台参加小演员的挑选,不想考官都是爸爸妈妈的朋友,于是很无辜地被选中。作为当时上海市少年宫仅有的两个男演员之一,偶尔,马良会在电视剧中跑跑龙套,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则是,每逢节日,马良就会被老师从课堂上叫出去,换上白衬衫蓝裤子,涂上红脸蛋,拿着花环,和其他孩子一起站在南京路上欢蹦乱跳,等待载着领导或外国友人的红旗车疾驰而过。
那时的马良是个害羞的孩子,厌恶任人摆布,也怕面对镜头。爸爸妈妈问他将来想做什么,他回答想做一个画家。在他看来,画家是一个不需要抛头露面的职业,可以握着画笔,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因为经常缺课,马良成绩很差,满心自卑。不过他画画很棒,是班上的美术课代表。六年级的一天,马良帮老师把教具送回校长室。那是很小的房间,马良推开门,空气似乎被带动了,办公桌上的纸张和穿过彩色玻璃窗的阳光散落一地。校长捡起一张纸,突然问他:“你是不是叫马良?”马良点头。校长把那张纸递给他,马良接过一看,上面写着“上海市华山美术学校推荐表”,那是当时上海唯一一所设有初中部的美术学校。校长拍着他的肩说:“马良嘛,神笔马良就应该考美术学校。”
马良一直记得这个带有魔幻色彩的瞬间,一个少年的命运由此转折。
向着梦想迂回前行
198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甲肝大流行让整个上海陷入恐慌,刚刚考入美院附中的马良不幸染病。那时,他的爸爸妈妈都在瑞典工作,姐姐远嫁杭州,唯一可以照顾他的保姆得知马良染病,飞也似的逃掉了。
马良被关在家里,居委会的大爷大妈坐在门口守着他,每隔几天带他去趟医院。10个月是如此漫长,没有娱乐,没有朋友敢来探望,孤独的少年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家里所有的书都看一遍,他背诵北岛、食指、顾城的诗歌,读叔本华、尼采的哲学,16岁的少年被迅速催熟。那段安静的时光弥足珍贵,马良读书、写诗、画画,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995年,马良从上海大学工艺美术系毕业,有点儿“越狱”的兴奋,更多的则是对未来的迷茫。彼时,马良痴迷电影,渴望成为一名电影导演,却始终没有机会进入电影圈。有朋友告诉他,拍广告和拍电影差不多,而且很赚钱。马良听从建议,进军广告业,从美术师助理做起,修习技艺,期待日后能够成功跨界。
短短几年,马良已经成为上海广告界“一哥”,单条广告收入动辄数万,广告短片作品获得多项大奖。但这些获奖作品观众难得一见,电视台和客户要的永远都是最安全的方案:漂漂亮亮的女明星手捧商品,站在花好月圆的背景中。马良内心苦闷,却又难以割舍——眼看青春已逝,还没有真正满意的作品,但如果执著于梦想,不成功怎么办?难道要做一个落魄的艺术家?
那段时间,马良独自远行,期待在旅途中收获答案和勇气。马良买了一部数码相机,摄影让他寻回了自信和灵感,他渐渐放弃了广告导演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摄影。不拍电影,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造梦。
做一个时光的歌手
马良的摄影作品大多色彩浓烈,充满离奇的想象和乌托邦式的浪漫与迷离。超现实主义的风格让人沉醉,也常常因为解读不同而产生争议。在马良看来,真正的视觉艺术一定是语焉不详的,应该给观众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而不是设定一个标准答案。
马良对纪实摄影并不太感兴趣,他的方式是搭建一个舞台,用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来还原自己内心的画面。广告短片导演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马良的摄影创作,他有着强烈的操纵欲望,希望拍摄对象可以进入自己为照片设计的氛围。在摄影作品《不可饶恕的孩子》中,他干脆让所有的人物都戴上面具,隐去真实身份,成为一个象征符号,游荡在废弃的游乐场、烂尾楼和荒草地中,诡异又美丽。
马良是个念旧的人,他的照片总是有种旧旧的感觉,却带着温暖的底色。《邮差》是马良特别喜爱的作品:一位穿着旧式制服、仿佛来自时光深处的邮差,穿行在日渐颓败的弄堂里,寻不到曾经的地址门牌;昔日孩子们欢闹的乐园已成废墟,邮差扛着毫无用武之地的自行车站在瓦砾上四顾茫然。城市巨变,无力阻挡,唯有“用想象弥补出一个亦真亦幻的过去,沉溺其中片刻,以获得某种温情安抚”,仿佛一切都还在原地,安静从容。
马良怀念那些纯真的东西,特别渴望回到最初的状态:17岁的少年,拿着画笔,给家里所有的门上都画上一幅画。因为学了美术,少年希望力所能及地让自己的家变得好看;客人亦会赞叹,这个家庭因为有一个会画画的孩子而显得与众不同。
其实,艺术的作用就是这么简单,它无法拯救世界,却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给焦灼不安的人们以温柔抚慰。而马良想要做的,就是从现实的世界里抽出一个比较不现实的瞬间,让被拍摄者体验浪漫的想法,从而暂时摆脱严酷现实的束缚,享受到些许自由。
带着这样朴素的想法,不惑之年的马良启动了“移动照相馆”计划,开着卡车去不同的城市免费为朋友和陌生人拍照,为他们留下一段浪漫的回忆。马良并不在意别人对于“移动照相馆”摄影作品的非议,事实上,这已不再单纯是摄影,在这场流浪的修行中,马良和他的团队用自己的真诚,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同时播下善意的种子。
每个艺术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创作方式,栖身书斋,高居殿堂,或者行走在路上,只为前方从未遇见的风景。马良说,为了理想,我们总是胡乱披挂上阵。但这无情的世界,正因为热情的蠢货,才有些浪漫。
马良曾经这样写道:“照相机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把木吉他。我只想用它弹奏一些时间和光影的旋律,然后,把想唱的歌轻轻地唱给那些想听我唱歌的人。把生命里的那些疼痛和爱都点燃成温暖的熊熊篝火,让那些在照片里不老的美人和所有被一一定格的美好风物,在我的歌声里笑得花枝招展。”
今生今世就这样做一个时光的歌手,多浪漫。
拍摄过程非常有意思,马良总是很乐意倾听被拍摄者天马行空的想法,并全心投入,帮其设计得更完美。就比如我们的《爱情三部曲》,本是一场血雨腥风,却有相拥微笑的结尾。
愉快的拍摄经历以及作品最终的呈现会让你觉得原来艺术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并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在拍摄过程中,你会感到马良的浪漫、善良、温和。这些都是有感染力的,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马良说,他想用他的行动为喜欢他的人做一些事情,让他的“艺术”变得有用一些。当然,他和“移动照相馆”证明了一点,无论它看上去多么理想主义,但只要有强大的意愿,这世界就会容纳这份不可思议的梦想,冷漠的世界也会因此温暖一些。
——李梦宇(兰州)
谢谢马良,认识你6年,第一次给我拍的照片是与我未来的至亲在一起。人一辈子都在得到与失去中度过,你等待的终究是你最缅怀的。爱的毁灭和重生其实都是同一瞬的事。希望“移动照相馆”载着每个人的爱无悔前行。
——苏楠(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