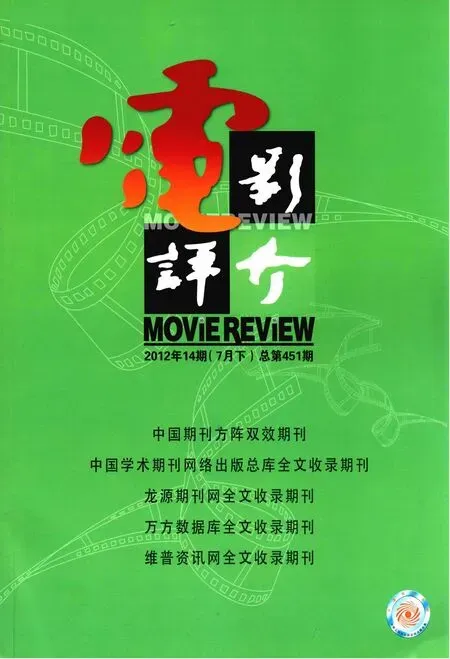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原生态”音乐的运用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步入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转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电影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少数民族电影主题从“17年时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的想象性再造”[1]逐渐转向为对少数民族自身文化身份的思考和建构。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商业化大背景下,新时期少数民族电影的主题,更多在于挖掘和探索‘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异质性、差异性,在价值观上坚持少数民族的文化选择,与社会主流文化保持一定距离,更多采用纪实风格,突出记录性和人类学色彩,较少迎合普通观众的观影心理。”[2]
新的文化视点导致了电影美学风格的重大转变。就电影音乐而言,引用西欧现代作曲技法创始人之一的勋伯格在去世前的四十年代末给他的学生、波兰裔法籍著名作曲家、理论家莱博维兹(R•Leibowitz 1913一1972)信中所指出的“每一个企图树立一种新风格的作曲家,在今天差不多都感到一种迫切的愿望,想恢复到古老风格中去”。 [3]电影作曲家们的创作也体现出这种想恢复到“原生”风格中去的倾向。与17年时期“以西方交响乐队配置和创作手法为主,吸收和运用民族音乐语言和表现形式为基础改编创作的电影音乐”[4]体现出的民族化相比,将少数民族原生态民间音乐直接置入到电影中突出音乐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则成为新时期以来电影音乐民族特色的重要表现。
在几部较有影响的如《孩子王》、《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金沙水拍》、《千里走单骑》等少数民族电影中,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是电影音乐的一部分,更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增加了电影对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环境真实性的描述。由于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电影音乐表现形式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在具体运用中,原生民间音乐也以不同形式与电影主题和画面结合在一起,成为电影凸显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手段。

一、作为电影主题音乐
电影《花腰新娘》以12个女子舞龙的故事为主线,将花腰彝族传统的海菜腔、烟盒舞、舞龙、民族服饰等传统民风民俗融入其中,用时尚、唯美的拍摄风格展现了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同时也反映出花腰彝族青年在现代社会语境中所面临的经济、文化等种种冲击。影片主题音乐选用彝族特有的真假嗓结合的海菜腔。海菜腔是彝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歌,严格说来,真正民间的《海菜腔》的曲式结构,是数百年来发展演变而成的,它的结构有着很严的定格与规矩,内容的表述也有着不可逾越的程序。“悠扬而富于歌唱性的拖腔音调,与带有叙述性的说唱式的音调相结合。其旋律进行多以平稳的级进与四度五度、甚至八度以上音程的大跳相结合。因此,它的风格时而婉转细腻时而跌宕起伏、抑扬不拘激越荡漾,这种风格的对比与变化,对内容的表达,对感情的倾吐,都具有丰富的表现力。”[5]
谱例:
演唱者李怀秀是被誉为“云南歌王”的民歌手,她演唱的海菜腔的音调作为影片主要音乐元素贯穿始终。影片从一开始音乐就以她极富魅力的声音展示了少数民族特有的音乐风情,MTV式的拍摄风格,传统的民间音乐被赋以新的现代时尚元素。

图表1
黑白的影像,诗意的叙事,运用音乐蒙太奇[6]手法把小凤美成长的一切都包含在响遍山野的歌声中,画面与音乐结合得自然、流畅。悠远嘹亮的歌声穿透山野,就像是“卸妆”的美少女,与影片中其他更具现代气息的钢琴、长笛、电子音乐等音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主题音乐在影片中多次重复,将海菜腔特有的“歌唱性的拖腔音调与带有叙述性的说唱式音调”完美呈现,时而高亢豪放,时而婉转悠扬,音乐不仅成为电影展现花腰彝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丰富了电影视听语言的艺术表现力。
二、作为揭示电影主题的重要段落
原生态民歌在电影《诺玛的十七岁》中则有着不一样的含义。影片向人们讲述了生活在红河哀牢大山深处17岁少女婼玛的一段凄婉、美丽的青春故事,是一部表现现代文明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的影片。导演章家瑞曾坦言:“我们选择非职业演员,并采用哈尼族的语言,就是为了不同于过去的《阿诗玛》、《五朵金花》那种带有包装的成分。我们想原汁原味反映哈尼人的文化,呈现哈尼人真实的状态。”[7]
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简单、纯净,音乐弱化了民间音乐中的旋律性,la-mi-re-sol的小调式单音旋律,在弦乐长音的衬托下,用钢琴、钟琴等键盘乐器敲击的音响一个个缓缓流淌出来,这一旋律每次出现总是伴随着哈尼梯田诗意的影像,为影片营造了一种平和、温暖的氛围。在这一安静的氛围中,奶奶、喊魂象征着古老的传统,智慧而内敛;而来自省城昆明的阿明给婼玛随身听里面播放的爱尔兰歌手恩雅演唱的歌曲,音乐类型上,恩雅是属于“世界音乐”范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音乐作为一个符号概括了电影的主题——现代文明对这个民族,特别是对17岁婼玛的冲击。
影片运用了完整的原生态民歌《叫魂调》作为电影的一个重要段落揭示主题,对于少数民族电影音乐创作来说可谓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叫魂调》是哈尼族传统的祭鬼古歌,“魂为肉体的伴,伴没有了,即魂就掉了,魂掉了肉体就病,这时吃药不好就非要叫魂,把魂叫回来,肉体的病才会痊愈。……叫魂必须请祭师来作法,用红公鸡、酒、饭、鸡蛋、香等祭鬼敬鬼,并唱‘叫魂歌’。这歌平时不能随便唱,一般只能在特定的祭祀活动中由祭师演唱,有时也由家中的长者唱。”[8]电梯、照相馆、随身听等等都是现代文明的符号,17岁的哈尼族少女诺玛面对外面世界的种种诱惑,而17岁又是个精神最易漂移的生命阶段,“叫魂”是让她从精神上对传统回归与固守,影片以非常朴素的手法来表现这个主题。

图表2
“魂兮归来”,把民歌置入哈尼族的生活环境,本民族的语言,不加修饰的音色,尽管对于观众来说,歌词是陌生的语言,但画面并没有去解释歌曲的内容,所有的物像都被置入真实的自然环境中,好像是一个旁观者,静静地凝视着发生的一切。声音从画外转入画内,简洁流畅的镜头语言传达出民歌中深厚的文化内涵,极具震撼力。这首民歌与其说是电影音乐,不如说这更是一种哈尼族民俗文化真实的再现,从中可以感受到创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态度。
影片自然地把哈尼族的日常生活、风俗以及信仰渗透到了情节和人物之中。那些贯穿全剧始终,在片中多次出现的梯田及织布机的声音,背篓、木楼梯、开秧节等等都代表了传统的哈尼人的文化,它们不仅是环境的交代和点缀,更是一种古老传统的象征,具有更深层的文化涵义。
三、作为音响结构元素
电影《金沙水拍》主要反映红军长征途中路过云南、四川凉山等民族地区时充满艰险离奇、悲欢离合的感人故事。作曲家晓耕曾详细阐述了在《金沙水拍》中对一个战争场面创作音乐的想法:“在红军路过彝族地区,遇到不明真像的彝族群众抢夺枪支的冲突中,在一声‘嘟……’的具有神秘的、地方味十足的喊声中,几百彝族汉子从山坡上往下冲,踏着黄灰,卷起风沙,突如其来地冲到红军面前时,我们避开了用紧张音响的传统手法,而是以彝族语言中一些有特色的词组如:迪士格杀、哦来木吉、柯来木吉、呀哆等等为音乐符号,用语言字母音节中抑扬顿挫的律动,单双音节和长短句的有机结合,在说、喊、唱多种语言声部节奏中,用电声的低频作长音背景,利用多轨录音技术中扩展声响空间,增强立体感、纵深感、现场感,加大力度和紧张度。利用少数民族吹管乐中不同音高的吹管乐器,采用不规则的重音节奏,大量用非常规的奇异音响,偶然音乐、多声、多调、多节奏节拍的分割性重叠。在昆明音像公司制作时,特别邀请在昆明的一些民族歌手,以他们独特的声音造型,即兴地运用各种彝族语音配唱、配喊。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进行后期制作时,又把拍摄时的那些真实的呼喊声、撕打声、喘息声、真枪真刀碰撞的金属声,和昆明录音棚录制的声音混录在一起,编织成一首粗犷的、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特色的乐段,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受。”[9]
运用少数民族歌手独特的声音条件,即兴配唱的手法在反映僳僳族、傣族抗英斗争的电影《石月亮》中也有出现。作曲家将现代技法的多声思维纳入到电影音乐的创作中,在场景音乐的设计上直接运用少数民族的语言音调和声音特色在听觉上造成的色彩性变化形成一种“声音的交响”,这种音乐音响化的效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四、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
在电影《孩子王》中导演陈凯歌运用了树桩、牧童、字典等元素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传递着自己对生活、文化的思考。在老杆教知青念书一场中(55’00-56’02),知青们反复吟诵“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在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的故事,单个人的朗诵声不断重复越来越强,有着强烈传统文化意味的傣族赞哈也加入其中,“傣族赞哈是从叙事古歌衍变而来的说唱音乐,除娱乐功能外,还具有某种教育功能,是傣族人了解傣族社会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重要文化活动方式,可称得上是傣族的‘百科全书’。”在这一段落中,音乐的无序、杂乱暗示、象征着文化的因袭与循环,而傣族赞哈在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深意,更传达出创作者对传统教育方式的深刻反思。
张艺谋在电影《千里走单骑》里把父子之间的情感融入云南的乡土风情画中。在影片中,古老的傩戏成为串起故事的主线,两对父子:一对来自日本,一对则是远在天边的云南丽江。本是相隔千里,却因为一出约定中而未完成的“傩戏”联系在了一起。傩戏是一种特殊的、古老的民间戏剧形态,主要在祭祀活动中演出,又称端公戏。傩戏表演上的最大特点是借助形象生动的面具,表演者戴面具,扮做驱逐疫鬼的神魔形象。[10]傩戏在影片中作为具有特殊意味的文化符号,一方面是民间传统文化的象征,另一方面,影片利用傩戏中的面具,传达了创作者对于“面具人生”的思考、表达“面具下的人心”、“自己的本来面目”等深层含义。有学者称:“在惊叹于导演细腻娴熟的表现手法的同时,也惊讶于导演对民俗元素如此大胆的‘排列组合’……张艺谋以其深厚的艺术洞察力,创造性地将两种文化一并混淆,不可谓不高明。”[11]
结语
与17年时期引用少数民族音乐曲调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音调,并将少数民族语言改为普通话演唱的单一创作模式不同,新时期云南电影中出现的原生态民间音乐大多是以本民族语言或方言演唱的。原生态民歌自然地反映出少数民族语言语调的不同,很多民族都有某些特色性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是外族很难模仿的。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民族语言还是方言的吟唱,唱词是有具体内容的,但电影中不论是作为色彩性或是民俗仪式中的歌咏,唱词的内容却被有意识地忽略或被模糊,有时则以字幕代之,这就使得歌咏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并不执著于唱词所叙述的具体意思,而是被最“原生态”的自然的声音本身的魅力所打动。在这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最鲜活的表现形式之一,音乐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声音符号,更代表了一种文化,是一个具有强烈文化意味的符号。不仅在声音层面丰富了少数民族电影音乐的表现形式,也从更深层次揭示了电影文化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没有像《五朵金花》、《阿诗玛》等17年时期那些流传广泛的电影音乐作品,可是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于人的尊重和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关注却是极为可贵的。
注释
[1]陈旭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谁在说”和“怎么说”》,载《当代电影》,2010年第9期
[2]李春:《功能诉求转向与少数民族电影的变迁》,载《现代传播》,2011 年第10期
[3]转引自饶余燕:《现代音乐创作民族化的两个问题》,载《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4]赵乐:《建国后17年少数民族电影音乐研究— —以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例》,载《民族艺术研究》,2010年第2期
[5]梅璧:《<海菜腔>的音乐特征及内涵因由》,载《中国音乐》,1988年 第2期
[6]注:音乐蒙太奇是指当一组镜头是用音乐来组接时,音乐不仅成为连接这些镜头的纽带,同时赋予这组镜头以镜头之外的涵义。见曾田力《影视剧音乐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81页
[7]贺永连:《<诺玛的十七岁>美丽而古朴的诗情》,载《电影艺术》,2003年第1期。
[8]周凯模:《云南民族音乐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65页
[9]晓耕、曹鹏举:《<金沙水拍>音乐创作断想》,载《民族艺术研究》,1995年第3期
[10]资料来源: www.crionline.cn,国际在线,2006-04-07
[11]叶田:《别去丽江看傩戏》,《文汇报》,2006年2月8日
1、《民族音乐概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
2、《民族音乐学译文集》,董维松、沈洽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6月版
3、《民族音乐学概论》,伍国栋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3月版
4、《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5、《论电影音乐》,王云阶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
6、《电影的元素》,李.R.波布克,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
7、《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电影家协会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8、《影视剧音乐艺术》,曾田力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
- 电影评介的其它文章
- 寻找“伊莎贝拉”——电影《蝴蝶》叙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