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城市:大城市需要城中村
钱亦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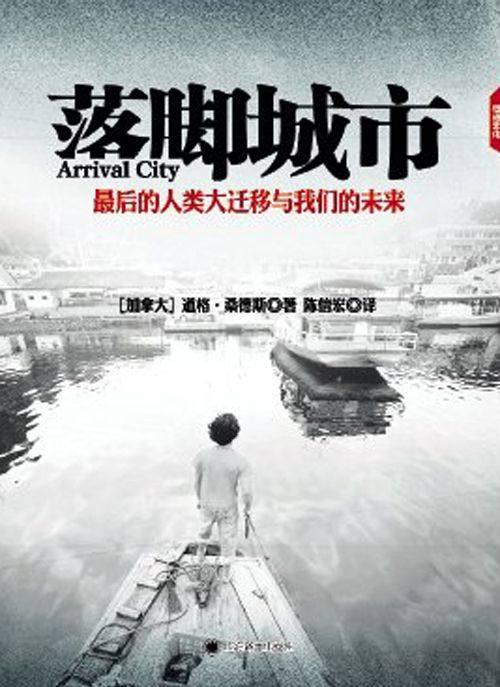
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根据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截至2007年,世界上已有33亿人生活在城市,超过了全球人口总数的50%。而在中国大陆,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化运动正在进行之中,根据官方数据,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
也许我们可以将迅猛的城市化归结为生产力变革和信息传播。制造业迅猛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风潮提供了大量的城市就业机会,就好比中国每一个“Made in China”背后都有着城市农民工的血汗;道路和电力的构建,使得再偏远的农村也与城市接轨,农民们也感受到时代的改变,而电视、网络等丰富的信息传播渠道,让他们知道城市里的收入远高于农村,让他们也向往电器和汽车,向往另一种生活方式。于是世代不离乡土的农民纷纷启程,开始了迈向城市的征程。
然而,从赤贫到中产,并非一蹴而就,一个农民真正融入城市、被城市所接受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是为何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那么多问题甚至危机。“人们不会说把自己农村的家当收拾起来,然后搬到城市里面去,这样就城市化了。城市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程,他们可能会经历大概数年甚至数代的努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经历往返,包括资金的往返流通。”加拿大记者、作家道格·桑德斯如是说。桑德斯是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记者站站长,曾四次获得代表加拿大新闻界最高荣誉的“国家新闻奖”,他走访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潮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现象进行深度调查,撰写了《落脚城市》(Arrival City)一书。近日,他携书来到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进行了一系列演讲和对话。
落脚城市不能轻易毁去
落脚城市,指的是农村居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脚并聚集定居的地方。桑德斯认为,适宜的政策和支持会让落脚之地获得接纳,他们也得以融入正常的社会;反之则会导致经济停滞、极端势力增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有政府把落脚城市定义为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一般民众更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贫穷脏乱将其鄙夷为恒久不变、无可救药的贫民窟,更具杀伤力的思维则认为,这些拥挤的社区是都市杂乱蔓延以及人口过剩的罪魁祸首。
这样的城市边缘的城中村,在如今的中国也并不少见,和世界其他地方如孟买北端、德黑兰边缘、圣保罗的山坡地等一样,这里充满着不满情绪。“我在这里见到的都是原本生长于乡村的人口,心思与志向都执著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身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当中,目的是在城市里为自己的子女争取一片基本但长久的立足之地。”桑德斯说。
在书中,桑德斯写到了中国重庆市郊的六公里,这就是一处城中村。桑德斯曾采访到一户四川乡村的农户,住在泥地小屋里,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后来通过15年的努力,在城里买了属于自己的公寓,月收入达到1.5万美元。他们当初进城就住在重庆郊区六公里的社区,这里聚集了12万人,他们通过自己工作上的收入,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基础。“这里不是重庆周边最贫困的乡村,相反来到这里的人是存了最多的钱,拥有最具雄心的计划。他们一开始可能多数在工厂等地方打工,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里面,在存了几年以后搬出来,开始了自己的小生意。一开始可能只是水平非常低的商品交易,在街頭出售食物,比如著名的麻辣烫。”桑德斯介绍了他6年前走访六公里时的所见所闻,但是户口、治安等问题都是这些落脚城市不得不面对的共同困境,而且,当时他就担心集体所有制的六公里随时都可能被政府移为它用,但这势必将摧毁许多家庭在都市边缘投注一切所得来的生活与经济基础。
如今,六公里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拆除了,政府把贫民窟改建成了漂亮大楼,在条件上,这的确是更好的住所。“但是,这毁坏的不仅是落脚城市的经济结构,也会脱离重庆和四川周边的乡村经济,也可能毁掉了这批移民孩子的教育和他们的未来。”桑德斯说,其实世界各地也有不少政府在对待落脚城市上,走过弯路。而在巴西,脏乱差的贫民窟法维拉没有被取缔,而是通过来自政府的援助对它进行改造,使人们有机会在这里立足,政府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并且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使他们不必搬离这个贫困社区而进入中产阶层。
桑德斯认为不能轻易破坏落脚城市的经济生态,贫民窟或许并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是摧毁贫民窟是更不好的做法,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住家和每一个工作场所,都不断联系着两个方向。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从而使得下一波的村民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年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教育、村庄本身也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落脚城市也和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联系:其政治体制、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与买卖交易等一个个的立足点,目的在于让来自乡村的新进人口能够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站定脚步——不论这样的立足有多么如履薄冰——从而谋取机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获得社会的接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不能落脚的城市和空巢的农村
支持桑德斯的观点——在大城市中要允许贫民窟的存在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秦晖教授。《落脚城市》一书中还涉及到一个中国大城市,那就是深圳,被桑德斯叫作“无法落脚的城市”。在深圳这座有1400万人口的城市里,只有占百分之十五的210万人口拥有户籍,在2010年年底前,如果没有户籍,孩子将无法就读本地的学校,月薪5000元以上的白领能勉强负担起深圳的房价,对普通劳动者而言,拥有房产却是难以企及的梦想。秦晖认为这座城市要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鼓励贫民窟的发展。
秦晖走访过世界各地好几处贫民窟,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人会说贫民窟是个好东西。但是比贫民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家庭离散。……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不能忍受这种状态,他们愿意全家住在一起。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以3亿人口的家庭离散作为代价换得了城市的光鲜,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信息。”
在中国,落脚城市是遭到歧视的,农民工无法通过合法手段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转变身份。允许打工,却不允许安家,是目前进城民工遭遇的一大困境。桑德斯则以欧美等已经历过城市化的国家的历史为鉴,他们也产生过误区,第一是阻止农业人口迁移进入城市,第二是已经迁移落脚到城市的居民,不给他们正式的存在身份。这直接造成了激烈的暴乱和冲突。相反的例子是,伊斯坦布尔的奥扎尔公布了第280号法案,将占地居民转变为合法纳税人,让他们对自己临时搭建的房屋及土地取得所有权后,一个混乱敌对的板块成转变成了繁荣的社区。
在城里得不到合法身份、享受不到对应的医疗教育福利,也使得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大规模城市化运动中出现了大量的家庭离散以及农村的空巢现象。桑德斯曾接触过四川的偏远乡村水林,就是典型的空巢农村。他这样描写它:“儿童、牲畜、祖父母。十四岁至五十五岁之间的人口,包括所有儿童的父母,都已背井离乡外出工作,只留下寂静的夜晚、空荡荡的房间和深邃的思念。”当然,他提到,这也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罗马尼亚,空巢已成为全国性议题,罗马尼亚的乡村也由祖父母抚养小孩,并由孩子的父母从遥远的城市寄钱回来支持他们的生活。
秦晖认为,目前中国的空巢现象非常严峻,“今天在中国农村有很多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就过着类似于孤儿的生活。这不但有农民工的因素,还有目前由于乡村衰落,政府的服务也开始退缩。很多地方原来的农村中小学都合并上收,比如说小学上收到乡镇一级,中学上收到县城,因此这些孩子进小学就得住校。像这样的一代孩子,他是完全没有对亲情的体验,这些人的心理会有严重的问题……中国现在面临乡村的家庭危机是相当严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