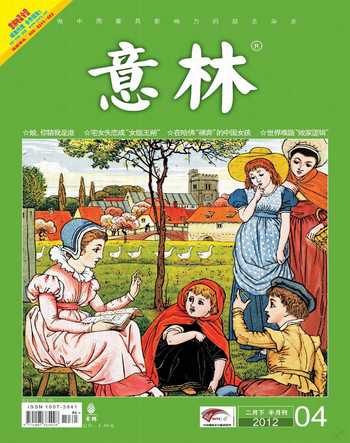火豺
我和波农丁每人挑着一担柴,踏着夕阳从山林回寨子。转过一道山湾,波农丁突然用手势示意我停下,指着山谷对面一片荒草地说:“快看,一大群豺!”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果然一群毛色艳红的豺在小路上走着。豺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的动物,显然,这是由三家豺组合起来的群体,因为整群豺分为三个小部分,每个部分都是两只大豺和五六只小豺。六只大豺齐心合力地拖拽着一头牛犊,十五六只小豺围着自己的父母兴奋地跳跃奔跑。看来,这三家豺联手猎获了那头倒霉的牛犊,正要找个清静的地方享用丰盛的晚宴呢。
果然,六只大豺把牛犊拖进石崖下一个山洞里去了。
“哎呀,我们要发财啦!”波农丁一张皱褶纵横的老脸笑成一朵花,“快,跟我来。”
我稀里糊涂地挑着柴,跟在他后头一路小跑,迅速接近那个山洞。
我一面跑一面心里打着小鼓,我以为他要带我去和豺群搏杀,那可是小命吊在刀尖上的买卖。豺生性凶猛,尤其是纠集成群的豺,敢与豹子争食。
我和他是上山来砍柴的,既没带猎枪,也没带弩箭,光凭两把柴刀,要和六只大豺十五六只半大的小豺玩真的,下场恐怕比那头牛犊好不了多少。
“我们先把豺群锁在山洞里,然后,到寨子里叫人。唔,我进过这个山洞,形状像葫芦,洞口小,里头很宽敞,但这是个死洞,没有第二个出口。”波农丁把我带到离洞口30多米远的一丛茅草里,小声对我说。
“先把豺群锁在山洞里,这主意挺不赖。”我没好气地说,“我们先给山洞安一扇门,然后去买一把大铁锁,‘咔嗒一声把大门给锁上。”
“年轻人,说话别刻薄。我啥时候说过要给山洞装木门啦?我是说给山洞安一道火门,唔,用火来锁。”
波农丁说着,从筒帕里掏出一大团随身携带的火绒,又让我捡了许多枯草,爬过去轻轻撒在山洞口。那群豺大概是在洞底聚餐,大概是吃得太高兴,太忘乎所以,竟然一点儿也没发觉我们在洞口所做的一切。太阳落山了,群鸟归巢,暮霜沉沉,我们在洞口铺起厚厚一层枯草。波农丁用火柴点燃了火绒,霎时间,燃起一片大火,洞里的豺们这才如梦初醒,嗷嗷怪啸着,挤到洞口想夺路逃命,又被炽热的火焰烫得缩回洞底。野兽最怕的就是火,对豺而言,火门比铁门还要厉害。
这火门安得可真是地方。这个山洞坐落在一条小石沟的底端,换句话说,一出洞口,两边就是绝壁,石沟约有1米宽,5米来长,然后才是空旷的山野。豺再狡猾,也不可能擦边溜底绕开火焰逃逸;5米长的火带,豺的弹跳力再棒,也休想像舞台上表演的狗钻火圈那样嗖地蹿跃过去;再说,洞口狭窄,它们若想助跑跳远,必然会一头撞在洞顶的石壁上,脑浆迸裂,呜呼哀哉。
我和波农丁挑着两大担柴,足够烧一阵子了。波农丁蹲在洞外一丈多高的陡坎上,一面慢悠悠地往底下的火带扔柴火,一面遗憾地说:“要是风向对头,不用回寨子叫人,浓烟灌进洞去,熏也要熏死这些豺!”
可惜,刮的是东南风,会让窒息生命的浓烟都刮到山洞的左侧去了。
“你守在这里,注意别让火熄灭。我去寨子叫人,最多半个小时就回来。”波农丁说。
“没问题。”我拍着胸脯说。往陡坎下扔扔柴火,这活儿轻松得就像玩儿似的。天旱物燥,除非老天爷立刻下场暴雨,这火焰绝对不可能熄灭的。
天空繁星闪烁,不见一丝云彩,没有任何要下雨的征兆。
波农丁去了二十来分钟,我听见洞里传来一声声如婴儿啼哭般的豺的哀嚎,令人毛骨悚然。我拼命添柴火,那条1米宽5米长的火带火苗蹿得一米高,像一条鲜艳夺目的地毯。又过了几分钟,山谷外传来狗的吠叫声,哦,波农丁带着猎人们和猎狗群快赶到了,山洞里的这群豺,很快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
就在这时,发生一件让我这辈子永难忘怀的事:一只腹部吊着两排乳房的成年母豺,突然跨出洞口,明亮的火光中,我看得十分清楚,火舌像把推剪,一下子把它的胡须和脸上的毛“剪”光了,红白相间的漂亮的豺脸被烧得一片黑,成了一张丑陋的黑脸。它龇牙咧嘴地怪啸一声,疯狂地扑向火焰,它在火带上趔趔趄趄地向前迈进,整个身体变成了一只火球。天晓得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毅力,竟然在一米高的火焰中坚持走完了5米长的路程,一直走到火带尽头,这才四肢趴下,匍匐倒下。它的身体盖熄了一段火带。紧接着,一只成年公豺又重蹈覆辙,倒在前面那只母豺的身后,六只大豺,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接一个倒在火带上。5米长的火带,被六只大豺的尸体压熄了,那上了锁的火门,被无畏的生命撞开了。
这时,半大的小豺们从山洞里鱼贯蹿出,踏着它们父母的身体,踏着用生命铺出来的通道,越过石沟,越过死亡,逃进浓浓黑夜莽莽密林。
飞蛾扑火,牺牲自己,拯救后代,六只大豺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看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等我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十五六只小豺已逃得无影无踪。
波农丁带着猎人和猎狗赶到时,带头走进火带的那只母豺早已被火焰烧成焦炭,又由焦炭变成红彤彤半透明的火堆,在四周跳动的火苗的映衬下,栩栩如生,像一只梦幻中的火豺!
(李苏杰摘自《沈石溪动物小说自选集》重庆出版社图/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