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土地”上的脚步
编辑整理/津 沙
汪洋“土地”上的脚步
编辑整理/津 沙
在人类迈向海洋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种艰辛和挑战。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海洋的?在这片既是阻隔又是媒介的“土地”上,我们迷失过,惶恐过,但最终,我们学会了“行走”,甚至“奔跑”。
人们最初的航海就像蹒跚学步的婴儿,总是离不开陆地母亲的怀抱。
早期的北欧海盗在航行时,靠海面和海中的自然物识别方向,需要对周围的动物和景象十分熟悉,如鸟类、鱼类、浮木、海草、水流、水色、冰原反光、云层、风势等。9世纪,北欧著名航海家弗勒基总会在船上装一笼乌鸦,觉得船即将靠近陆地的时候,就放飞笼中的乌鸦。如果乌鸦在船的周围漫无目的地飞翔,说明离陆地还远;如果朝某个特定的方向飞去,他就会开船追随乌鸦飞去的方向,而那往往是驶向陆地的方向。不过,这种方法仅仅在距离陆地比较近的情况才起作用。
古代的水手除了要有过硬的驾船技术,还需要有超好的视力和灵敏的耳朵,因为他们的航行主要靠岸边教堂的塔尖和树梢以及狗的吠声来辨别方位。即便是这样,在航行途中,他们也是逢岛必登,为了避免船被风吹到看不见陆地的大海中央,一到夜晚,他们还要把船拖到岸边的陆地上。
据说,尽管中世纪商人的航线遍布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但他们却从不让岸上的山脉在他们的视野里消失超过几天。那时,航海者在海上总是保持与岸边比较近的距离航行,通过他们能够看到的陆地上的特征来判断航向是否正确。像欧洲各城市的商船大多采用沿岸航行,他们宁愿沿着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地中海海岸作迂回航行,也不肯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向东直航。总之,没有一个船主敢冒险出海到望不见陆地的洋面上去,他们认为沉没在大海里比碰到暗礁和浅滩可怕多了。他们不敢穿洋直航的主要原因是怕迷失方向。由此可见,在远洋航行中,确定船只的方位是第一位的。如果13世纪下半叶那件“被施了魔法的小针”还没有传入欧洲,欧洲航海还将继续它那代价高昂的痛苦历程,完全依靠运气和猜测惶恐前行,仿佛摆脱不了学步车的孩童。

古代的水手除了要有过硬的驾船技术,还需要有超好的视力和灵敏的耳朵。
在指南针发明以前,海上航行只能靠日月星辰辨明方向,航程短而且多沿海岸航行。到了宋代,有确切记载宋人使用了带有指南针的航船。吴自牧《梦梁录》说:“风雨晦暝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这样一来,人们就再也不会迷失在茫茫无边的大海里了。后来,指南针通过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时间大概是在13世纪。
“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这小针总能告诉你哪儿朝北。”这个消息从欧洲港口的啤酒屋里传出来,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被撒旦施了魔法的小针。不过在最初的时候,一般的水手都不敢使用这个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小针,只有那些大胆而又谨慎的船长才暗暗地使用,使用时把它装入一个小盒子里,生怕被别人看到。第一批威尼斯人在这根灵敏的小针带领下,从威尼斯的浅海峡航行到了尼罗河三角洲。直到13世纪后期,指南针才在欧洲得以广泛使用,世界第一次开始缩小,原先各自孤立而不相联系的大陆和国家被联系在一起。
后来,人们发现它并不总是指向正北,有时偏东一点,有时偏西一点。在专业术语上,这种差别就是所指的“磁差”。由于南北磁极与地球南北极不在同一点,这就导致磁差的产生。由于磁差的存在,对一个船长来说,仅有指南针还不够,还要有航海地图,以便了解世界各地的不同磁差。
仅仅确定了航向还是不够的,作为船长还需要知道船只所在方位。中世纪的船长在茫茫大海中辨别方位时,只有两件工具可以借助,一件是测深绳,另一件是测速器。
测深绳几乎是同航船一起问世的。它能测量出海洋任何一点的深度。假如船长手上有一张航行的海图,上面标明了这片海洋的不同深度,通过观察所在水域的情况和测深绳的测量结果,就能算出船只所在方位。
最原始的测速器是一块木片,把它从船头抛入水中,然后观察船尾通过这块木片共花去了多长的时间,由于船的长度是已知的,通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得出船的航行速度。后来,绳子取代了木片。这种绳子很长很细也很结实,预先按照固定长度打上一个个的绳结,一般一个绳结代表一海里,并把一块三角形木片系在绳子的一端。将绳子投入水中的同时打开沙漏,沙子从瓶中漏干时(一般为两三分钟)再把绳子从水中拉起来,数出这段时间内下水的绳结有多少个,就能够得知在这段时间里船开了多少海里了,从而算出船的航速。知道了航速,通过航行时间计算,就知道距离出发点的具体方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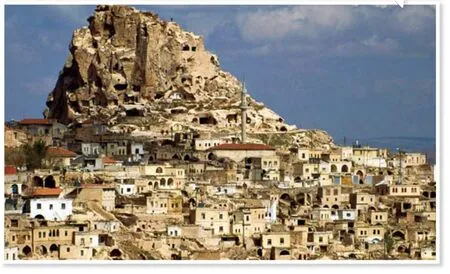
过去,东西方的交流与沟通主要通过陆路通道,但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建立切断了这条交流纽带,于是欧洲人非常迫切地需要发现一条通往印度的新通道。从这个角度讲,最初欧洲人走向海洋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决定。
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洋流、潮汐和狂风随时可能打乱船只的航速和航向。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寻找到一个新的参照物,来替代教堂上的塔尖。
教堂上的塔尖、海滩沙丘上的树冠、堤坝上的风车以及沿岸的狗叫声,都曾在航海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有了这些参照物,水手们就能够把自己的方位推算出来。如果能找到一个本质性的“参照物”来替代这些人工的“参照物”,通过三角学的计算就能确定船只的方位。人们首先想到了北极星,因为北极星距离人类十分遥远,看上去就像是静止不动的。另外,北极星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即使是最愚笨的水手也能指出它的方位来。那时,航海家用“雅各竿”来测量北极星的角度。就是用两根竿子在顶端连接起来,底下一根与地平线平行,上面一根对准北极星,然后利用得到的偏角差来计算纬度和航程,这种古老的技术被称做“纬度航行”。如果船只越过了赤道在南半球航行,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因为在南半球是看不到北极星的。
尽管如此,“纬度航行”的方法在西欧盛行了很久,人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把自己置于与目的地相同的纬度线上,然后保持在这条线上航行,就能到达目的地。但在几乎没有像样的航海工具的过去,“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误差经常发生。哥伦布西航就是一个例子,他自认为先南下到达与印度相同的纬度后,再直线往西航行就可抵达印度,但实际上登陆的只是加勒比海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
16世纪初,圆球理论取代了圆盘理论。地理学家通过地球两极中轴线和赤道的确立划分出了南北半球的纬度。代替“教堂上的塔尖”的那个参照物就是南北极点,因为它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六分仪和航海钟的发明,让船员可以迅速、准确地得知自己所在位置的经纬度。从此,人类从“原始航海”进入“定量航海”的新时代。
1732年,象限仪成为海上航行的必备仪器。25年后,坎贝尔船长把象限仪弧度扩大,可以量120度的夹角,象限仪演变成了六分仪。这个测量纬度的理想仪器,既方便携带,又可以在摆动着的船体上观测,所以直到20世纪40年代,六分仪仍被各国船只广泛使用。
纬度的问题解决了,经度的确立却一直悬而未决。该把哪一条子午线作为东西半球的分界线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很多国家把自己的首都或主要的天文台当做本初子午线,航海家们则选择某一航线的起点作为本初子午线,这种混乱持续了几百年。直到1884年的国际子午会议上,各国才达成共识,把穿过格林尼治的经线定为本初子午线。
不过,测量经度远比测量纬度困难,传统的计算方式一次就要花4小时,除非有可靠的海上定时器。在当时,怀表非常昂贵,还需要每天上发条,由于每个人上发条的习惯不同,很容易产生误差,因此怀表无法当做船上定时器。摆钟在陆地上可以长时间稳定运转,但在颠簸的船上则会剧烈摇晃,严重影响它的稳定性。
钟表匠约翰·哈里森发明了一种航海钟,里面的钟表构件几乎无摩擦,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颠簸摇晃,运行部件之间都保持着极好的平衡。它能够以任何一种形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准确地报出格林尼治时间,而且天气变化对它不产生干扰。这是由于在航海钟里,哈里森增加了一个叫做“补偿弧”的装置,它能够对平衡簧的长度作出调整,来适应因温差而引起的热胀冷缩,因此,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对航海钟没有任何影响。哈里森费时40余年,先后造出了5台航海钟,其中以“哈氏4号”最为突出,在“HMS迪伯特福特”号上接受测试时,从英格兰朴茨茅斯开往牙买加,航行了64天,只慢了5秒,远比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2分钟还少。
如今,这些伟大发明的辉煌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人们并没有把它们丢进历史的大海,很多船上依稀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未经勘测的茫茫海域再也不存在了,那种在惊涛骇浪之前,纵然是最优秀的水手也会刹那间不知所措、迷失方向的岁月远去了。

1707年,一支英国舰队在英国西南的锡利群岛遇到大雾,由于无法确定准确位置,4艘船撞上岛屿沉没,淹死1400多人。空前的海难震撼了英国,让英国政府意识到测定精确经度的重要性。171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经度法案》,悬赏高额奖金征求能解决经度问题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