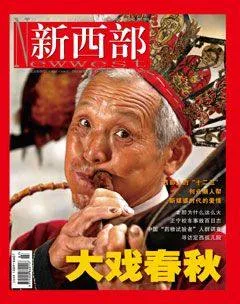杨海潮:行吟在路上的歌者
他不通乐理,不识简谱,却写出田震的《干杯,朋友》、《月牙泉》和俞静的《楼兰新娘》等流行音乐经典;他对体育运动并无兴趣,但CBA联赛主题曲《相信自己》及中超联赛主题曲《超越》,在他笔下浑然天成,激情四射。一个“70后”的奋斗史,成为这个社会由清纯走向物欲横流的现场记录。
生在70年代对杨海潮来说是幸运的,那个纯真的年代送给他一颗纯真且充满激情的心。
从《楼兰姑娘》到《干杯,朋友》,再到《相信自己》……一首首歌红了,而杨海潮依然沉默。
2011年的杨海潮除出了一本书,其他的日子都跟以往一样,“基本靠做广告谋生”,偶尔也外出和朋友旅行、做慈善。
但是,好听的歌没了!是不是他再也无法相信自己?抑或再也没了20年前“高五”学生闯京城的激情?
一把钢镚闯京城
1992年,自嘲自己是“高五”学生的杨海潮再次高考落榜。
“那时大学还没有扩招,高考还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对于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还是一个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杨海潮的父亲一直期望自己惟一的儿子能通过考大学来“光祖耀宗”,但他最终还是失望了。
与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后,杨海潮决定离家出走。
那时的孩子是没什么零花钱的,身无分文的杨海潮来到了朋友程光进的家,得到了朋友慷慨激昂的勉励,和一堆5分钱的硬币。
杨海潮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的流浪。“当一百多个硬币在我身上叮当乱想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形容人穷时要用‘穷得叮当响’这句话了。”
杨海潮站在宝鸡火车站,一脸茫然。用这一堆5分钱的钢镚所能到达的地方,绝不是他梦想所要去的。“站在站台上,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自己想去遥远的地方,至于想去干什么,也没想明白,只是觉得自己会唱歌,在我们学校也是号称四大歌王之首的,应该不会饿着的吧?于是我决定,只要是停在这个站台上的火车,不管去哪里,我都上!”
杨海潮等来的这列火车,是到北京的164次。直到今天,杨海潮依然认为他当年挤上的那趟火车可能是世上最挤的火车,“世上还能有这么挤的火车?车上密密麻麻全是人脑袋,站台全是拼命想上车的人。”
火车终于挤上去了,没买票的杨海潮又开始担心查票,好在一路都没人问他。
“说来有些可笑,我发现自己会写歌,还是这次出走北京。那晚在天安门广场上,气温零下8度,还刮着大风,饥寒交迫,我都觉得那晚可能会活不下去了。在这种环境下,我写出我人生的第一首歌:‘我头枕着伤痛,身上盖着梦,蜷缩在异乡的街头,幻想成功。我吞咽着泪水,咀嚼着寒风,面对无边的暗夜,编织着光明……”这就是我人生写出来的第一首歌的雏形,后来完成后定名为《淘梦者》。那一瞬间,我觉得写歌也并是不太难的事,我就决定我以后开始写歌吧。”
但对杨海潮来说,此时的饥饿和寒冷已经完全压倒了他对首都的一切新奇和向往,反倒是“回家”的念头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第二天一早,杨海潮在警察的指点下,来到了北京市民政局,在一个名叫“人民信访办公室”的房间里拿到了回家的车票钱。
“工作人员问清我父亲的姓名和单位后,在电话里给我父亲说,孩子回家后尽快把车票钱寄来,父亲在电话里由衷地感谢北京市民政局。”杨海潮说。
几年以后,杨海潮创作的《干杯,朋友》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天空是蔚蓝的自由,你渴望着拥有,但愿那无拘无束的日子将不再是一种奢求……”
可对于一个向往着心灵自由的年轻人来说,现实似乎永远是无边的桎梏。“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你得到想要的生活了吗?我还是只能以苦笑作答,我知道,在永无止境的欲望面前谈心灵的自由,简直就是妄想,而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的青春大半已逝。”
摆地摊的灵感
2011年11月29日,杨海潮在自己的微博中写到:“互联网真好,离家两千里却在一指间。突然很想白鹿原上的姥姥家,这条路小时侯每年都要走几回,一上到原顶,左边是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往北接着是汉文帝夫人窦太后陵和他本人的灞陵。文帝是著名的孝子和模范丈夫,陵墓如此安排取‘负妻背母’之意。南陵顶上视野辽阔,古都长安尽收眼底,想白鹿原了。”
1992年的秋天,杨海潮带着女友也曾来到白鹿原边他最喜欢的地方—薄太后陵。高考的又一次失败,父母对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是深深地失望了。
“父母也知道我整天在创作歌曲,可在他们看来,这跟我每年都信誓旦旦地要考上这大学那大学一样,不可信。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就是总喊着“狼来了”的那个孩子。每次有新歌写出来,我都会兴奋得无以名状,在家里扯着嗓子高唱,看得出爸爸很讨厌我这样。”
尽管还想离开宝鸡,但杨海潮还是想首先学会在最底层生活。他拒绝去父亲单位上班,开始在城镇之间摆地摊。“什么八鱼,石羊庙,虢镇之类的地方,只要是物资交流会之类的热闹场所,都能看到我的身影出没其间。”
后来,杨海潮在北大给同学李琪讲起自己如何创作的《楼兰新娘》:“有一天黄昏,我收了摊从虢镇往家骑,望着西边即将落下的太阳,突然一段旋律在我脑中出现,我就像被电击一般赶紧停下,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旋律太美了。我真的怕自己把这旋律给忘了,又骑上车子往家赶,一边骑一边唱着这首还没有词的歌,直到我确信自己再也忘不了它。回到家我一鼓作气,准备给它填上词,试了好几个题目都不满意,但这段旋律隐约有种西域的感觉,于是我在想到楼兰新娘这四个字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
填词的过程很顺利,他想起中学时一位来自新疆鄯善(古楼兰所在的地方)的女同学,“她那种来自西域的气质以及我对楼兰的神往,通过我的想象,幻化成了这首歌词。”
杨海潮把新创作的这首歌唱给女友、死党和朋友听,所有人强烈的反应让杨海潮明白,自己的音乐之路已经铺开了……
北大“编外生”
1993年春节,在老同学的聚会中,杨海潮遇到了李骐。大家被杨海潮的创作才华所倾倒,而在听到他想去北京时,在北大上学的李骐给他留下了详细的联系方式。
“只有在那个有梦想的年代,才会让北大能容纳我这样一个人,而且一待就是两年。”1993年春节一过,杨海潮给家人留了一封信后,又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北大对中国大都数的青年人来说,都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走进北大,夹杂在这样一堆状元探花们中间,杨海潮有些自惭形秽,但李骐的热情让他不再拘谨。
“卞智洪,高成海,周世一等人刚开始是因为我是李骐的朋友而对我照顾有加,后来大家熟了以后,发现兴趣相投,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3年前后,中国的流行音乐进入了一个空前繁盛的年代,唱片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了。杨海潮跟众多音乐创作爱好者一样,一家挨一家向唱片公司递上自己的作品,却四处碰壁。
“当时我连一点微弱的希望都不放过,听到谷建芬和付林老师开了一个培训班,就去找他们了。”付林老师对他的《楼兰新娘》非常感兴趣,杨海潮也没有想到,后来这首歌经付林老师重新编曲后,唱红了全国,并上了春晚,获得了中国音乐电视大奖。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才是这首歌的“父亲”。
但这已是后话。当时漂在北京的杨海潮不断碰壁,便对自己的音乐水平有了怀疑,恰巧家里在宝鸡的一家化工厂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他就回去老老实实地上班了,成为父母和周围人眼中的“正常人”。
然而,这种“正常”现象只存在了非常短的时间。“1994年春天来的时候,我的梦想也苏醒了,我又踏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正是在广州时,杨海潮在央视第六届“通业杯”全国电视歌手大赛上看到了参赛歌曲中有《楼兰姑娘》几个字,心里一惊:怎么这歌名和我的《楼兰新娘》就差一个字啊?赶紧看字幕,上面写着:杨海潮原词,付林改词作曲。”
杨海潮狂喜不已。回家,北上,这是他当时立即作出的决定。
“黄燎原的汉唐文化公司看上了你的《楼兰新娘》。”这是杨海潮到了北京后得到的第一个好消息。见到付林老师后,他也得到了《楼兰新娘》的词作者一半的稿费500元,“获奖证书只有一个,我没有好意思要。”杨海潮说。
1995年的夏天,李骐他们毕业了。在火车站送走一个又一个朋友的时候,杨海潮脑海里突然就有了这样的句子: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一醉到天尽头。也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再没有停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回到宿舍,杨海潮为这几句词配上了简单的和弦声,然后唱给卞智洪听,两个人都觉得非常的好。
这首半成品的歌,成了杨海潮在北大最后的作品,也是当时所有离别的人最真实的感受。
2011年1月7日,久违的内地乐坛大姐大田震出现在杨海潮新书《干杯,朋友》(流浪北京的日子)发布会现场。凤凰网COO李亚、英皇星艺副总包胡尔查、音乐人栗正也到现场。
“当时我刚看到海潮的时候,他就是一民工样子,还以为是电工呢,但是听到《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小样时,我立即就被打动。”田震对现场的观众讲起了两人的渊源。
上世纪90年代的歌手和音乐人,大都没有什么经纪人,“走穴”是很多人生存的方式之一,包括像田震这样的大腕。一场演出,基本就是把参差不齐的歌手混在一起,唱些当下流行的或是观众要听的歌,钱一到手,大家就散伙了。
杨海潮也以歌手的身份参加一些这样的演出,有时出场的服装都是借别人的。
那时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极低,只要能吃饱饭、写歌、看书,就满足了。“那段时间我写了不少的歌,写歌的视角完全跟着我当时的兴趣走。我对西域非常着迷,于是写了《月牙泉》、《水、草、骆驼》、《嘉峪关的回忆》、《艾玛和妈妈》等歌曲。”
杨海潮对月牙泉的了解来自李骐,李骐去过一次敦煌,回来就给杨海潮描述月牙泉。“那个夜晚我对月牙泉的想象,成为我日后写出《月牙泉》这首歌的最初灵感。”后来,有很多次能去敦煌的机会,但杨海潮都放弃了去看月牙泉。这个习惯了美好想象的男人,或许是害怕现实将这种想象打破吧!
但是,《月牙泉》一度根本无人问津,直到遇到了田震。
第一次听到杨海潮作品的田震,完全无法把眼前戴着眼镜、衣着如同民工的人,与这一首首如甘泉般清灵的作品划上等号。田震也因为《干杯,朋友》、《月牙泉》红透大江南北。但杨海潮的名字,却并没有如他的歌曲一样家喻户晓。

为”70后”精神立传
杨海潮的《干杯,朋友》(流浪北京的日子)一书发行时,有一段这样的推荐文字:他不通乐理,不识简谱,却写出田震的《干杯,朋友》《月牙泉》、俞静的《楼兰新娘》等流行音乐经典;他对体育运动并无兴趣,但CBA联赛主题曲《相信自己》及中超联赛主题曲《超越》,在他笔下浑然天成,激情四射。他曾在音乐学院的初试中被淘汰,多年后,他的作品成为众多艺术院校考级曲目。他没有学过一天广告,但他的广告作品频频得奖,成为许多大学广告专业的范例。呈现一部“70后”坚强不屈的奋斗史,是一段这个社会由清纯走向物欲横流的现场记录。
其实,这本书的由来非常偶然。
2006年11月,杨海潮看到许多人将自己的故事写在网络上,他寻思自己刚来北京时的一些事儿也非常有意思,于是在天涯社区注册了“喀纳斯湖怪”的ID,开始将自己从一名高考落榜生到音乐人的20年坎坷经历一一记录下来。慢慢地,关注他的在线读者越来越多。著名评论人“十年砍柴”看到后,将此书稿推荐给了出版社。
十年砍柴非常钦佩这个只比自己小12天的同龄人。“我和海潮,或许更多的同龄人,年少时都有一个长安梦。我的实现方式,则是循古人的路径,雁塔题名,获得进城的资格。而海潮让我佩服和尊敬的是,他在连续高考落榜后,腰揣5元钱的硬币,敢于逃票来到陌生的“长安”。相比较而言,我的梦更为平庸与现实。”
更让十年砍柴感兴趣的是,从杨海潮的文字里,他也感受到了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对过往时光的怀念和不舍。“感谢海潮的文字让我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早期那段时光,大学‘扩招’还没有开始,‘房奴’更是一个未来的名词,理想主义不像今天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靠自己的奋斗可以改变命运的信念还不曾被怀疑。因此,北大的校园才可能接纳他这样一个‘六无人员’,他的身边也才可能聚集起那么多忧道不忧贫的同龄人,身无半文却一点也不影响歌唱理想憧憬未来的心情。也因此,我这样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农家子弟能分配到北京,实现我的‘长安梦’。”
而杨海潮表示,这本书并不是北漂成功史或者中年人的回忆录,而是为一种人甚至一代人的精神做传。他期待多年以后,这本书会成为记录一个时代思想变迁与文化形态的文本。
“读完这本书的人应当相信,在任何一个时代,哪怕是物欲横流、人情浇漓、世风日下的时代,有诗人气质的人,依然有生存下去并获得成功的理由与机遇—只要能坚守,不放弃。”他说。
2010年,杨海潮收到各地使用其歌曲的版税共25000元,他说中国的音乐创作人员,一年如果版税收入上万,就能排进全国前50名了。
对杨海潮来说,这样的变化或许会成为他继续坚守的一个重要理由。而这样的坚守中,也或许能使他走向音乐创作的另一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