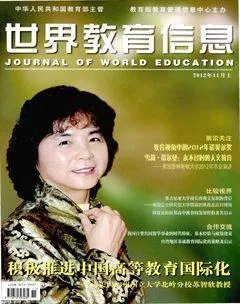欧罗巴:远见之神
时下,由欧债危机引发的种种困境严重危及“欧盟”这个一体化组织。它渐现支离破碎,甚而日趋分崩离析。正值此际,幸运之神不期而至——欧盟问鼎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谈及欧盟的成就,人们往往会关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已实现的目标,如跨国界自由流动、欧元、自由落户以及统一的宪法,而忘却教育一体化进程中的种种艰辛。诚然,欧洲教育一体化进程虽未能尽如人意,却可圈可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势必依傍欧洲教育空间之构建。
一、迷惘的一代
2012年10月16日,就在欧盟获奖喜讯传遍全球的第4天,中欧基础教育国际化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与会者既有芬兰中小学校长联合会终身名誉会长Jorma Kalevi Lempinen,也有德国中学生。会上,德国学生即兴放歌,激情万丈,博得掌声阵阵。而时下,一首葡萄牙歌曲《我有多蠢》(Parva Que Sou)红遍欧洲大陆,唱出一代欧洲青年人的心声——无能、无助、无奈和无望。无病呻吟乎?
据欧盟统计署(Eurostat)2012年10月1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8月,欧元区17国失业人口高达1800万,失业率攀升至空前的11.4%,且形势还将持续恶化。其中,尤为突出的是25岁以下青年人的失业问题,欧盟27国青年失业率已达22.7%。在西班牙和希腊,青年失业率竟突破了50%。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的青年失业率均徘徊在31%~36%的高位。无论是经合组织(OECD)还是国际劳工组织(ILO),都无法预测欧洲经济短期复苏之可能。10月23日,欧洲优化生活与就业境遇基金会(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发布的报告《既未就业亦未就学:欧洲的特征、代价和政策应对》(NEETs-Young People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Characteristics,Cost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Europe)指出,欧洲的未来须由9400万青少年来肩负,然而,当下的经济危机正在摧残这股希望。去年,欧洲15~24岁年龄段的青少年中有750万既未就业亦未就学,即所谓的NEETs(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此外还有650万25~29岁年龄段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2011年,为失业提供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疲软的购买力使欧洲遭受了高达1530亿欧元的经济重创,约占欧洲GDP的1.2%,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增幅为28%。这些仅为保守的估算,由此激发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尚未顾及。其中付出最大代价的自然是南欧各国,希腊的财政损失占其GDP的3.28%;意大利的损失数额最高,达326亿欧元。而人口规模更大的英国、法国与德国分别为180亿、220亿和155亿欧元。与2007年(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夕)相比,青少年失业所造成的经济代价在希腊上升76%,西班牙45%,罗马尼亚最高,为78%。OECD就业政策负责人斯蒂法诺(Stefano Scarpetta)甚至危言耸听道,阿拉伯之春或许会在欧洲大陆上演。
ILO于2012年9月4日发布的报告《全球就业展望:青年劳动市场前景暗淡》(Global Employment Outlook: Bleak Labour Market Prospects for Youth)再次为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南欧诸国敲响警钟。报告显示,中东与北非地区的全球青年失业率最高,分别达26.4%和27.5%,欧洲紧随其后,亦高达16.9%,远高于东亚地区的9.5%和南亚地区的9.6%。为欧洲青年高失业率推波助澜的无疑是南欧诸国。通常情况下,高等教育是青年失业的缓冲器。然而,南欧高校却自顾不暇。例如,为实现1000亿欧元紧缩政策,西班牙保守党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4月中旬颁布《公共教育体系合理化紧急措施》。此项举措承担着整项紧缩政策1/5的使命。举国上下,大中小学,人人自危。若此举真正落实,1/3的高校职工将失业。卡洛斯国王大学(Universidad Rey Juan Carlos)的教师竟从自动取款机上惊闻解雇——没有任何预兆,学校汇给这些教师每人1万欧元的遣散费。在希腊,去年夏天大学生示威的景象仍历历在目,1900余所中小学校面临关闭。今年3月的债务紧缩政策导致高校在希腊银行(Bank of Greece)储备降级,缩水量达到1.4亿欧元。课时缩减,课程挤压,实验室因缺乏实验设备与材料而无法展开教学与科研,食堂因拖欠员工工资而关闭,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已成奢侈之举……高校认为,财政预算自2009年以来至少已减半。大型高校尚可依赖特别账户渡过危机,小型高校只得听天由命。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高等教育人才。国家奖学金管理中心(IKY)2011-2012学年终止了针对博士生和参与其他学术深造项目的学员的奖学金;希腊高校去年竟未新聘一名教学或科研人员。2010年10月成立的失业科研人员组织今年3月份向教育部疾呼,等待若遥遥无期,这些才俊只得远走高飞。此举可谓雪上加霜。希腊马其顿大学(University of Macedonia)经济地理学教授Lois Labrianidis根据一项调查得知,13.9万希腊学者散布于世界各地——这绝非本国人才剩余的结果。希腊高校因师资短缺无法培养创新人才,进而导致产业低水平运作,国家财政状况由此低迷不振,恶性循环。
趋势研究院(Trendence)最新发布的欧洲最大规模高校毕业生调查显示,南欧高校工科毕业生出国寻求谋生道路的意向显著,在希腊几乎占50%,西班牙约为40%,意大利约为37%。毕业生通常涌向欧洲经济首强德国,但其学历在他乡备受冷遇。于是,南欧学子未雨绸缪——与其国内求学国外就业,不如直接留学。由欧盟资助的院校报考网站“学习门户”(Studyportals)发现,南欧四国报考欧洲其他国家高校的人数同比陡增150%。此需求与南欧四国15~24岁年龄段青年失业率成正相关。2011年,欧盟留学意向增幅最大的四国——意大利(181%)、希腊(162%)、西班牙(156%)和葡萄牙(140%)——青年失业率恰恰最高:意大利(36.0%)、希腊(52.3%)、西班牙(51.2%)和葡萄牙(35.8%)。而欧盟27国这两组数字的均值分别为92%和22.6%。
ILO5月22日发布《2012全球青年就业趋向报告》(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2),称南欧四国青年为“迷惘的一代”,甚至将其打上游手好闲与自暴自弃的烙印。而OECD亦指出,南欧四国因人才短缺而丧失全球经济竞争力。
二、裂变的大陆
以区域一体化实践名留史册的欧盟,在均衡发展方面却不尽人意。欧盟统计署2012年3月12日公布的欧盟各区域2009年基本经济数据显示,2009年,欧盟GDP总产值为11.75万亿欧元,人口为5.05亿,年人均GDP为23500欧元。英国内伦敦(Inner London)高踞首位,年人均GDP为7.8万欧元,是欧盟年人均GDP的332%;而保加利亚的赛维罗萨帕登地区(Severozapaden)屈居末位,为6400欧元。欧盟最富和最穷的地区年人均GDP相差竟达12倍之巨。东欧诸国劳动力成本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反而成为欧盟制造业的新增长点,对于促进欧盟人力资本流动的良性内循环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传统的欧盟版图,即欧盟东扩之前,显现的却是一幅南弱北强的经济格局。欧元的诞生重货币统一而轻财政契约,因而无以填平南北贫富的鸿沟。债务危机骤起,南欧各国危在旦夕。南欧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其国名英文首字母组成“PIGS”,国际舆论谑称为猪猡四国。
南欧四国使欧盟深陷分崩离析之窘境。恰在风雨飘摇之际,殊荣从天而降。2012年10月12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当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Thorbjoern Jagland)宣布欧盟为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喜讯时,不仅在场记者嘘声不绝,欧洲一片哗然,全球各界尤为莫衷一是。
欧洲的裂痕不仅显现在经济层面,亦在教育范畴。在欧洲,人们生长与生活的地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教育机会及其成就。这是欧盟9月14日发布的报告《警惕差距:欧盟各区域间教育不均等》(Mind the Gap:Education Inequality across EU Regions)之结论。该报告揭示:严重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不仅遍布于成员国之间,甚至出现在一国境内。
这份报告由设在法国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院(INRP)的教育与培训社会观察专家网络组织(NESSE)为欧盟委员会撰写。报告采用欧盟统计署数据,从地理与教育两大维度展开研究,即视欧盟统计署“地域统计单位命名法”(NUTS)的欧盟27国271个二级地域单位为教育的地域基本单位①,并参照“教育国际标准分类”(ISCED)的7个层级②。报告通过100多幅图表形象地展示了教育的地域差异,并分别列出每项指标的十大最佳与最差区域。欧盟各国之间的教育不均等现象如下:
?誗各级各类学校在读学生占总人口比率高的地区是北欧和西欧,尤其是芬兰、瑞典、比利时和爱尔兰,比率低的地区为德国东部、意大利北部、东南欧以及西班牙西北部和葡萄牙。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最高(35.93%),保加利亚的赛维罗萨帕登地区最低(14.4%)。
?誗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南部以及荷兰、丹麦和瑞典南部是义务教育阶段在读学生占总人口比率高的地区,比率低的地区是意大利北部和东南欧。
?誗从最高学历为初中者占15岁以上年龄段人口的比率来看,高比率主要集中于南欧,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低比率则出现在英国、中欧和东欧。葡萄牙的阿连特茹大区(Alentejo)最高(78.36%),捷克的布拉格最低(10.69%)。
?誗就初中学历者占25~64岁年龄段人口比率来看,高比率现象主要出现在南欧,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比率较低的则是英国、中欧和东欧。捷克的布拉格最低(3.2%),葡萄牙的首都地区(Centro)最高(77.9%),而且比率最高的10个区域全部集中在南欧四国。
?誗25~64岁年龄段拥有高中文凭的人口比率方面,高比率地区为东欧,低比率地区为南欧。捷克的中摩拉维亚地区(St■ední Morava)以77.1%位居榜首,葡萄牙北部以11.4%排列榜尾。
?誗在比利时、意大利、瑞典和芬兰,义务教育完成后接受非高等教育的学生占15~24岁年龄段人口比率高,低比率则出现在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法国。
?誗以15岁以上人口完成大学学业的比率来排序,比率高的地区首先是英国、比利时和荷兰,其次是西班牙北部和塞浦路斯,而低比率地区为意大利、葡萄牙、中欧和东欧。伦敦市中心比率最高(41.82%),捷克的赛维罗萨帕登区最低(7.03%)。
?誗在德国、英国和荷兰,人们能就近(路途花费时间在1小时之内)接受高等教育,而在东南欧、瑞典北部、芬兰、波罗的海、西班牙、丹麦和法国,则需长途跋涉。
?誗以参与终身学习者占25~64岁年龄段人口比率来考量,英国、丹麦、芬兰和瑞典的参与率较高,低参与率则出现在东南欧。丹麦的首都地区(Hovedstaden)最高(19.2%),保加利亚的赛维罗萨帕登区最低(0.27%)。
尽管欧盟每个成员国均有义务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但教育在地理空间的不均衡现象仍根深蒂固,由此,在一体化道路上渐行渐远的欧盟被撕裂得支离破碎。这是第一份该类报告,描绘出欧盟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图景,并呼吁各成员国为构建机会均等的教育体系尽心尽力,共同采取举措并制定政策。此外,欧盟读写胜任力高级专家小组(EU High Level Group of Experts on Literacy)在今年世界扫盲日(9月8日)宣称,欧洲尚有1/5的15岁学生和成年人不能掌握日常生活、学习与工作所必需的读写能力,而且,这些缺乏必要读写胜任力的学生绝大多数并非移民。
三、一场“盖浇饭”盛宴
该报告发现,就教育不均等的方式、程度及影响,欧盟各区域间的区别明显。综合各项指标来看,欧洲南北差异悬殊。不仅南欧青年被视作“迷惘的一代”,在教育领域,南欧四国亦成为欧洲大陆“迷惘的一角”。正因为落伍,南欧各国奋起直追,而问题恰恰由此凸显。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过犹不及,成为南欧四国人才流失之祸端。欧盟大家庭中经济偏弱的西班牙,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竟高于欧盟均值。刻意追求学术化,大量职业教育专业被无端纳入高等教育体系,而大学课程仅有两成与实践相结合。重理论而轻实践,重高教而轻职教,立志从事技工职业却往往被打上失败者的烙印,勤工俭学亦受鄙夷。高校毕业生过剩必然导致高等教育贬值以及人们对本国教育制度的失望。在希腊,只有两成工科大学生认为,学习能够为就业作准备,这一比例在3年内下降了10个百分点。94%的商科大学生和98%的工科大学生为其职业前程担忧。这种忧虑也体现在86%的西班牙大学生身上,超欧洲均值。而本国学生的背井离乡使深陷欧债危机的南欧四国雪上加霜——本国优秀生源在全球竞争中流失,尽管OECD在2005年便通过在欧洲实施“评议区域与城市发展中的高等教育”(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in Regional and City Development)项目来激活造血功能,即以强化高校、城乡与企业间的纽带来推动人才培养、城乡建设与经济发展,却收效甚微。媒体不失时机地揶揄道,欧债危机把以居家著称的南欧人打造成为欧洲最富流动性的青年。当然,欧盟司法、自由与安全委员会2007年9月13日推出的“欧盟劳工蓝卡”(Blue EU Labour Card)无疑推动了人力资本流动性的提升,但是南欧青年才俊的此番流动实为被迫之举。
其实,人员自由流动乃欧洲一体化之引擎。早在1999年6月19日,欧洲29国教育部长便在意大利中部城市博洛尼亚(Bologna)签署《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宣告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次年正式启动。该进程旨在构建一个共同的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显然,博洛尼亚进程是欧洲军事、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在文化教育层面的延伸,更是欧盟应对全球化之举措。其意图无非是在人才全球争霸中立于不败之地。学界宣称,这是欧洲200年以来最宏大最深刻最彻底的一场高等教育改革。然而,欧洲大学联合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2010年出版的一份调查报告却发现,只有15%的欧洲高校认为博洛尼亚进程会对本国高校今后5年的发展产生首要影响。该联合会的另一项调查显示,49.3%的高校遵循的是国家方针,23.7%强调地方特色,只有9.2%视欧盟为瞻。2010年3月11~12日,欧洲46国教育部部长在博洛尼亚十周年庆典上通过《布达佩斯-维也纳宣言》(Budapest-Vienna Declaration),旨在为未来10年制定行动规划。之前,该联合会出台的《趋势报告2010:欧洲高等教育变革十年》(Trends 2010: A Decade of Change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表明,在821所成员高校中,认为博洛尼亚进程具有积极意义的仅为58%,38%持观望态度。这印证了由欧盟委员会于2008~2010期间资助的两份评估报告《欧洲教育区实施首个十年:博洛尼亚进程独立评估》(The First Decade of Working o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The Bologna Process Independent Assessment)和《高等教育改革在欧洲的进展:治理改革》(Progress i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cross Europe: Governance Reform)的结果,即博洛尼亚进程所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并没有深入到院校层面,所期待的高教改革如高校自治与高校体制的效能提升之间缺乏显著性关联,反而导致大学信息系统官僚化地管理着学习的每个阶段,持续评估成为高校无法承担的负荷。而且,博洛尼亚进程的改革效应也仅停留在形式化层面,如学制转换、欧洲学分引入等,一旦涉及课程与教学,便遭遇到各国现有的学术传统与大学文化的抵制。欧洲物理学会于2008年考察了24个博洛尼亚进程成员国的152个物理本科专业,这是首次在全欧洲范围内对博洛尼亚进程在某个特定学科产生的影响的调查,其结果证实了上述观点。
(一)博洛尼亚徒有虚名?
宣言以“博洛尼亚”来冠名,并非空穴来风。建校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而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千年古城,或许是因为古老,在后现代社会已不再宜居。目前城中居民不足38万,经历历史沧桑却不失精致的博洛尼亚却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10万名学生。该城不仅以大学闻名,还有特色饮食。无论何种主食,面条、米饭还是土豆,均浇上以肉糜与番茄酱熬制而成的汁——博洛尼亚汁(Ragù alla bolognese),与中国的盖浇饭类似。而欧盟推行的各项举措岂不是给各国特有文化与制度浇上一勺勺“博洛尼亚汁”?博洛尼亚进程岂非最为名副其实的一勺“博洛尼亚汁”?确实,专家于博洛尼亚进程启动之际便断言,该进程仅仅是个“自上而下”(top down-process)而非“由下往上”(bottom up-process)的实践过程。甚至能否在2010年实现博洛尼亚理想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国政府借一体化之东风,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自身的体制改革。事实上,2009年在比利时鲁汶(Leuven)召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部长级会议(EHEA Ministerial Conference)便把创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期限推迟至2015年,以至于批评者把《鲁汶公告》(Leuven Communiqué)视作博洛尼亚进程破产宣告。这种怀疑与批判甚而激化为对欧洲一体化的全盘否定。
(二)欧洲教育一体化进程,一场盖浇饭盛宴?
博洛尼亚大学于1088年建校时,欧洲大陆尽管战乱不息,分合交替,但“民族国家”概念尚未形成,人才的流动性与自由度远甚于20世纪。可见,欧盟的真正危机并非可紧急化解的债务,而是对历史遗产的忘却。欧盟在教育一体化上已取得举世瞩目之成就,其项目之命名便可展露对历史遗产的顶礼膜拜,如苏格拉底计划、伊拉斯谟计划、达芬奇计划、夸美纽斯计划。
博洛尼亚进程的命名则更能彰显欧罗巴精髓。博洛尼亚方案构建之初,民族国家意识便急于作祟。法国认为,西方最古老的大学应该是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成立于1198年,而且有教皇手谕为证。何况,巴黎大学还是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学之母,从一开始便力图将其打造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学府。而博洛尼亚大学的奠基却无从考证。于是,欧盟采取一贯的平衡伎俩。1998年5月25日巴黎大学800周年校庆之际,欧洲四架马车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教育部部长在巴黎签署《索邦宣言》(Sorbonne Declaration),并拟定《博洛尼亚宣言》。言下之意,博洛尼亚进程仅仅是《索邦宣言》的产物。至于这个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最终还是冠以“博洛尼亚”之名,主要旨在突显世俗的力量。当初,博洛尼亚大学就是从一所所小型的以教授世俗法为主的法学院发展而来,是对宗教势力尤其是教皇绝对权力的抗衡,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
四、述往事,思来者
自古希腊时代起,一个大一统的欧洲就以神话之形式而存在于欧洲人的意识之中,由此形成欧洲人的憧憬——一个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述往事,思来者”。诺贝尔和平奖青睐欧盟,不仅是对欧盟历史功绩的追认,如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而言,“欧盟及其先驱者过去60年一直致力于推进欧洲的和平与和解,以及民主与人权”,更是通过褒奖历史功绩以期重振雄风。饱经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欧洲人深知,作为欧罗巴精髓,人文主义、科学精神、民主意识须经由互为流动与平等对话来激活、保鲜及弘扬,就此,教育大有可为。今年4月26~27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部长级会议再次强调人才国际流动之必要性,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明潮暗流,澎湃涌动,当下的经济危机无以阻挡。同时,47国教育部部长签署《为好好学习而行千里路:欧洲高等教育区2020流动战略》(Mobility for Better Learning: Mobility Strategy 2020 for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为共同实现到2020年欧洲高等教育区内至少1/5的学生拥有国外学习或实习经历的目标而制定行动方案。此外,长期以来,欧盟拟定教育政策时与相关利益者形成对话与合作机制,它们有欧洲大学联合会(EUA)、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ESHA)、欧盟学生联盟(ESU)、欧洲家长联合会(EPA)、欧洲成人教育联合会(EAEA)、欧洲院校联合会(EURASHE)、欧洲大学终身学习联合会(EUCEN)、社区学院联合会(ACC)、欧洲青少年闲暇机构联合会(EAICY)、欧洲职业培训联合会(AEFP/EVTA)、欧洲职业培训机构联合会(EVBB)、欧洲培训与人力资源发展联盟(ETDF-FEFD)。
遵循“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中的“教育与培训2010工作项目”(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0 Work Programme)和后续战略的“欧洲2020”(European 2020)中的“欧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战略框架合作”(Strategic Framework for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以及2007年启动的“终身学习项目2007~2013”(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me 2007~2013)所展示的宏伟蓝图,构建一个共享的欧洲教育空间指日可待。
诚然,对于“病魔缠身”的欧盟,诺贝尔和平奖固然无法妙手回春,但其对欧盟的眷顾,全然可视作对欧罗巴精髓之高扬,亦为对欧盟追求“多元一体”(United in Diversity)之赞许,更是热盼欧盟再次为世界各大区域如东盟、非盟、阿盟的一体化乃至天下大同奉献范本。
欧罗巴(Europa),古希腊语意为“拥有先见之明的女神”,此番问鼎诺贝尔和平奖,不啻为溯本求源之机与高瞻远瞩之缘。■
注释:
①欧盟统计署的“地域统计单位命名法”(Nomenclature des unités territoriales statistiques/NUTS)把欧盟领土划分为6个层级,即民族国家(NUTS 0)、大型区域或省或联邦州(NUTS 1)、中型区域(NUTS 2)、小型区域或大都市(NUTS 3)、城镇集合体(LAU 1)、城镇(LAU 2)。欧盟区域的一级、二级和三级地域单位分别共有97个、271个、1303个,欧盟人口第一大国德国以16个、39个和429个占数量之最,而卢森堡和塞浦路斯,一个国家同时也是1个一级、二级和三级地域单位。
②“教育国际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ISCED)诞生于70年代,1975年在日内瓦召开的教育全球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上正式予以确认。该分类把教育分为7个层级,即学前教育(ISCED Level 0),小学教育(ISCED Level 1),初中教育(ISCED Level 2),高中教育(ISCED Level 3),中学后非高等教育(ISCED Level 4),高等教育(ISCED Level 5),博士生教育(ISCED Level 6)。2011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大会表决通过使用2011年版的分类(ISCED2011),把原先7个层级扩展为9个,即把原先的高等教育(ISCED Level 5)细分为短期高等教育项目(ISCED Level 5)、本科生教育(ISCED Level 6)和硕士生教育(ISCED Level 7),而原先的博士生教育(ISCED Level 6)改为博士生教育(ISCED Level 9)。此份报告采用的仍然是1997年版的分类(ISCED97)。
参考文献:
[1]Andrée S.,Hanne S..Trends 2010: A Decade of Change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R].Brussels: EUA,2010.
[2]CHEPS,INCHER,ECOTEC.The First Decade of Working o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The Bologna Process Independent Assessment[R].Twente: CHEPS,2010.
[3]CHEPS,INCHER,NIFU STEP. Progress i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cross Europe: Governance Reform[R].Twente: CHEPS,2010.
[4]Crosier,D.,Purser, L.,Smidt, H.. Trends V: Universities Shaping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An EUA Report[R].Brussels: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2007.
[5]ILO.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2[R].Geneva:ILO,2012.
[6]ILO.Global Employment Outlook: Bleak Labour Market Prospects for Youth [R].Geneva:ILO,2012.
[7]Kehm,B.M.,Eckhardt A..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ologna Process Reforms into Physics Programmes in Europe[M].Mulhouse:EPS,2009.
[8]Mascherini,M.,Salvatore,L.,Meierkord,A.,Jungblut,J.M..NEETs - Young People 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 Characteristics, Cost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Europe[R].Luxembourg: EU,2012.
[9]NESSE.Mind the Gap: Education Inequality Across EU Regions[R]. Luxembourg: EU,2012.
编辑: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