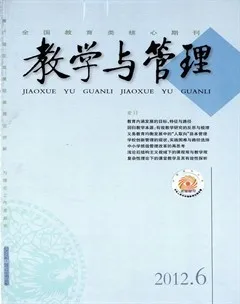教育内涵发展的目标、特征与路径
随着教育意识水平的提升,社会各界对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将生存和发展作为教育的目标而要求教育回归生活。由此,各阶段的教育发生着质的转变,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并提出内涵发展的理念力求渗透到各阶段的教育实践之中。教育内涵发展是学校从内部出发,依靠结构优化、人文突显、效能提高和科学管理等,引发学校发展原动力,从而促进学校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其发展的目的被外界强加的终极目的所左右,并非将教育的“应然”寓于教育过程和教育活动当中,与教育本质背离。提倡教育的内涵发展的价值在于依靠现有资源唤醒教育的人文精神,逐渐摆脱社会、政治所决定的外在虚无目的的束缚与制约,实现教育的终极关怀,即回归教育自有的立场。
一、教育内涵发展的目标:本质的回归
在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和升学为目的的教育政绩观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应试教育”的倾向与素质教育的要求相悖,违背教育规律,淡化了“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成长与发展,并不是成人经验的强加,虽然教育无可选择地要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也受制于诸如制度、规则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教育所应有的“本然”的东西不应由于社会历史条件而发生“本质”的背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育作为一项既定的社会活动总是从某种先定的观念或理念出发讨论如何培养出理想的个体,这就必然或多或少地使教育带有功利性。生发于体制内的各种外在教育之物,都在利益的左右下被打上了炫目的光环,当教育依附于其时,就可能沦为达到这些外在之物目的的工具,或为统治阶级所独有,或为某些团体所控制,给予学生的东西都被赋予了极强的压制意味,致使教育变成制作“人”的模型的流水线,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和能言的鹦鹉一般,缺少了自动的能力。
教育本质的“应然”与“实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会有所偏颇,但作为培育、提高全体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教育一旦忽视“人”的存在,很多人性的内容在教育中就会严重缺失或是受到扼制。教育是源发于人的生活需要的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游离于生活之外,而是天然地与生活联系在一起[1]。然而,现代物质世界的充斥下,教育的工具性特征日益明显,教育价值观的偏差无疑助长了“应试教育”的倾向,教育除了分数、成绩、升学率,还能剩下什么?升学的功利追求使得本来应该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无奈选择了“升学为要”,将“人的全面发展”变成了考试分数的提高,教育与生活的割裂日趋膨胀,已失去了“现实世界”的光辉,留下的仅是与考试相关的课程、活动、管理、教学。
教育内涵发展强调的是由内而外的作用机制,将人的培育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教育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的角度重申“实然”教育之人性化的一面,其目标是将受制于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重新拉回跑道,还教育以本来面目。因此,从理念的源头上说,教育本质的回归首先应重建教育观。这就要求教育逐渐摆脱应试的束缚,依靠观念的变革使教育走出本质目的之外的困局,给予学生一个适合其发展的更为广阔、美好的纯洁环境。其次,教育本质的回归需要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理念为现行的教育提供启示,即如何为学生创设儿童眼前生活与教学内容和谐统一的平衡环境,使学生的学校生活与学校给予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因为“生活世界”是每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基石,虽然不及经过抽象、归纳和整理以后的“课程知识”那么有条理,用记忆、考试的方式无法把握,只能用非理性的方式把握它,但在对其进行体验、品味、揣度、想象与领悟的过程中,人生的乐趣、价值和意义就蕴藏在其中[2]。如果学校能够将“现实世界”的养料注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其价值不仅仅使得教育走入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其理念、方式上的先行,对于摆脱应试教育的“怪圈”是一个强大的力量。
二、教育内涵发展的特征:学生的终极关怀
学生的终极关怀即学生生命价值的展现。学校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校中的一切活动及必要措施都应该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服务。现行教育中充斥的技术和工具理性太过浓烈,以至于过早地抹杀了学生的“人性”,其生命的价值受到压迫和摧残。可以想象,学生在各种标准化的学校教育中的生存状态,其“生命”变得单一、简单、模式化。教育能否真正走上内涵发展之路,其特征是教育要使“人成为人”。学生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展现其生命力,使其生命价值不断拓展、增殖的过程。作为精神的存在,生活的展现虽然周期较长,但在学校教育中给予与其发展相适应的条件,步入社会的洪流中亦有极大的机会得以最终实现。换句话说,教育提供的是学生生命展现的基石,通过精心的、艺术的诱导唤醒“生命”。这一过程中,教育作为为现存社会培养新人的活动,秉承时代精神,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最佳方式。
教育的质的规定性就是直接指向人的身心发展,并对其产生影响,这是一般社会实践活动所不具备的。教育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它能把间接的“实践活动”的影响转变为对学生的直接影响,学生的生命价值就是在缤纷复杂的教育实践活动中逐渐实现的。在社会正在走向“后现代”的今天,人们所持有的主导文化理念与人才的价值观已发生变化,为适应这一变革必须反思工业社会对现代教育造成的影响,应将“人”的需要与价值作为教育的重心,摒弃以追求数量为目标的教育,使教育由“一元化”的应试的藩篱中解脱出来,走向更合乎教育实际和学生个性发展的多元化阶段,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
在践行这一展现过程中,首先应理解学生生命价值的展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使其保持生命力。相对于以外在目的决定的教育,内涵式发展模式下的教育更加注重过程,即关注学生在学校期间的生活状态、环境构建,且对学生的发展的作用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除了必需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外,将学生情感与能力的发展寓于教育与教学过程中,将现实生活简约于学校生活中,通过“体验”、“熏陶”等人文方式影响学生,而非“注入”。其次,学生生命价值的展现是教育所应持有的职责,其作用应是隐蔽的和潜在的。正如英国学者托马斯·摩尔所说:“教育是一门推断、引导或揭示一个人潜能的艺术……在最深层形式中,教育则是一门诱使灵魂从其茧中、潜在的烦恼中、隐藏的洞穴中显露出来的艺术。教育不再是学识、信息、数据、事实、技艺或能力的基础,而是一个发展中的直观事物,它就像一粒隐藏于泥土中的种子”。[3]学生的生命价值是看不着、摸不到的东西,学生自由、充分、独特的“生命场”依赖教育活动各主体间的交往与互动,依赖对学生当下心理状态及心理特点的关注。因此,学校场域中学生生命价值的展现是“细水常流”的,是在教育过程中所引入的“生活世界”的感悟和体味中“食人间烟火”的,这就要求教育中的一切要素与学生的生命发展相一致,充满浓烈的“生活性”。
三、教育内涵发展的路径:教学改革、文化重建与教师成长
1.以课堂教学改革为切入点
“外铄”教育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课堂教学,当前的课堂带有明显的预设性,场景、模式、目标等看似具有科学主义范式的意味,但长久演变而来的现实教学较少关注表现性目标、教学过程和师生互动等,学生的主体地位未曾得以体现,学生的生命价值在课堂中无以展现。事实上,新课程改革所提倡的生成式教学含有“生命”的内涵,强调多变、适时的教学体现着内涵发展的本质。因此,从教学角度而言,方式的变革是教育走向内涵的第一步。
首先,课堂教学中关注“人”的存在。传统教育的方式是灌输式的,教师一般作为课堂的主宰而独居主体地位,学生则扮演消极的听众角色。现行的教育将这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片面地强调“注入”与“填充”,学生的兴趣、现实的需要被抑制,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因此,内涵式的教育的课堂表现形式应是多样的,结构是不确定的。这就给予学生最大限度的信任,将人文与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生活整合起来,融于课堂教学中,进而使课堂的人文化教学与学生的需求结合起来,显现课堂教学中的“生命”关怀。
其次,教师的作用意义重大。课堂中的教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外,附有“育”的职责。这里的“育”是指“生命”的培育,且将“育”的过程置于教学与活动中,这就对教师提出较高的要求,如何准确把握学生的“生活世界”,如何将现实“生活世界”的内容融于课堂教学中且与知识传授相统一,是实现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也是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表现。因此,教师要关注课堂中的“生命”,关注课堂交往过程,关注生成。终究而言,课堂教学的彻底改革要求教师的自我反思。教师的自我反思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教师成为研究者”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反思,要在教学中开展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实验研究结果,循环往复的过程能归纳总结出合适的教育方式,使不同的学生所具有的差异性“生命”得以获得相同的结果。
2.以学校文化建设为根基
教育的内涵发展需要重建学校文化,而文化选择与文化定位一直是学校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在社会转型加剧的背景下,学校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逐渐脱离了原有的文化范型,没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新的可以依赖的文化范型,反而在“现代化”理念的冲击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用了技术领域的逻辑,如学校布局的精简与效率、学生管理的模式化、教师工作的绩效等,这种引入吞噬了学校文化最本质的内涵[4]。
首先,探寻学校文化的“应然”。学校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社会主流文化的缩影,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当前社会的主流文化表现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发展态势,是在一个变革时代所孕育出的新的文化形态,并逐步影响到各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欣喜的同时也暴露出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世态人心”,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成分被冲淡,学校也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变得摇摆不定,甚至失去了学校本应有的“应然”文化,生活与学习在无主流文化的学校场域中的学生没有了信仰。因此,教育内涵发展必须寻回学校所特有的文化,以学校文化的精神感染教师和学生,也只有在学校特有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氛围和前提下,真正的教育才能够成为可能。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应成为学校文化的根基。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学校文化的重建,理应是在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选择与合并的过程。目前,众多学校将学校文化建设列入学校发展目标的规划中,并有意识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学校文化。这一做法意在以文化的渗透力感染学校中的“人”,说明了学校管理层已意识到文化缺失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学校文化的重建,可以认为是重新建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实现的是多元无主流的学校文化向主流引领下多元的学校文化的转化;核心是回归与创新,其意义与价值关乎学校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
3.以教师专业成长为支撑
教育的内涵发展需要教师的内涵发展。教师内涵发展的核心是教师的专业成长,这里所指的专业成长是广义的,包含了知识与技能、教情感与态度以及师德等方面的内容,是与教育、教学相关的一切能力的发展与成长。在信息网络发达的今天,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化身和学术的权威,如继续束缚在几个学科和几本教科书之内的“专攻”,教师将不再因为其特殊的角色而被列入“专业化”队伍,也将失去人们所赋予的各种“光环”,教师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取,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形势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也只有自我的专业成长才能成为教育内涵发展的支撑。教师专业成长作为教育事业长久发展的重要支撑,其意义关乎整个教育事业的持续经营。狭义角度上的教师专业成长看似教师自己的事情,这仅仅是从教师个体的角度考虑,长远来看,是对教师“地位”的维护和教育事业的“名誉”的担忧。因此,以提高教师自身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可的角度诠释教师的专业成长,从根本上解决的是为什么发展的问题。
内涵发展目标中的教师专业成长,关键在于唤醒教师自我发展的情感。任何外在动因都无法替代内在驱动力对于教师发展的作用,教师本人在专业发展中的自我主体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教师作为学校“家族”的成员,本身在情感与意愿上带有为“家族”奋斗的心理,学校“家族”的成员也渴望家族能够延续、和谐、团结、富足。如何给学校的“家族”成员以归属感和安全感,并唤醒他们的责任感与荣辱感,关键在于“家长”对权力的使用,其中仁慈领导与德行领导将是善用权力的很好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刘旭东.“无立场”的教育认识与人的全面发展.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2] 刘旭东.论教育对生活世界的回归.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
[3] (英)托马斯·摩尔.心灵书——重建你的精神家园.刘德军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4] 柴江.学校文化建设的策略发展与路向选择.教育学术月刊,2011(2).
[5] 陈金干,丁步洲.区域初中教育内涵发展行动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付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