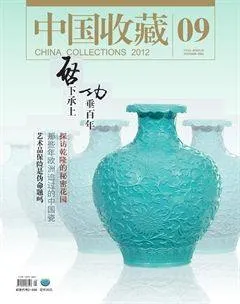楚马殷铅质小平钱趣谈
最近网上拍卖一枚日本泉家平尾赞平旧藏、《昭和泉谱》原物的“天策府宝”铜钱。此钱是五代十国楚国马殷称天策上将军、开天策府之后的铸币,是历代泉家梦寐以求的珍品。五代十国时期,连年征战,社会经济混乱,铜资源缺少,各割据政权铸铜钱较少,多沿用旧钱。楚马殷也沿用唐代钱名铸造自己的货币,如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乾封泉宝等,但其所铸钱多为大钱,且有明显特色。但是当人们都在关注马殷大型铜钱的时候,却也忽略了楚马殷故都长沙经常出土的铅质小平钱。
铸造背景
公元911年,楚马殷铸造了天策府宝铜质大钱,而对于马殷铅质小平钱和大铁钱的记录到公元925年才出现。《十国春秋》中记载:“同光三年(925年)冬11月⋯⋯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辏,湖南地故产铅铁,用都军判官高郁策,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又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泉宝,用九文为贯,以一当十,流行境内。”然而史书上并未说明铅钱是什么钱文,对于铅钱和铁钱之间的兑换也只是一句话带过去了,于是笔者带着一系列问题开始了对马殷铅质小平钱的研究。
史料上说,楚国早期曾经造了5000斤重的大铜柱,由此可知,湖南并不缺铜。那为什么马殷还要大肆地铸造铅铁钱呢?《十国春秋》中的兑换比例为铅质小平钱10枚兑换小平铜钱1枚,9枚铁质乾封泉宝为一贯。由此可知,1000枚铅质小平钱兑换9枚大铁钱或兑换小平铜钱90枚。笔者推测,这就是官方定价的“短陌”(以不足实数一百而当百钱使用的钱)。史载楚国当时的谋臣高郁提出了一个利国的政策被采纳,在楚国故都长沙城内必须用铅质小平钱和大铁钱,即小平铜钱只能用于兑换,但城内禁止使用。如此一来应对了唐末的铜钱荒,也使自己的铜钱流通得以保留,外部的铜钱还能留在境内。这样使当时楚国的经济得到稳固和发展,军事地位也不断提升。
铸造分期
据史料记载,在楚国境内有三处钱监,一处长沙城(潭州)、一处贵阳监(彬州)、一处在桂阳。自911年开始铸造天策府宝到951年楚亡,马殷铸造钱币的历史应该是40年。925年到951年铸造铅铁钱的历史是26年,而楚国存在时间总共是55年。因此,铸钱几乎贯穿了楚马殷时期的始末。笔者认为马殷铸造钱币的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公元894年到925年。有史可查的只有公元911年铸造了数量极少的纪念性质的天策府宝铜质大钱,而对于铸造其他钱币的情况却很少有资料提到。那么911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楚马殷用的是什么货币呢?政权在立足未稳的时候继承和掠夺是最好的办法,也就是沿用和掠夺前朝的旧钱。笔者认为,这个时期马殷已经开始试图铸造货币,即仿照前朝铸造铅钱。在长沙马殷遗址就曾出土与唐代风格基本一致的铅质小平开元通宝钱和铅元重宝钱。这些钱是直接用前朝钱币做范,特别是会昌范的风格继承较多。但是字体表现比较拘谨,缺乏早期开元乾元的规整和洒脱,且钱开始变小。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背潭者,此类背潭铅钱约占到铅质小平钱总量的6成以上。钱币重量从2.6克到6克,多数为4克左右。
唐代,潭州(长沙)一直在铸造开元小平铜钱,会昌开元里背潭的小平铜钱在长沙以外比较容易找到,但在长沙出土的唐代开元钱中,背谭并不多见。而在出土的铅质小平钱中却有大量的背“谭”开元通宝钱出现,这也许是当时被官方以铅铁钱收缴兑换的结果。《宋史》食货志记载:“盖五代以来,相录用唐旧钱。”由此可知,在铸造铅质小平钱的同时,五代十国时期多沿用唐代旧钱,即使自己有铸造钱币,也会沿用旧钱的钱文。故笔者推测马殷在894年到911年之间沿用唐代旧钱,同时也铸造了钱文相同的铅质劣钱。不过这段铸钱的历史在史书上记载寥寥,有可能就是在回避楚国当时战乱中残酷的掠夺事实。
第二个阶段是公元925年到951年。公元925年以后,马殷配合铁钱使用的铅钱风格为之一变,文字漫晦、铸工粗率、钱体轻薄,且文字时常变化多端。似乎有意在和唐代钱文以示区别,如开元通宝、五五、五朱、开元五五等等,变化大概有几十种,直径一般在2厘米至2.7厘米之间,重量一般在0.9克至3.1克之间。背文有一、二、三、四。此外,还有金、南、兴以及金南兴配一、二、三、四,长沙泉友还藏有背桂的铅质小平钱,更是非常少见。第二个阶段小平钱铸造的数量不多,最多也就是前期铸造的四分之一。此类钱在十国时期墓里常有发现,因此也有人认为此类钱币可能是当时的冥币。但笔者认为应该是行用钱,从近几年出土情况看,此类铅质小平钱常伴随着铁钱乾封泉宝钱一同出土,可以推测应该是参与流通的。
那么在后期小平钱背文为什么只出现了一、二、三、四或者金南兴呢?为什么背桂钱存世较少呢?笔者推测,金南兴可能就是三处钱监或是钱炉所在之处,而一二三四可能就是纪年。也就是说这些钱币只铸造了四年时间,分别在三个地方铸造,这可能也是铸造数量不多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从时间角度来看前后期铸造时间大致差不多的情况下,后期的钱币出土量又要小于前期呢?前后期铸造量的差异也有一种可能,劣币由于只在特定区域流通,势必会造成前期铸造量的积累,使其流通开始显得缓慢,前期货币要比后期货币耐用和结实得多,老百姓的接受程度要高很多。而且这也是经济本身所显露出来的衰败所形成的,楚国后期“五马争槽”造成了严重的内乱和经济衰退。在和铅质小平钱同时铸造的乾封泉宝铁钱上也反映出类似的问题。一些铁钱铸造精美,字体规整,八分书体明显;而一些铁钱的重量和大小不足同时代的一半,文字变化跳跃性大,字体变形,铸造粗糙,钱体上漏铸现象严重,反差之大让人匪夷所思。而在铅质小平钱中背“桂”更少见的原因也可能是桂阳处于和敌国交战的前沿,在一段时间内,桂阳还被敌国占领,铸造量会更少。
一点思考
有些泉友认为此类钱币为南汉时期所铸,笔者认为不妥。笔者对比《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卷三》等书籍中关于此类钱的资料记载,可知乾亨通宝铅质小平钱为南汉钱无疑,且此类钱多数为素背或是背邑。一般乾亨重宝钱直径会大于同时代的马殷钱币,钱文风格也存在着差异,四个字的变化不大,相对比较稳定。乾亨重宝钱文也没有出现过多的跳跃,其字体狂放,字体略粗,规范程度要高于马殷钱币,同时也比马殷钱币厚重。而将五五、五朱、乾元等的钱币和乾亨通宝放在一起来比较也会有很大差异,五五等钱币背字都存在金南兴以及一二三四。而南汉钱币出土量最大的乾亨通宝背字只出现了邑字,马殷钱币后期字体虽似幼书,实则遒劲。
五代十国时,南汉和楚国有多次交锋,互为敌对国,而南汉灭亡在楚国之后(917年至971年)。南汉的势力范围曾包括了广西、广东、海南、越南的大部分,928年封州之战南汉就曾打败楚国。桂州就在广西境内,钱监就在那里,当然是必争之地。楚国951年被南唐所亡,南唐似乎没有使用铅钱的记录,只有铜铁钱。大量铅钱的出路就在南汉,而当时离楚国最近的就是南汉了。从近些年来的出土情况看,长沙的出土量要大于广西。在长沙同时还出土了背潭、背桂铅质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钱,笔者收藏的金南兴宝也出土于长沙。因为在同一个时代,战乱始终贯穿其间,争夺货币就是争夺生存的命脉。而广西出土此类钱币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就是在占领期间自行铸造,并且可能就是拿来主义,连钱的样式都不用动的,因为做好的铅钱也只在南汉境内使用。951年后到971年间的20年桂阳就在南汉的掌握中,而当时的楚国被南唐所灭。第二类就是掠夺楚国铅质小平钱,在南唐不能用的铅质小平钱在南汉是可以用的。
在南汉的势力范围内为什么广东没有开元背金南兴、五五、五朱等背金南兴钱币的大量出土?为什么没见到背桂的开元乾元在广西、广东等地大量出土呢?这些出土量最大的地方还是在长沙,而在今天的广西境内也能找到背潭的开元通宝铅质小平钱,这些现象说明继承和掠夺以及拿来主义是当时十国生存的不二法门。
近些年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楚国铅质小平钱也随着不断出土,但是由于气候地理和钱币质地原因,出土的多数钱币碎裂或者粘接在一起,完整者甚少。再者,因为楚国铅质小平钱的文字大多散漫,一般不被泉家所重视,因此近些年介绍此类钱币资料的文献较少,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出土的很多铅质小平钱中文字怪异,多不能破解,真是待字深闺人未识啊!笔者抛砖引玉,相信通过此类钱币的不断出土和大家的不断关注,一定会有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出现,让我们了解楚国铅质小平钱背后更多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