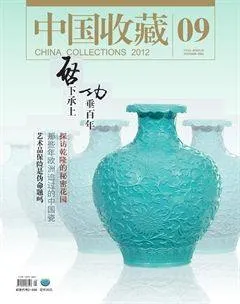三尺讲台 一身布衣
【赵仁】
那时,启先生的“坚净居”很小,只有十几平米,但先生家总是高朋满座。可是如果他跟学生约好了回答问题,当天要是再有别的客人,哪怕客人地位再高,他都会拒绝,告诉人家“我跟学生约好了,必须接待学生。”
我平素喜欢写诗,常把自己的诗作拿给老师点评。启先生批改诗文,看出什么问题,都会拿铅笔稍微划一下;有时候也会改动一两个字,但都说是“宜作”什么什么,表示再和学生探讨。启先生对学生从来没有过严词批评,顶多微微皱眉,伸出食指隔空点一下,说句半截话“你看你又⋯⋯”做个提示,点到为止,剩下的让学生自己去领悟。他生怕伤害到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上世纪80年代,先生除了系里安排的课,还每周额外给我们开版本目录学的课,并且专门跑到学生宿舍给我们上课。只要启先生来上课,我们狭小的宿舍里就会挤进来十几个人,站的站,坐的坐,还有趴在上铺床上听课的。师生完全打成一片。讲累了他就跟我们聊会儿天。兴之所至,也会提笔写几幅字。今天送你,明天送我,并且作品上总是非常客气的写上称谓,如“某某老兄”,实在是让人感动。此外,除了正儿八经地上课,私下和先生闲聊,也是一种愉快的学习过程。先生将它当成启发式教育,同样非常重视,并冠名这种教学方法为“熏”。
先生的心里任何时候都惦记着学生。一位同学做论文,需要参考的一个版本在国内没有,只在日本有,启先生便直接写信到日本,让日本朋友帮忙提供。又一次,先生受邀到上海博物馆看展览,尽管行程紧张,却执意抽出半天时间,特意跑到博物馆库房,在浩如烟海的藏品里,一卷一卷地翻看,为学生寻找资料。
【吴龙辉】
我参加完博士生考试不久,就接到硕士生导师聂石樵先生交给的一个任务,为启功先生搬家。原来,为了逃避访客安静著述,启先生曾在留学生公寓躲了一段时间,这时准备搬回去。我去的那天正好下雨。先生便不让我收拾东西,而是坐下来聊天。刚寒暄两句,两年没见面的启功已认出了我,说:“中文系有一个会写旧体诗的研究生⋯⋯”我赶忙回答:“是的,是我。”启功高兴起来,说:“哈,我说这么眼熟呢。”对此,我很是感慨。年近八旬的老人,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访,不知道要会见多少人,居然还记得我和我向他学诗的事。
没有客人来访,外面又下着雨,这样的环境很适合交谈。我们谈了好久,后来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对我说:“走,谋食去。”那时北师大的东门外有一家名叫燕鲁烤鸭店的小饭馆。先生显然对这个它很熟悉。落座后,他没有询问我要吃什么,直接叫过服务员来点了一份烤鸭和几个小菜,又要了瓶啤酒。然后我们大吃起来。先生的食欲很不错,但我吃得更猛,转眼吃个精光。后来几次,先生都带我到这个小馆子吃饭,烤鸭、小葱豆腐和啤酒,一样也不能少。吃完都是先生去结账。我想,先生这是在借机给我改普伙食。
【首生】
启先生讲课,深入浅出,课堂氛围极好。一次他给我们上语言课,讲文字时说:同学们注意了,“茜”对“晒”说,出太阳了。你咋不戴草帽?“旦”对“但”说,胆小鬼,还请什么保姆?“兵”对“丘”说,你几时截得肢?幽默,诙谐,同学们可乐坏了。我还记得,1959年暑假,先生带我们去郊区顺义参观古寺,有学生问先生四大金刚手里拿的是什么?先生说是“风调雨顺”,并加以详细解释,学生们一个个恍然大悟。
【熊国祯】
我爱人毕素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后,有点半改行性质。她参加山西应县木塔辽代文物的整理研究,乍一接触文物研究,有些底气不足。我建议她去找启功先生做辅导。当她自报家门,说到自己姓毕,父亲是满族人时,启功先生马上说“毕努氏,汉姓为毕;瓜尔佳氏,汉姓为关”,并从此戏谑地把素娟称作“我的半个同胞”。在启功先生的细致指导下,她的论文进展很快。一天早晨,在小乘巷先生家中,看完稿子后,先生觉得内容比较充实,就说:“可以了,干货不少了,一个大中错。(“错”是方言量词,截、段、斡。“中错”就是鱼身子)你再把文章的开头、结尾好好织一下,把段落之间的衔接理一理,润色润色,这就成了。一篇论文,好比烧鱼,主体部分是中错,要结实丰满,味道好,有吃头 。但是也要有鱼头、鱼尾、鱼腮、鱼鳍,把这些个零件和中错搭配在一起,才是一条启功赠熊国祯、毕素娟夫妇一条整鱼。写文章哪能全是干货!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作用组织得当,各尽其职,就是好文章。”接着先生又亲自给《文物》杂志写信推荐 。
素娟在改正誊清稿上曾把启功先生的名字写在前头,自己的名字写在后头。先生拿起笔就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说:“你自己写的文章,干吗要写我的名字?划掉,划掉!”一点商量余地也没有。素娟只得在文末“附记”中郑重申明:“本文撰写过程中,承启功先生热情关心,多次给予指导,谨此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