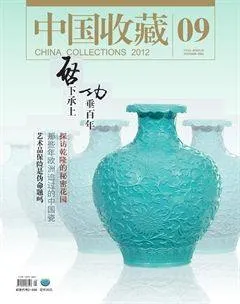鉴定:还需知其所以然
收藏也好,鉴定也好,不是单纯的鉴定真伪,这里面的内容非常广泛,只要稍稍地考证一下,就会牵扯出多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启功先生不是简单的鉴定家,而是一位大学问家,是国学大家。我和先生相处40年来,我觉得先生不敢说通百家,也绝对通几十家。先生所涉及的领域之广、学问之深都是旁人不及的。先生从小立志要当一位画家,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先生就画的少了,但不管书画哪一方面,他都是从临摹古人入手的。先生遍临大家的名迹,转益多师,把古代的书画传统完整而又有自我取舍地继承下来,把它们融汇在自己艺术审美取向里边,这一点我们从他的画和他的学问就能看得出来。
我曾把自己收藏的清初刻本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请先生过目。先生看后说书的版本、年代、字体都好。“但其中有‘南北宗论’,我是不赞成的。”可见先生并不随波逐流,而是能坚持己见,而且在实践中来践行。他的书画有一种雅韵,非常人所能,这跟先生的学问有莫大的关系。先生主张“透过刀锋看笔锋”,从字里行间和笔画之间去体味古人笔下的意趣。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他终成一代书画大家,而这给他的书画鉴定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条件。正如先生所说的,如果你学鉴定而不去学书画,那你就是瘸腿!因为你并不理解古人字画之间的笔墨关系是怎么回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向先生学习的。
先生是大学问家,不管是碑还是帖,不管是对文字内容的考证还是字体的考证,先生能够指出来什么是真本,什么是摹本,什么是翻刻本。有一次我得到一本王羲之的圣教序,自己觉得还不错,但启先生拿来一看就说,你这是最好的翻刻本。那为什么是翻刻本,先生给我举出一堆例子,这个字怎样,那个字又怎样,讲得头头是道。
又有一次,有人拿收藏的明代吴历画册给先生看。册页画得很精细,后面的题跋也都是明清人的书法,一般来说这样的东西大家都会认为它是真的,但先生一眼看就是假的。原因何在?先生说吴历的笔墨不是这样,他的笔法不是这样,他的渲染也不是这样。接着先生又说,吴历的书法是学的苏体,学苏的书法一般会发肥、发扁,所以这个字也不是吴历所写。先生又翻到后面的题跋说,这个是抄录谁的哪一段,哪个是抄录谁的哪一段,他连抄录之处都能给你讲清楚,因此他最后断定是假,那别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所以,我们对于先生书画鉴定上的学问不能只看表面,更是要看其实质。这种实质就是先生所说的:要多方面去看。画、笔墨、整体格局、时代气息等等方面,从外表到实质,都看穿了,这种看穿,没学问不行,不了解广泛的知识不行。
有一次我去先生家,先生拿一个文征明的册页打开让我看,其中有部分是收藏者的题跋图章,他就提出,这两个图章是一个图章,它们一模一样,但它们盖在这里的时间差了20年,时间相差如此之长为什么印章还会一样呢?对于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但紧接着先生就说,这个图章是没问题的,我看它是象牙制的印章。因为象牙质的印章不容易变化,打印沾的印泥少,跟石头印章盖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些细微之处的差异,先生都注意到了,对书画的鉴定能不准确吗?
先生的记忆力极强,他的分析能力也极强,所以在他判断东西的时候是不会犹豫的。这种不犹豫是一种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品格,即“负责”的表现。既是对国家的负责,也是对我们传承的文物的负责。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老先生在这方面从来都是直抒胸臆,没有什么可保留的。比如一次,先生对一幅国家的博物馆想要出钱购买的画作,明显地提出了异议。先生说:如果这幅画是某个有钱的主出于个人喜欢要买,那咱们自不必多说,但是如果非要国家的博物馆去买这件东西,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那我理解这个“说道说道”绝非一般的表态,而是必得分出个是非曲直,因为先生认为糊弄国家那绝不行。这是先生负责的精神的最好表现,也是先生给我们所有鉴定人的一个表率。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是结合目前的形势来看,尤其值得一说。
先生在鉴定上能如此的有成就,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先生对于传统文化、对于古书画的发自内心的喜好。这种喜好是要学进去,要领悟,要和古人对话的。如今先生走了,去和古人对话了,那么我怎么办?以后有了问题我去请教谁?谁能回答我?所以我觉得这又是先生在冥冥中激励我继续努力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没有可停止的地方,先生一生就是这样。
(金煜先生系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