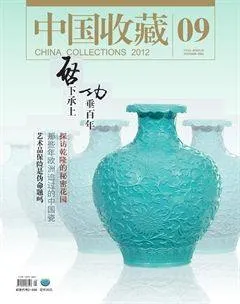开朗与平和是一种风格




8月初的几场雨,让北京的空气清新了许多。暑期的北师大校园显得颇为安静,启功先生生前居住的红六楼宿舍藏身于北师大一个僻静的角落,旁边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几位老人正在晨练,呼吸着北京难得的清新。在这个盛夏的清晨,记者带着对启功的景仰以及对先生为人处世的一些好奇,走访了《启功全集》编撰者侯刚先生和启功内侄章景怀先生。
“人家喜欢是看得起我”
《启功全集》编辑部与红六楼仅隔着一条小道,当记者走进编辑部时,启先生生前的助理侯刚正在埋首整理着手边的文稿,记者的到访使得这个陪伴了启先生20余年的老人再次追忆起启先生的才情和德行。
“我是1979年与启先生相识的,那时我在北师大校长办公室工作,经常到先生家通知事情。当时,启先生在北师大不但给本科生上课,还主动承担了夜大的课,教授古典文学,课程繁重,”说起启先生,侯刚颇为动情,“启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上世纪80年代初,启先生在社会上已经颇有声望,事务也越来越多,为此,学校打算给先生配助手,但先生却婉拒了,他说:‘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耽误年轻人的前程。’后来,当时的北师大校长王梓坤就让校长办公室帮忙处理启先生的一些日常事务,我也因此与先生结缘。”
1988年帮启功先生筹备书画义卖一事让侯刚至今也感慨颇多。“当时,北京女孩择偶有一句俗语——‘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就是说那会儿师大的学生生活困难的比较多,启先生有感于此,向学校提出了义卖他的书法绘画筹集奖学金的想法。”
从1988年到1990年,三年的时间里,启先生创作了10幅画,选出了100幅字。其实,侯刚透露,在三年的时间里,启先生创作了不下500幅书法作品,但最终仅留下了100余幅,这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缘由。“有客人来了,正好赶上启先生在写字,于是就问他‘您这是给我写的吧?’启先生就随口回答,‘你想要那就拿走吧’。”无奈之下,北师大校办就在留学生公寓给启先生找了一个房间让他安心写字,要不然连这100幅都很难凑齐。“张中行先生就曾问过他,怎么对自己的作品这么不在意呀?启先生回答说‘人家喜欢是看得起我’。”最终,启先生创作的这10幅书画和100件书法在香港拍得160余万元,并全部捐赠给北师大,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以“励耘”命名是为了纪念启功的恩师、北师大的老校长陈垣先生。
对启先生的随和与平易近人,侯刚颇为钦佩,“我们北师大的司机、食堂的大师傅、修电话的工人手里都有启先生的书法作品,有的还不止一幅。”说到这里,侯刚想起了一件趣事,有一次,一场暴风雨使得红六楼的电话线出了故障,启先生着急地找到侯刚,侯刚立刻带着电话工小杨去修理。修好了后,启先生十分高兴,主动提出要送一幅字给小杨。启先生一边写一边询问小杨是否有对象,并向小杨许诺,等他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再送他一幅字。第二年小杨结婚后果真上门去拜访启先生,启先生二话没说,立刻写了一幅字送给小杨,贺他新婚之喜。“启先生就是这么随和的一个人。”侯刚说。
北师大的“礼品制造公司”
在北师大,师生们都习惯把启先生等几位老教授居住的宿舍称为“小红楼”,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5年先生去世,启先生在“小红楼”里居住了20余年。虽然启先生仙逝已经7年,但红六楼启先生的宿舍还保留着他去世前的原貌。
十多平米的书房,除了书桌和三套沙发外,都被书籍塞满了。“这张书桌是九三学社的人送给先生的,他用了20多年,许多作品都是在这张小书桌上诞生的。”章景怀告诉记者。从1983年开始,启先生的内侄章景怀就一直在先生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在启先生生前,这间十多平米的书房常常高朋满座,“经常是这拨刚谈完,那拨就马上进来了,他人缘儿特别好,”章景怀介绍,常来常往的除了张中行、冯其庸、徐邦达这些大学者外,“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能跟人攀上话,他知识面很宽。有一次,一个制作笔的小伙子来拜访他,他兴致颇高地跟人谈起了怎么做笔制笔,小伙子颇受启发,回去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写成了一本关于制笔的工具书,还来找启先生写序,据说,制笔界正好就缺这么一本工具书。”
和启先生共同生活了20多年,在章景怀眼里,启功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一个整天都乐呵呵的老头儿。常有人问章景怀启先生高寿的秘诀,他每次都回答说,启先生是个佛面佛心的人,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宠辱不惊。
侯刚也认为,启先生之所以能高寿,缘于他良好的心态。“虽然他一生这么坎坷,但他从不温习烦恼,他曾对我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很短暂,但将来还很长远。”
启先生的幽默可谓人尽皆知,在侯刚看来,幽默也是启先生高寿的秘诀。“有一次,我们学校一个修管道的小青年在路上遇见了启先生,启先生要跟他握手,小伙子一边在衣服上擦手,一边说‘我手脏’,启先生笑言,‘手脏没关系,只要不是黑手就行’。”侯刚还回忆说,当时,北师大的领导出差或访问都要带些礼品,而启先生的书法自然是首选。此外,启先生还给北师大加油站写了不下20幅书法作品,每次加油站需要进油了,就送一幅启先生的书法给油田,所以北师大加油站的汽油总能源源不断。为此,启先生戏谑地称自己是北师大的“礼品制造公司”。
“启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大家都知道他随和,其实他也有不随和的时候。”侯刚告诉记者,曾有一位空军军官来向启先生求字,一进门就把自己的名片亮出来,说自己是什么军衔、什么来头,启先生对这套有些反感,就让他把名片留下,改天再给他写。可这位空军军官非得当天就要,启先生急了说:“你今天不派飞机来轰炸我就写不了。”章景怀也讲述了类似的一件事。有一次,一位高官派秘书来向启先生索字,启先生一反往常的随和,对来人说:“我要是不写,你们首长不会停发我工资吧?”
“做人诚平恒”
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启功是因书法家的身份而闻名的。“行文简浅里,做人诚平恒”——这是挂在红六楼启功书房里的一幅书法作品,“这个字他写了好几遍,最终选了这一幅,他这一生也是这么做人做文的。”章景怀告诉记者,启先生每天都要写字画画,对于他来讲,写字、画画就是一种娱乐,“他癖嗜碑帖,临摹了大量的碑帖,光唐人写经他就临了无数遍,大家都说启先生字写得好,殊不知他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
跟随在启功身边多年,耳濡目染,章景怀对书法也颇有些见地。“启先生有时也会跟我谈谈对书法的一些看法,他说,写草书就如同公共汽车中的大站快车,到小站的时候可以不停但必须遵循一定的路线。他的草书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他真正懂草书。”不过,启先生对自己的书法作品却颇为随意,他从不认为这些书法值钱,“他有一方印章,可以说是他心态的写照,叫‘令纸黑耳’。”启先生还有一方闲章叫“功在禹下”,因为大禹的儿子是夏启,所以“禹下”就指“启”。此方“调皮”的印章的用意也在强调他的姓。
除了书法家,启功还是一位大学者、诗人,而许多人都挺困惑,启先生每天既要教书,又要练字,还有那么多应酬,他哪来的那么多时间看书呢?“启先生起居十分随性,困了就睡,但他时常睡不着觉,或者很早就醒了,因此他的床边总放着书,睡不着的时候就看几页书。除了书外,他的枕边还经常放着些小铅笔头,有时灵感来了,就写上几句,他的很多诗都是这样做出来的。”作为启功身边最亲近的人,章景怀对启功的“学问”是从何处而来的最为清楚。
在北师大从教70余年,启功专攻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对史学、鉴定学、宗教学很擅长,甚至对敦煌变文也有研究。侯刚说:“启先生传统文化的底蕴十分深厚,他除了写字画画外,有时候还会唱诗,按照古代的唱法来吟古诗,他十分在行。”
说到做人的“诚”,章景怀和侯刚都不约而同地说起了两件事,“启先生跟人照相必定要平起平坐,要坐着大家都坐着,要站着大家都站着,绝不会别人站着,他坐着。”章景怀说,启先生还有一个习惯,每次家里来了客人他都会把人送出门,然后再自己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以免影响邻居。“他对钱财也没有什么概念,同事、学生有困难,他都会热心帮忙。他的大部分钱都捐给了北师大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侯刚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