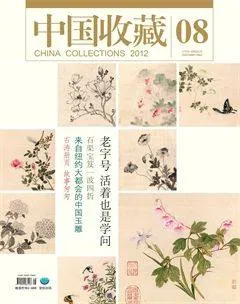转身是一道风景


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
每座城市都会有个市中心,即使在百年前也不例外。在这样的繁华地段中,旺铺、字号林林总总,各有特色。这种茂盛的生机似乎具有某种魔力,牵引着人们的脚步难以停歇。如此热闹的生活气息,不仅成为老百姓们纷纷来此购得生活所需的场所,也令不少或是具有商业眼光、或者原本就是为了糊口的人争相希望能在此地掘得一桶金,就连平时难以跟市井打交道的达官贵人们,有的隔三岔五地也要来逛一逛。今天我们来品味老字号,实际上就是品味一种生活气氛、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历史和一种文化。
是道风景
提到百年前商业街与老字号的繁华,首先让人容易想到的便是京、沪、广这三大城市。
当年上海哪条街的老字号最诱人,非南京路莫属。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迫辟为通商口岸。1842年中英签定的《南京条约》打开了上海的大门。当时的上海县城在今天的城隍庙一带,英国人在这个椭圆形县城的北面至外滩开辟租界。
南京路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确立了它在上海近代商业发祥地的地位。它先是英租界,后成为公共租界。当时外国金融集团先在外滩建立起金融集中区,后沿着当时被称为“花园弄”的一条东西向“大马路”发展商业。随着“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和“中国国货”等五大著名环球公司的崛起,南京路便成为上海最热闹,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一般指的正是南京路步行街这一带,马路最宽,商店最大,东西最洋派。
南京路的形成与租界和跑马场是分不开的,“先路后店,街随店延”是它发展变迁的主要模式。
如今,沿着南京路一路数下来,店门挂“中华老字号”标牌的仅几家:邵万生、上海张小泉、沈大成、三阳南货⋯⋯
其中的“邵万生”,从始创的咸丰二年算起,迄今百余年。其名声大噪,是在创始人邵万兴1870年将店开到南京路并更名“邵万生”之后,意为“生生不息,向前发展”。当年每逢蟹肥,邵万兴总让店员在门口,将阳澄湖运来的大闸蟹一只只当众过秤,只只足秤三两多,还必是雌蟹。这样的精挑细选,难怪后来造船大王包玉刚也年年来此购醉蟹。
而在另一端的中国南部的广州,现存的老字号企业中,历史最短的也有七八十年,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企业陈李济,已有着四百多年的历史。
广州的老字号大多有着鲜明的岭南风格,岭南文化内涵丰富。如广州酒家、陶陶居、北园酒家、泮溪酒家,将岭南的饮食文化、园林文化、建筑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岭南餐饮业的奇葩。陈李济、潘高寿、敬修堂等老字号企业生产的药品,其产品类型和主治功能等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岭南特色,如王老吉凉茶、保济丸、夏桑菊等等,产品在岭南区域和东南亚地区,乃至国外的华人社会都很有市场。
老字号是广州古老文化的标志之一,例如早在1600年创建的陈李济药厂,被国家命名为“中华老字号”,成为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最古老的中成药制药企业,有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陈李济比著名的北京同仁堂还年长69岁,所以陈李济的各类药丸亦成为“广药”的代名词,形成广州陈李济、北京同仁堂和杭州胡庆余堂三足鼎立的局面。
是种融合
首都北京早在清代早期就已经形成了四大商业街区。这其中又以前门商业街为胜,不仅商业味浓,而且人气足、财气旺。
《日下旧闻考》中说:“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据悉这里的商铺在4000家以上。而在众多商家的激烈竞争中,出现了一批原料好、做工精、服务周到的商号,比如马聚源帽店、天成斋鞋店、长春堂药店、长盛魁干果店、天蕙斋鼻烟铺等等。
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外,当年前门商业街上吃的、玩的好去处也不在少数。因为地处皇宫的正前方,这里云集了众多会馆;饭馆、钱庄、戏院一众排开,里面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手师傅,并且从中培养出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
在老字号发展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种融合、变通与交流。
这一点,北京地区的老字号表现最为明显。由于特殊的行政功能,就像今天我们常说的“京漂”一样,当年的京商也是来自全国。他们以各自的经营传统根植于北京市场的沃土上,掌控了北京城不同的商业行业,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精华。
大致上,明清以来,北京的餐饮业多为山东商人,主要是登、莱州人氏,以东兴楼、天福号等为代表;药材和银号业多来自浙东商人,宁波人是其中的代表,同仁堂、鹤年堂、永安堂都在此范围;而我们所熟悉的晋商经营的行业较广,纸张、印染、银号、酱园等等皆有所涉及,并且占了很大份额和很强势的地位,比如六必居;以商业头脑发达著称的徽商则主要从事茶叶、布匹等行当,例子为张一元、森泰、吴裕泰等。
外地商业渗透北京老字号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地商人来北京开店起家;还有一种则是原本发家于外地,后将分号开至北京。比如著名的盛锡福,从当年的外壳包装上我们能看到,其总号在天津法租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在此不多赘述。
是种文化
今天我们通过老字号的历史来探究其文化,暂且抛弃管理这些深层次的学问不谈,单从牌匾——这个人们最直观的感受上,就能看出个端倪。
开店铺的人们都希望将来名号能叫得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取个好名字,是商人们非常重视的事情。这个名字既要朗朗上口,容易被人记住,又要具有美好的寓意。往往在买卖正式开张之前,便开始琢磨起什么字号。不过,早年间许多做买卖的人其实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化底子,但是没关系,因为那时的文人墨客跟一些买卖家保持着密切关系,自己不行,可以向文人墨客去求个字号。比如内联升。据说,创办人赵廷肚里没多少墨水。鞋店开张前,为了起个好字号,他不惜重金,四处求人,最后选定了内联升。这三个字有讲究:内指大内,也就是朝廷;联,与连谐音,体现这个字号与大内有关系;升,有步步高升、连升三级之意。
仍以老北京的字号为例,其来源不一,有直接以人的姓名为名,如“王致和”、“王麻子”、“馄饨侯”、“烤肉宛”等;还有以地名和名胜古迹做字号的,如“丰泽园”、“柳泉居”等。另外,也有顾客叫出来的字号,如“砂锅居”最早的字号叫“和顺居”,取和和顺顺之意,因为它用一口明代的大砂锅煮肉,以肉味奇香取胜,招徕食客如云,以致大家几乎都知道他家这口大砂锅,于是习惯性称为“砂锅居”,后来店家索性就用了这个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存的老字号匾额中,由郭沫若题写的很多。郭老为人比较随和,题匾不收“润笔”,有时请他吃顿饭就能讨块“匾”。当然了,郭老不会随便乱题,也不会只看字号的名气大小,需要机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据说有一次,郭老和夫人到“都一处”品尝烧麦,跟经理栾寿山和几位职工聊起乾隆写的虎头匾的故事。栾寿山灵机一动,说“虎头匾只能挂在店里,我们店门口还缺块匾。”说到这里,他有意卡了壳。郭老看穿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说:“我给你们写吧,不过,我可没皇上写得好。”没过几天,郭老果然给栾寿山打电话让他来取字,“都一处”的匾就这么挂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