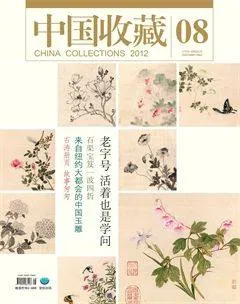藏书未必非旧不可
今年端午节北京雨水多,因此想起藏书的话题。
在酒仙桥Indigo(颐堤港)“百灵鸽”买了牛津版董桥的《绝色》和《故事》,忍不住在雨中的车里就要阅读,因为《绝色》讲的大抵是装帧精美的英文旧书,诱惑力实在难以抵挡。《故事》此前我已经买了“作家”版,灰色纸封面,不亚于手里的布面精装本。于是想到其实藏书无所谓非那种不可。
90后的孩子常说旧书都让你们买光了,我们没什么可藏的了。我自己的经验则是藏书未必非旧不可。文本好、纸墨讲究、装帧精美的书都在可藏之列。这道理就像粗粮和粗布衣服之于人的营养和审美。我买过一套近年“企鹅版”三卷本《天方夜谭》,其用纸和装帧插图跟经典的旧书不分伯仲,其价格也超过了大部分英文旧版《天方夜谭》。
有一次,一位也卖书也藏书的“限量本”发烧友,赏我看了一位时贤的散文集限量布面精装本。版权页定价25元,他说低于600元此书不出手。我于是知道那价钱的书不一定是古董书。如果经济条件达不到如此消费水平的书人,我的建议是另辟门径。藏书领域和学术领域一样,本来是无所谓一定之规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只要是喜欢,任何领域的藏书都能卓然。我敢断言,将来专事搜集盗版书的也能建一道风景,只要他有足够的空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本终究也会成为一种文献,尽管它们不经典不美观。私人藏家不屑并不能否定文本的文献性质。今天热门的“文革”出版物,当年就是人们恨不能立刻烧了的东西。
今天许多没人读的出版物印量很小;一部分极精美的奢侈出版物印量也很小。试想一下,邮票要是一种只印500枚,集邮的人群会怎样顶礼追捧。今天好书只印500本的绝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我主张藏书的人根据兴趣买书,能“藏”之前不要刻意培养偏见。这就像学习的时候不能培养学术偏见一样。喜欢读的喜欢那样子的又不阮囊羞涩的,就买了藏了。假如非要强调人无我有,则选择一个特别喜欢的领域广为罗致。有讲究版本的条件当然好,没有条件的搜罗新本子全乎也行。
这是雨天的端午节买书买出来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