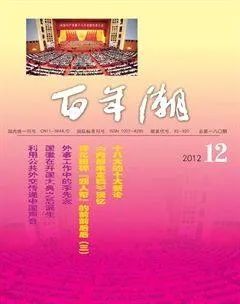胡乔木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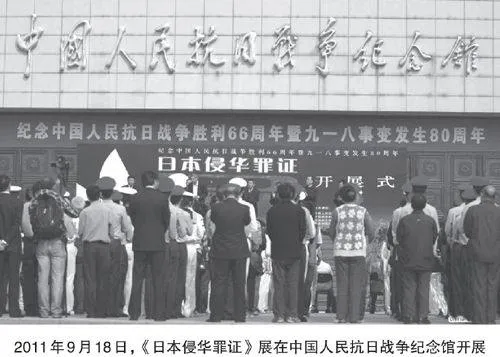
胡乔木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坐落于北京丰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从倡导到筹建,从设计到展览内容,再到健康发展,都倾注了胡乔木的心血。
上下协调,费心筹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始于1983年。筹建之初,在建馆和选址上有不同意见。1984年4月,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报送的建馆请示报告,最初的动议是要筹建一个七七纪念馆。胡乔木曾就筹建七七纪念馆的拨款问题写信给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后经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后,资金得到落实。但在怎样定位纪念馆的问题上仍有分歧,如有的力主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为此,1983年11月24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白介夫请示胡乔木。胡乔木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不搞个抗日战争纪念馆说不过去。”他表示,“要抽时间去宛平城看看”后再定。
为了全面了解纪念馆的情况,1983年12月19日,胡乔木在白介夫的陪同下来到宛平县城,实地考察了抗日史料陈列室,认真听取了关于筹建纪念馆的汇报以及各方意见。之后敲定:在宛平县城搞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不搞七七事变陈列馆。他说:卢沟桥事变实际上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在卢沟桥建纪念馆不能只反映卢沟桥事变,还是应该在宛平县城搞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并提出很有必要在县城内建抗日公园、纪念碑、搞万人坑的模型以及像法国巴黎纪念普法战争的蜡人一样的雕塑。
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敲定之后,纪念馆建在什么地方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利用两个城楼即在旧城楼的城墙上稍加扩充,建立一个初具规模的纪念馆。另一种意见主张在宛平县城内单独选址,建一个庄严朴实、布局紧凑的国家级抗日战争纪念馆。对此,胡乔木颇费思考。他认为,博物馆、纪念馆的建设应尽量利用古旧建筑,如寺庙、古迹等稍加维修就可以对外开放,这样既能保护文物古迹,又能充分利用古旧建筑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为国家节省建设资金。所以,他最初倾向选址就在旧城楼的城墙上稍加扩充,利用两个城楼进行陈列,如果面积不够,还可在城内公园里建房陈列。
1984年5月,国家计委按照胡乔木的上述意见起草了《对北京市建设抗日战争纪念馆问题的意见》,上报国务院。但历史学家刘大年等人提出,应在宛平县城单独选址建馆,并就此分别向白介夫和胡乔木作了反映。1984年6月4日,胡乔木收到白介夫的信。信中希望他就选址问题作出批示。胡乔木对刘大年等人的意见非常重视,一方面建议北京市委对建议认真研究后拿出初步意见;另一方面立即向中央有关领导请示。收到白介夫信的当天,胡乔木批示:“请万里同志批示”。
6月6日,白介夫再次致信胡乔木。信中说,刘大年等人的意见也是很多专家和知名人士一直呼吁的,建议“应该考虑”。胡乔木收到白介夫的信后,经过多次与文化部、有关专家及北京市政府等有关部门协商研究,最终决定把原准备利用改建后的宛平城墙、城楼开辟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计划,改为由国家计委及北京市共同投资,在宛平县城内单独选址,创建一座规模宏丽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由于筹建抗日战争纪念馆意义重大,其陈列内容和资料征集涉及全国各方面,政策性、专业性很强,故白介夫在6月6日的信中还建议,纪念馆的建设“请文化部负责主持,中央和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参加,组成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建领导小组。建馆的经费、开办费及经常费,都要在文化部主持下,组织起专门班子……有了牵头单位即可抓紧工作。争取在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建成”。
胡乔木认为,白介夫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像这样重大的事情,由北京市牵头会遇到许多不便,还是应该由中央部门即由文化部牵头筹建,北京市负责承建为好。于是,他与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朱穆之紧急磋商并征得他的同意,又与总政治部等有关部门协商并取得他们的大力支持,之后就此问题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称:“以上意见是否可行,盼予批示,以便文化部邀集有关各方,提出具体修建方案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北京市则可据以进行施工。” 6月8日,万里批示:“同意,请纪云同志酌处。”6月11日,田纪云致答白介夫:“关于请文化部牵头问题,乔木同志已与朱穆之商定,请遵乔木同志指示办理。”
随后不久,由朱穆之为主任、白介夫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汉为副主任的15人组成的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北京市政府还专门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基建指挥部,具体负责馆舍建设。同时由北京市、文化部及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部门组成“抗战馆陈列办公室”,负责展厅陈列任务。
以史为鉴,指导布展
在纪念馆筹建过程中,胡乔木经常听取有关纪念馆的工作汇报,批示有关部门呈报上来的请示,帮助解决建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在建筑艺术、建筑布局特别是布展总的指导思想、布展形式和内容等方面,提出过非常具体的指导意见。
时任纪念馆基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后任纪念馆副馆长的刘建业回忆说:
抗战馆筹建过程中,头绪非常多。乔木同志始终提醒我们,“不管工程头绪怎样杂乱,你们要紧紧抓住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建筑和陈列的统一。建筑要为陈列创造条件,陈列要及时对建筑提出具体要求,使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千万不能各干各的”。当时由于建筑工程时间非常紧迫,建筑设计完成后,陈列方案尚未出来,如果完全按照建筑设计图纸施工,将来陈列形式就会被建筑所限制,而等待陈列方案,又会拖延工期,不能在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之际竣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乔木同志经常召集建筑、陈列两方面的人员在一起协商。
胡乔木有时还把一些同志请到家里,研究解决有关难题。对陈列内容,胡乔木非常重视,他提出,布展总的指导思想是要以史为鉴,一方面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一方面要反映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具体而言,他认为,整个陈列要按抗日战争的发展分四个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为第一阶段。这段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九一八事变、抗日联军、党领导的北平学生运动、万里长征、西安事变等都可以表现。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以党的统一战线为主线,中共中央发表红军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开到华北抗日前线。平型关战役也要表现,不管林彪这个人后来如何,这个战役在全国影响非常大。王明路线可以提一下,不要放在重要地位。华北的抗战、台儿庄战役等都要表现。1939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第三段。这段时间日本搞“三光”政策,穷凶极恶,中国人民这时非常困难,但仍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对美国介入中国抗战,包括通过缅甸修一条公路以及苏联在初期支援抗战,末期出兵东北都要表现。他说,对日本的侵华暴行要有足够的揭露,对于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作用应有充分的评价,对于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也要让人民知道。然后是尾声。他说,尾声可以拉长一点。时间从1945年8月到1946年7月。一方面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一方面要反映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例如聂荣臻抚养日本女孩等反映出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谊是在不同形势下继续着的。“中日不再战”是日本提出的口号,但不能搞成中日友好馆,那样气氛不协调。对国民党要实事求是,既不要把好的说成坏的,也不要把坏的说成好的。关于历史资料,可以找一些研究近代史的同志咨询。
胡乔木的意见,为纪念馆的陈列勾画出清晰轮廓。在胡乔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终于在1987年七七事变50周年时建成。
高瞻远瞩,确定三大任务
1987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揭幕仪式,杨尚昆、万里、王震、胡乔木等出席开幕式。此时的胡乔木,对纪念馆的关注并没有结束,他又在谋划纪念馆的发展。经过慎重思考,他提出纪念馆应该肩负三大任务:
一是抗日战争纪念馆应当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心。他说,要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格局中去考察研究。在这个前提下,开展多方面的、深入的抗战史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工作。要团结全国的专家学者,特别是要与国际上的学术团体、专家学者建立广泛的联系,把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产生一系列跟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相称的,在学术上、政治上、文献资料上有足够分量的学术著作。他强调,要深入总结抗日战争历史教训,澄清历史事实,明辨历史是非,把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搞深搞透,对于否定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作用的观点,要用大量翔实的有说服力的资料去驳斥。对于否定侵略性质,为军国主义者招魂的逆流,要以事实去批判,要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还要特别注重历史资料的采集、整理,要抢救一批濒临灭绝的“活资料”、“活证据”。在他的倡导和指导下,1988年7月5日,纪念馆举办了首次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胡乔木出席会议并作讲话。1989年4月,胡乔木带病再次来到纪念馆视察,他除了再次强调纪念馆要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心这项重要任务外,又提出“抗日战争纪念馆应当成为对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应当利用抗战史这部活教材,充分地宣传中华民族的崇高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为了国家与民族利益摒弃一切私利的奉献精神,要使全国人民从抗日战争的伟大历程中撷取精神力量,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团结”。三是抗日战争纪念馆还应当成为一座联系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桥梁,成为加强与台湾、香港、澳门爱国人士团结的纽带。
20世纪90年代,胡乔木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关心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发展和建设的热情丝毫未减。在他的大力推动下,1991年1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纪念馆牵头,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抗日战争史学会,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专家学者欢聚首都,商讨全面组织撰著抗战学术著作。病魔缠身的胡乔木未能亲临会场,就在病床上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高度评价中国人民抗战的深远历史意义,希望抗战史学会今后多发挥组织促进作用,将处在分散状况下的研究组织起来,推动我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在他的关怀下,中国第一本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专刊《抗日战争研究》,于1991年9月正式出版,在海内外公开发行。其后又有多部研究抗日战争的专著相继问世。
胡乔木晚年对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企图把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关系拉向后退给予高度关注。1982年,他组织批判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之后又组织对《“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的批判。他要求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专著来揭露日军在我国制造的许多惨案,如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和细菌战、重庆大轰炸、平顶山事件等等,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少年。他提出要特别关注保护日军侵华暴行遗址。当他在阅报中看到日本731部队细菌战试验场地遗址均已盖了工厂、仅存地下试验室遗址的报道后,心急如焚,立即给有关领导和部门写信,“望文化部告文物局,通令全国查明,定出保护措施和进行宣传教育的办法”。当白介夫和刘大年提出要成立日军暴行调查组开展调查时,胡乔木大力支持,从调查计划到资金的投入,再到基金会秘书长人选,都一一帮助落实。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