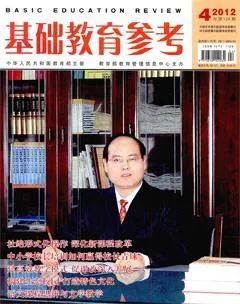语文课程思辨与文学教学
2000年秋季起使用的高中语文新大纲明确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既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也明确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
一、充分认识语文学科
究竟什么是语文,虽然众说纷纭,但都定位于一个两分的概念,因此造成了种种分歧。比如,梳理语文科的来历,我们不难看出,它是“国文”和“国语”的合并,也就是“词章”和“语言”的合并。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国文”科是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中国文学”科来的;而“中国文学”则是从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的“词章”科来的。循着“词章”一“中国文学”一“国文”的路径,大致可以肯定,所谓的“国文”,应该是类似孔门四科中的“文学”,而非现代意义上所说的文学(literature)。从这个角度考察的结果,语文应该是语言和文章。
再比如,王力先生在谈到语文时有两处不一样的表述。《在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第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王力先生说:“我们这语文课到底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呢?好像多数人的了解应当是语言文学。可是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而在《漫谈中学语文教育》中,他说:“‘语文’这个词有两种意义:一个是‘语言文字’,另一个是‘语言文学’。我想中学的语文课大概是指的‘语言文学’。1956年中学语文分科,就分为‘汉语’和‘文学’。”王力先生自相矛盾的说法,表现了他对语文的理解,即从一个语言研究专家的角度来说,他觉得语文应是语言文字;但他又看到多数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文学,于是又觉得中学的语文课大概是语言文学。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也认为“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以上种种都将语文看做是语言和文字的组合。但也有人强调,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王力先生所说的1956年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例子,可以证明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复合体。还有人提出过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化的说法,但影响不如上述几者大。
最为著名的当然是叶圣陶先生对语文的定义:“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新世纪出台的《语文课程标准》不再纠缠于从字面的两分来解释语文,而是从课程特点来为语文定性:“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从这个表述来看,它仍然是两种含义:从使用功能来说,它是工具;从承载内容来说,它是文化。对于包含在“语文”一词中的“语言”、“文章”、“文学”、“文字”诸因素未进行明确阐述。
要弄清语文是什么,不妨先撇开两分的思维定势,从学科本身的概念出发来做一番考察。所谓“学科”,在我们所讨论的范畴内有两个意义:一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一是学校教学的科目。前者指的是学术的分类,也就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那么语文是否能跻身其间呢?我们从语文的上一个层级开始考察。
时至今日,大概不会有人否认教育是一门科学,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教育学”也早已荣列一级学科,各地方的行政部门也设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教育科研。但是,如果稍微细致一点,却会发现,教育科研,尤其是我们的学科教育还是边缘化的。在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中,包括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等种种门类,却就是没有学科教育学。没有学科教育学,语文学科教育就无从谈起。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中国语言文学的门类去看,情况同样如此。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语言学”和“文学”,也可以在“中国语言文学”的统领下找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但却无法为“语文”找到它的位置。
语文之所以还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与它本身的综合性特征有很大关系。
如果取“学科”的第二个定义,即语文是一种教学的科目,是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课程”,那么,它的定义就应该包括“教学”这一基本含义,而不仅仅是内容的概括。合理的表述应该是:语文是对语言文字的学习。
从语言的角度说,语文包括对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学习,而以学习书面语言(或日“文字语言”)为主。因为“比较而言,口头语言是一种‘民主’的语言媒介,而文字语言则是一种等级性的语言。一个人掌握的文字符号越多,等级越高,越可能建立更复杂、丰富、深刻的意义世界。而要想掌握更多、更高级的文字符号,最有效、最有保证的途径就是接受教育”。
从文字的角度说,语文包括对文字符号本身的学习和对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文件的学习,以学习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文件为主。
对文字本身的学习基本只体现在低学段的识字教学中,之后的语文课虽然也涉及对字形、字音、字义的学习,但重点在于清除阅读障碍,而不在于对文字字形、字音、字义的理论性学习。
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文件包括各种各类文章。从目前语文教科书选文的情况来看,基本是由文学作品组成的。这并非因为语文课要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而是因为文学语言和日常的、科学的语言有很大区别,较之于后两者,它有更多精妙的表达,更适合用来学习。这也就是说,在学习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文件时,语文课以学习文学作品为主。
这样来定义语文,涵盖了“语言”、“文字”、“文章”、“文学”等诸因素,也为我们探究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奠定了基础。二、在明确内容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怎么写”上
当一篇文学作品放在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它“写了什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设计的第一个问题,往往也是关于这一点的。比如,学习葛剑雄的散文《邂逅霍金》,教师设计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作者写了一件什么事?”
“写了一件什么事”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最显著的特征。即使是非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只要把“一件事”三个字拿掉,“写了什么”依旧是教学的第一关注点,因为“写什么”是对文章内容的确认。然而,就文学作品的本质来说,有时更重要的却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形式”。
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世间可想到可说出的话,在大体上都已经被前人想过说过”,文学作品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它想出了前人从没“想过说过”的内容,而在于它不同寻常的想与说的方式,“变迁了形式,就变迁了内容”。如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乡思惆怅是常见的“内容”,这个“内容”对读者(包括学生)来说已毫无新鲜感可言,可是我们仍在被这样的一些诗歌所感动,关键就在于“形式”。正如朱光潜先生所列举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和“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表现同样的情致,而各有各的佳妙处”。语文课要学习的,正是这种“佳妙处”。
第二个原因是作者的“怎么写”,甚至可以改变事件的性质。写作的方法不同,不仅会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而且会让题材所代表着的“什么”发生质的变化。假如我们把内容设定为w(What),把讲述设定为H(How),那么,其结果公式将如下:
W×H≠WH
比如,《水浒传》中关于李逵杀人有这样一段描写:
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抡两把板斧,一味砍将来……不问官军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水浒传》的读者读至此处一般并不会憎恨黑旋风,反而会在心里充满痛快淋漓之感。这种阅读效果的产生,是作者的叙述方法使然。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假如这样的情景被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叙述:
宋神宗熙宁年间,汴梁有个官人,姓李,名懿,由杞县知县,除佥杭州判官……在任倏忽一年,猛思子李元在家攻书,不知近日学业如何?写封家书,使王安往陈州,取孩儿李元来杭州,早晚做伴,就买书籍……(李元)闻父命呼召,收拾琴剑书箱,拜辞母亲,与王安登程。沿路觅船,不一日,到扬子江。行至江边,却见一黑大汉抡动板斧迎面杀来,李元躲避不及,门面上中了一斧,顿时脑浆进裂,一命呜呼。可怜他的父母,一个在陈州,一个在杭州,如何想得到会有这等飞来横祸。
这个故事里的李逵杀人,在学生心头所产生的印象,显然就不同于《水浒》故事里的了。可见写作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比写作内容更为重要。
在鉴赏文学作品的时候,只关注“写什么”,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作品价值的。常听学生说这部名著“暴力”,那部名著“奸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只看了“写什么”,而忽略了“怎么写”。正是“怎么写”改变了事物的性质,赋予了它新的意义,文学作品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通奸”和“情杀”的事件,经由托尔斯泰和哈代之手,才具有《安娜·卡列尼娜》和《德伯家的苔丝》所表现的意义。因此,教师在教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引领学生在明确“写什么”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怎么写”上。
三、关注“在场”作品的同时,也关注“不在场”的作者
相对而言,在语文课堂上,文本是“在场”的。作为教科书,它被教师和学生充分关注。尤其是课改以来,对文本的研读越来越受到教师的重视。教师首先要把课堂的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用于对文本的研读。其次还应该充分注意“不在场”的作者。
教师在课堂上,都会用不同的方法介绍作者,笔者这里所说的作者“不在场”,是指我们在研读文本时,极易忽略它的“叙述者”。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说,作者和叙述者不能等同。但鉴于作者和叙述者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在散文中),我们在这里暂时把两者相提并论。当我们学习一篇课文时,很容易完全沉浸其中而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林嗣环的《口技》,它所呈现的内容有三个层面:第一是生活中的声音,第二是口技者发出的声音,第三是作者对口技者所模仿声音的描写。如果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第一层面,仔细分析写了哪些声音,是不够的。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其实并不是自然的声音,而是口技者对生活中声音的模仿,所有的声音都是从一张嘴巴里发出的,不注意这一点,口技者的技艺高超就无从谈起。但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也还是在第二层面。这两个层面都是“在场”的——有文字的表现。其实,更重要的是第三个层面:林嗣环把这个模仿声音的过程叙述出来了。正是他以观众身份的“叙述”,使我们不仅“听”到了口技者所模仿的生活中的声音,而且知道这是一场口技表演,因而为他的高超技艺所折服。作者使用语言的精湛技能,才是这篇课文的关键所在。由于林嗣环本人的“不在场”,这第三个层面就很容易被忽视。所以,教师应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去体味和感悟。
再如教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一文,教师一般会通过品读文本,让学生体会作者“对独立的、安静的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大自然的情怀”,看作者是如何“用比喻的方法,以神来之笔点出小屋的位置,接着用一组博喻来突出小屋点缀山,接着重点写小屋和树的关系”,“用暗喻和拟人,突出小屋的玲珑、小巧的特点”等。这些固然都是值得学习的表达技巧,但作为文学作品,李乐薇作为叙述者的存在是不能忽视的。这所建筑在山上的小屋,别的不说,仅是进出,就有诸多不便。爬山上到高处的过程,叙述者完全可以把它说成是一场苦役,在爬山的苦役中获得锻炼也仍然是托物言志,但文章所表现的主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是叙述者的基本立场,她带着审美的眼光来看小屋,小屋自然也就成了美不胜收的风景。如果忽略叙述者的存在,一味强调小屋的美和这种美是如何被表现的,最容易产生的后果,就是把“小屋”和“广厦”对立起来,这固然不能说是对作品的误读,但文学作品的一个本质特征——“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一个想象的世界”却被遗弃了,作者在平凡生活中发现、甚至创造美的精神和技巧也被遗弃了。
四、在“欣赏”层面之外,落实“表达”的需要
语文教学目标应该从内容知识、听说读写技能、学习或思维方法(认知策略)以及情感态度等不同方面着手设计。然而,对中学语文教学,特别是高中语文教学来讲,设置教学目标时又必须考虑听、说、读、写活动的特殊性。语文教科书之所以比较多地选用文学作品,是因为文学作品对语言的使用最为讲究。通过它更容易体会语言在表情达意上的功能。因此文学作品的教学,不要仅仅停留在对作品的欣赏上,而应该落实到学生对语言的使用这一关键问题上。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要表现在创作文学作品上,而且要表现在学生对日常生活的语言表达上,包括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书面表达可分为一般文字表达和特殊文字表达两种。一般文字表达指日常生活所需要使用的文字,可以分为几个层级:基础层级的标志性文字,如路牌、公交车站牌等;中低层级的告示类文字,如商品说明书、ATM机操作系统提示等;较高层级的文书类文字,如公函、报告等。文学作品则是一种特殊的文字表达。介于一般文字表达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就是语文课上的作文。
作文是学习文字表达的途径。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第一学段(1~2年级)在文字表达方面的要求是“写话”;第二学段(3~4年级)开始有“习作”;第三学段(5~6年级)写“记事作文,想象作文,读书笔记,常用应用文”;第四学段(7-9年级)开始“写作”,文体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日常应用文等。我们称为“一般文字表达”的文本都是有实用意义的,大部分的作文(除了课堂上很少写的“常用应用文”之外)显然不在其中。但作文又不是文学作品,这种特殊的文体离开学校的环境可以说是“百无一用”。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它是学习文字表达的工具,而课文则是它的学习对象。
教林嗣环的《口技》时,教师可用一段现代人表演口技的视频来导入,目的是激发学生兴趣。教师不仅要以颇具匠心的多媒体导引学生入境,从而提升作品的感染力,创设出学生“我想学”的氛围,还要让学生学习林嗣环的描写方法,自己来描写一下开始所听到的这段口技。且不说这样的导人设计首尾呼应,精简而实效,仅就学习文学作品的目的来说,教师的定位是准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每堂语文课都要以摹写为结局,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的表达能力,这一主方向是不应偏移的。教师要积极探索“读写结合”、“以读促写”甚至“以写促读”的方法,目的在于让学生在读或写上获得提高。其实,更加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作品精彩的语言艺术,不仅会欣赏,而且能学习。作文训练不能为写而写,重要的是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我们必须对这种特殊性给予足够的关注。只有从课程性质的角度进行思辨,我们的文学教学就会目标明确。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 王胜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