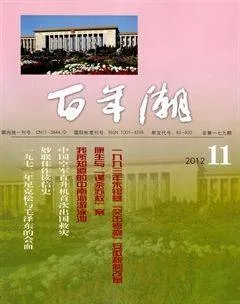“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不同声音
1972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文章,提出中学教学应“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在当时“教育革命”这个敏感的问题上公开表达了不同意见。这篇文章就是《分清路线是非,狠抓教学质量》,作者署名“沙中晨光”。40年过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出台过程却鲜为人知。经过对有关当事人多次访问,我们初步摸清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以及沙城中学当时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当中直接呼应毛泽东的指示,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968年8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当时推行“教育革命”的具体做法包括:实行“开门办学”,让学生走出学校,在学工、学农、学军的社会实践中,在工厂、农村的大课堂中接受教育,以打破“教师、书本、课堂”“三中心”;取消各级学校的考试制度,反对用“教育质量”和分数标准把工农子弟关在门外,否定教育中的等级制、智力主义的取向;高校实行免试推荐入学,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打击和降低教师的地位作用,批判师道尊严,等等。
1971年1月,“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第5个年头。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和“全面夺权”的混乱局面以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已建立起来,社会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但是,“教育革命”仍在主导着全国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分清路线是非,狠抓教学质量》的开头是这样交代文章写作缘起的:“去年一月,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党支部,派出由工宣队、干部和教师组成的教育革命调查组,走访了附近的工厂、农村,了解毕业生在工厂、农村的工作情况。工人和贫下中农普遍反映:‘近几年毕业的学生,政治觉悟高,劳动好,就是科学文化知识少一些。’许多毕业生也反映:文化基础知识缺少,适应不了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这个问题引起了学校党支部的高度重视。”
沙城中学党支部派出“教育革命”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走访,发现不少问题,提出中学教学应“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明显地与“教育革命”的口径不一致。可这篇文章为什么还能发表呢?原因就在于,1972年国内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九一三事件以后,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毛泽东也对这场运动进行了重新思考,开始在必要的范围内着手纠正极左思潮和做法。5月10日至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要求认真注意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8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10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时,对当时“教育革命”中不许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做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清路线是非,狠抓教学质量》一文被刊登出来。
沙城中学关于
“教育革命”的大讨论
我们的寻访工作是从沙城中学的退休老教师开始的。王庆华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位老教师,他是从怀来县委党校退休的。1972年,王庆华在沙城中学工作,是校革委会的办公室主任,他对文章的写作略知一二。他说,文章是王肃岐等人和当地驻军的一名战士写的,详细情况他不清楚。但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就是王肃岐还健在,居住在张家口,并提供了王肃岐的联系方式。
在与王肃岐取得联系并约定后,2011年9月9日,我们赶到他的家中。74岁的王肃岐须发皆白,因身患癌症显得憔悴不堪,但说起那篇文章来却记忆犹新,异常激动。“对,文章是我和张志写的。一个姓陈的解放军战士来沙城中学组稿,亲自送往报社的。”他靠在沙发里向我们回忆起熟悉的往事:
1966年和1967年两年,沙城中学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秩序很乱,学生不上课,成天戴着红袖标,搞串联,贴大字报,开批斗会、抄家。酷爱读书的王肃岐也不得不毁掉自己心爱的书籍和累年写下的读书笔记。他毁书做得不留痕迹,厚厚的一本著作,愣是花了很长时间,三页两页地揣在兜里,使劲撕碎,扔进厕所。后来革委会成立了,学校秩序稍微有了好转。担任校革委会主任的柳绩明果断发动大讨论,组织革委会成员、教师、学生代表就沙城中学的现状和未来进行反思。学校毕竟是教育人的地方,这样下去行不行?学校还办不办?学生混两年就出去了,初中毕业是小学程度,高中毕业连初中水平也没有,走向社会人家要不要?
沙城中学有组织的大讨论从1971年初开始,到1972年上半年就三个问题达成了共识。第一个问题是提高教学质量与“智育第一”的关系。搞革命还要不要上课,要不要提高教学质量?是不是提高教学质量就是“智育第一”,读书无用还是有用,读书无用错在哪里?什么叫“智育第一”,其表现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与“以干代学”的关系。社会实践、大批判和学校理论教学是什么关系,什么叫“以干代学”,“干”就是看手上的老茧?讨论中,听说有个学生毕业后成了养猪模范,物理教师于志沂说,“一万头肥猪也堆不出一颗原子弹!”如此掷地有声的话,敢于喊出来就是英雄,柳绩明当即肯定了于志沂的说法。大家认为,学校的本分就是抓教学,舍此,就是不务正业。革委会组织师生批判“以干代学”,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判轻视文化课教学的倾向,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系。通过批判会、学习会,大家明确了学生必须学文化,必须上好课,在学的过程联系实际,并且组织师生到怀来城校农场、校办工厂劳动,到4627部队参加军训。第三个问题是合理的规章制度与“管、卡、压”的关系。大家在思考,无政府状态究竟行不行,提高教学质量没有制度行不行,需要哪些制度,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大家认识到,学校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必须建立正常的教学制度、合理的学工学农制度和其他一切必要的制度。
统一了思想认识,王肃岐和张志就着手写这篇文章。初稿写了5000多字,发表时被压缩成2000字。文章共有三个小标题,即:提高教学质量与“智育第一”;理论联系实际与“以干代学”;合理的规章制度与“管、卡、压”。文章全面总结了沙城中学集体大讨论的思想成果。
现在来看看王肃岐的个人经历。他是1961年分配到沙城中学的,一直在教学一线。1968年,由王肃岐主笔、4627部队战士马奎元参与撰写的稿件《克服派性,增强革命大团结》几经修改,发表于1968年三四月份某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限于条件,我们没能查找到这期报纸,暂时存疑)。在谈到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时,王肃岐回忆说,当时他们住在北京一中,突击修改,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稿件在送给编辑部的同时也送到新华社,新华社华北组的冯代松编辑接待了他们,并提出进一步修改建议,直到凌晨三四点才终于改好,署上了“沙中晨光”的化名。不久,《河北日报》、《张家口日报》也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恢复高考以后,王肃岐连续多年教高三,1984年调到怀来县教研室任主任。1988年,王肃岐又回到沙城中学,直到退休。与王肃岐一起撰写这篇文章的张志已于前两年去世,而那位战士的下落一时也查找不出来,给我们的寻访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从王肃岐的家中出来,我们又去了沙城中学,在学校的档案室里找到了1972年制定的各种教学制度。那是刻写在蜡纸上的手写体,纸页虽然有些泛黄,字迹却清晰可辨。
沙城中学教学制度
1 全年上社会主义文化课不少于33周,其中复习考试每学期占三周(期中考一周,期末考两周)。学工学农全年占6周。不准随意占用上课时间处理班级工作,不准随意占用学生自习。教师有事需要调课者,必须经文教处批准。
2 加强计划性:学期开始必须认真制订教学计划,规定教学制度,明确教学要求,提出教改措施。
3 认真备课:认真备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各科教师必须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加强集体备课研究,要求做到以下几点:(1)备观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统帅教学。(2)备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学生实际和三大革命实际,充分利用实验室的教具和自制教具。(3)备双基:对全学期的教材内容要有全面了解,认真分析,确定重点难点,明确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内容。(4)备教法:运用少而精的原则及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每堂课要有一定的巩固练习时间。
4 认真批改作业:(1)作业目的要明确,要有启发性,分量要适当。(2)教师要通过批改作业,了解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知识的情况。(3)对学生完成作业情况要有记载,可按优良给予讲评,对经常不能独立完成作业的学生要及时批评教育。(4)语文教学每两周作一次文,要认真批改,认真讲评,对个别作文水平太差的学生要进行面批和辅导。(5)作业批改次数可根据担课情况由组内规定。
5 加强辅导工作:对学生要有计划地进行辅导和提高,对学习基础差的要进行补课。
6 教学质量检查:(1)期中期末考试后,各科进行全面总结,认真做好质量分析。(2)学校每学期抽查一至二次教育、作业和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3)学校每学期选定一定的科目、一定的班级进行检查。(4)坚持领导听课制度。
7 加强义务进修:每周保证半天业务学习或教学研究活动时间。
8 每学期组织一次学校性的运动会,每班一周规定课外活动二节,不得随意占用。
今天重读这些规定,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沙城中学教师坚守本职工作的勇气和胆识。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教学规定的缜密程度和可操作性也是极高的。除去这一教学制度,沙城中学还制定了学工学农制度,我们也把它抄录下来:
沙城中学学工学农制度
新的考试制度,反对分数挂帅,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通过考核进一步检查教学效果、总结经验、找出差距,改进教学工作。
1 考核的方法:(1)每学期学校统一进行期中、期末复习考试两次。(2)在系统复习的基础上,教研组统一出题,文教处审批后进行考试。(3)采取闭卷和开卷相结合,必做题和选做题相结合,书面和口试相结合的方法。
2 成绩评定:(1)成绩标准:百分制与等级评定相结合。试卷按百分计算,平时成绩按等级。(2)评分标准:学期考试成绩比重占60%,期中成绩占40%。可参考平时成绩和学习态度,学年成绩评定以第二学期为主,参考前学期成绩。
从条文可以看出,名为“学工学农制度”,实质上却是教学制度的补充和延伸。采访过程中,王庆华告诉我们,那时每个学期,他们有大约一个月的学工学农实践活动时间。王庆华清楚记得,当年的校办工厂的规模不小,有机工车间、钳工车间、电器车间、锻工车间、木工车间、制蜡车间、刨床车间和浇筑车间,总共8个车间,另外还有一个小印刷厂。每两周至少派一个班的学生,分配到各个车间学技术,其中以去制蜡车间的次数最多,学生基本掌握了制蜡的原理和技术。在劳动实践中,学生们深深体会到了没有文化课不行,因而更加热爱学习,更加努力钻研,更加促进了学风的良性发展,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王庆华回忆说,丛林里,操场上,到处是背诵的身影;自习课上,学生讨论争辩,独立完成作业。而老师们耐心帮扶,进行指导,浓郁的学习氛围随处可见。
“我们的果子一个也不丢”
谈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响时,王庆华带着孩子般的表情骄傲地说:“文章轰动了全国教育界上下乃至外国的学校,全国23个省市的中学纷纷来沙中参观,向沙中取经……”他特别提到,日本大阪市旭区旭阳中学一位署名大久保仪吉的音乐老师写来亲笔信,说文章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恳切询问教学情况和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这封信足有200多字,至今完好地保存在沙城中学的档案室里。
王庆华满怀喜悦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老师们按时上下班,兢兢业业,每天上晚自习,没有一个叫苦喊累的,他们都以在沙城中学教书为荣。学生努力钻研,好学上进,没有一个掉队的,“风气相当好!”最令王庆华感叹的是,学校实验室的每一件仪器都完好无损,这在当时全国的中小学都不多见。学校东边是个果园,秋天果实成熟后,无人偷着采摘。接受我们采访的另一位沙城中学的老教师廉润昶(当时担任校革委会副主任)补充说,前排教室前有棵大果树,枝叶繁茂,果实压枝,成熟的时候果子一个都不少。学校采摘后,再发给每一位同学。
还有一个情景让廉润昶至今难忘。北京市一所中学的师生前来参观,看到沙城中学安静和谐的校园环境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你们放假了吗?”二是“我们学校的桌椅板凳都损坏了,你们学校的课桌课凳是谁的?”当他们听到接待人员回答“我们正在上课”、“课桌课凳都是学校的,我们无一损坏”时,大加赞叹。张家口一所中学的师生前来参观,看到校园里柏树葱绿整齐,篱笆疏密有致,苹果又大又红,感叹道:“你们学校的纪律怎样,风气怎样,不用问就知道了。”负责接待参观的李泛(她是从北京一所中学下放到怀来的,她的丈夫赵拓曾担任怀来县人武部副政委,是电影《白求恩大夫》的编剧)满怀豪情地说:“是啊,我们的果子一个也不丢。”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