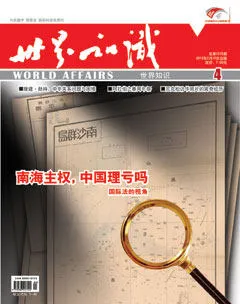中国应更多唱“文戏”
2012年龙年是中国的“本命年”,一个寄托了很多美好愿望的特殊年份。面对仍然不乐观的世界经济,很多国外媒体都把中国称为引领经济的领头龙(Leading Dragon)。如果说30年前的“开放”是中国面对西方的开放,那么如今的“开放”,则表现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新中国第一次走上世界舞台还是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当时的世界形势是,以中国为中心,在西线,越南在中国炮兵和军事顾问的支持下,用六万人把法军一万三千人围困在奠边府;在东线,志愿军把朝鲜战场稳定在三八线。周恩来总理身穿一件风衣,自信而傲然的走姿,令一旁的法国军人注目折服。为此周恩来说:“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
这里的“文戏”,一方面是相对于“武戏”的和平沟通,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文化价值观的推广和展示。一个国家究竟是唱“文戏”还是唱“武戏”,取决于该国家的国家身份定位。
建国初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是“革命国家”,就像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最主要的目的是生存。因此,中国当时是“武戏”为主,“文戏”为辅。英国学者弗·哈利迪在《革命与世界政治》一书中记述,1917年,被称为“红色拿破仑”的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他说:“外交部的任务就是发表一些革命宣言,然后关门歇业。”而1918年苏俄派往德国的第一任大使越飞,到德国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向德皇递交国书,而是向德国左派组织偷运武器,准备反对德皇的武装起义。因此,中国在日内瓦的“文戏”唱得好,但仍然不如朝鲜和越南战场上的“武戏”好。
而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家定位是“革命输出”国家,唱起了“进攻性的文戏”。西方国家的左派运动,拉美的游击队都受到中国的影响。毛泽东提出:“无论何时,只要有解放斗争存在,中国就会发表声明并号召举行游行示威,支持这种斗争。”但与此同时,中国推行和平外交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说明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文戏”为主“武戏”为辅。
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是“改革国家”。1978年,一名老外身穿毛料大衣,手插在兜里,气宇轩昂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引得身边的中国人“羡慕嫉妒恨”。这位法国时装大师皮尔·卡丹第一次来华的情景与周恩来总理到日内瓦开会的情景惊人相似。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韬光养晦”,处于文化守势。因此,在世界舞台上作为静观者的中国,也就谈不上“文戏”还是“武戏”了。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有些混乱。一方面强调“和平崛起”,但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都是以军事为衡量标志的;另一方面强调“和谐世界”,但它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理念,类似奥巴马提出的“无核世界”。因此,如果不能将目标、行动与路线图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就难以令人信服。这就要求中国告别模糊,重新站到舞台中央,唱一出新“文戏”。
首先,中国应该采取进攻性文化主义策略。新年伊始,胡锦涛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提到,中国受到来自西方国家软实力的攻击,中国需要进行还击。目前中国最大的中央级广电媒体资产总额约为350亿,仅为美国新闻集团资产总额的1/10。中国电视节目在海外“落地”也大多局限在华人较多的地区。因此,加大对媒体的投入势在必行。
第二,中国“新”文化必须具有消费性。美国学者雷默说过:“中国仍然习惯于那些老掉牙的戏剧文打武斗和平淡无奇的茶叶,他们还未意识到如何充分利用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美国的文化标志是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大片,中国也应该把自己的文化理念植入到“中国制造”的消费品中去。托洛茨基在20世纪20年代说:“一辆福特拖拉机与一只克罗索特枪同样危险,唯一的区别在于,枪支只能瞬间发挥作用,而拖拉机却时刻给我们造成压力。”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借助同样的消费文化冲击西方呢?
第三,文化战略应有机植入“和谐世界”理念中去。中国文化与“和谐世界”理论始终给人以“两张皮”的感觉。其实“东亚一体化”进程完全可以作为中国推行“和谐文化战略”的试验场。中日韩三国的共同文化基础就是汉文化。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日实力削弱。这就给中国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机会。
“文戏”既要多唱,更要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