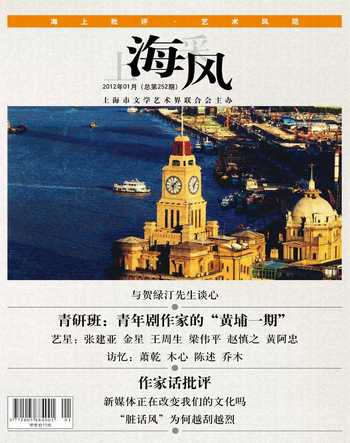跟随萧乾重温历史
姚曼华

去年6月,文洁若老师赠送我萧乾所著《从滇缅公路走向欧洲战场》一书。高兴之余,我不禁回忆起十四年前见到萧老的情景。
那是1998年春,萧乾先生及夫人的一位老友、我在外交部的老同事成幼殊约我同去看望住在北京医院的萧老。当时,这位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正坐在堆满书报、放置着各种治疗仪器因而颇显拥挤的病房中休息。见我俩进去,萧老喜悦相迎。我们刚挨近他坐定,就有全国政协机关的两位工作人员敲门进来,请身为八届政协常委的萧老填写九届政协委员候选人的表格。夫人、翻译家文洁若急忙上前接过表格,表示可以帮丈夫填写。不一会,又回头问萧老:“表上有一栏是‘有何专长,怎么填?”
“专长嘛,就是会写点小东西。”萧老回答时笑了笑。他笑得那么天真、自然,目光里充满了诙谐,令人感到在他身边十分轻松愉快。
闲谈中,我提到自己是云南人,因而对他写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印象极深。
“你是云南什么地方的人?”萧老和蔼地问。
“昆明人,地道的老昆明。”我回答。
“哦!我是1938年到1939年间在昆明的,就住在北门街。”萧老从容地回忆道。接着又说,“昆明人很老实,容易相处。在那段时间里, 我得到当地人的很多帮助,我对云南是有感情的。”
我高兴地点点头,说:“读到您文章中描写的筑路工人,不仅无医无房,甚至连伙食都没人管,许多人竟是白天修路,晚上讨饭,我简直无法想象和理解。”
“咳,当时政府没这笔经费,修路的任务又紧,不就把人征来硬这么干了!”萧老叹了口气,接着说,“那时在这条路上采访也很危险。有时清早出去一些记者,晚上就只剩两三个人回来,翻车啦!”
我真想继续听萧老谈下去,但怕老人太累,且又到了开饭的时间,我们便告辞了。
……
1999年2月,萧老不幸病逝。但我和文洁若老师一直保持着来往,也时常请教她一些问题。
重编在这本新书中的二十二篇散文,其故事所发生的地点,正好再现了萧乾当年由祖国的大后方去港,最终走上欧洲战场的道路。
这里应对萧乾与本书有关的经历作点介绍。1938年8月,当萧乾失业后辗转流亡到昆明困居之际,《大公报》社长胡霖决定创办香港版的《大公报》“作为抗战宣传的前哨”,复聘萧乾到港“共图大计”。
1939年夏,萧乾在港接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他担任该院中文系讲师的信函。富有远见的胡社长从经济上到思想上都竭力支持萧乾前往,因为他判断欧洲必有大战,这样,《大公报》在欧洲就有了自己的记者了,尽管是兼职。于是萧乾远渡重洋来到英伦,1944年,他果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访西欧战场的第一位中国记者!
阅读全书,笔者首先感到的是萧乾的强烈的爱国情感、民族自尊和奋勇抗争的精神。萧乾在书中多次写到海外侨胞挣钱谋生不易,并描写了他们艰辛劳动的场面,呼吁国人不能因华侨踊跃捐款支持祖国抗战而把他们看作财神!
萧乾也满怀热情地报道过鲜为人知的中国海员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贡献。当时,仅英国利物浦港就有两万名中国海员,他们大多从事最艰苦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工作:在底舱当火头军,船一旦出事,在船员中他们生还的可能性最小;二次大战期间,他们中有将近两千人献出了生命。
萧乾的这番爱国情怀,离开祖国后结合亲身经历,往往就表现为对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强烈反对了。《记坐船犯罪》就记述了作者从香港乘法国邮轮赴英途中,船上有诸多外国乘客,唯独四十二名中国人遭到法方人员令人难以容忍的种种欺侮和折磨。抵英不久,因受到房东太太的蔑视和毁约,作者还发表了一封抗议信。
不过,萧乾绝不狭隘。对英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他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在轰炸中,中年人顶替从军者担负起站在屋顶上瞭望的职责;警报一响,人们井井有条地进入地下铁道,常见到扶老携幼、相互照顾的动人场面……
十分感人的是作者在伦敦目睹的那些从敦刻尔克突围出来的法国士兵,尽管一个个满身泥泞地席地而坐,但依然唱着军队里流行的歌曲来嘲弄蔑视海峡对岸的希特勒。作者感叹道:“在危急时刻,这种气概,这种精神力量,对于一个民族的存亡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
1945年访美后,萧乾告诫中国读者:“不要只看到美国人的生活享受,更要看到他们的实干精神。”他还对比英美人的不同:英国人重门第,美国人重富轻贵,指出“倘若学美国的豪奢,再学英国的讲求出身门第,双料糟粕,那将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自尽。”这些话讲得多精彩,至今仍很有现实意义!
1944年6月,萧乾接受胡霖社长的建议,告别剑桥,在纳粹德国日夜的轰炸下,于伦敦舰队街挂出了“《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的招牌,随后又通过英国新闻部取得了战地记者的资格。他穿上军装,戴着绣有“中国战地记者”字样的肩章,感觉极好!为了让成亿的中国读者尽快读到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萧乾乘坐空军营救艇强渡布满水雷的英吉利海峡,然后穿越法国去追赶自己所属的美国第七军。在法国境内极目所见,都是被战争破坏的痕迹。巴黎“容貌憔悴,意态消沉”,到处都能碰上神气的美国兵,能嗅到美式生活的气息;最骄傲自己语言的法国人,居然在各个店铺的橱窗上挂出大字招牌:“我们说英语”。这里,作者向我们揭示了人生的无奈!
作者以他那记者的敏感和文学家饱含感情的笔,生动细腻地记下了刚刚战败的德国所呈现的种种景象。一路上不是难民就是俘虏,荒芜的葡萄园,被炸毁的坦克旁躺着戴钢盔的尸骸,寻找食物的饥饿人群。“从柏林到波茨坦可以说是从废墟到废墟”……不论在乡村还是城市,挽着美国兵的胳膊,嚼着口香糖游荡的德国女郎总是常见的一景。《仆仆风尘到慕尼黑》中的“女裁缝的自述”这一节,可以说是此种景象的“续篇”或“连环画”,值得读者品味。
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谈及了参观希魔一伙在慕尼黑发祥和进行活动的政治“古”迹。在细细端详了那些被炸毁的可贵希腊式建筑和巴比伦雕刻的残迹时,作者发现自己脚下踩过的,不是大理石的断腿便是肩头首级。作者深有感触:“这不是好逛的地方。真好像来扫全欧文明的坟墓。”这是对战争的控诉啊!
在德国,萧乾还专门采访过美军临时组成的军政府,旁听过对较低级纳粹杀人犯的审判,在纽伦堡参观了关押着二十三名纳粹主犯的监狱,走访了希魔于1933年在达豪建造的第一座集中营(设备齐全的杀人工厂),又到过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作者赞赏此处村民的生活中浸透了艺术,也耳闻了美国军官贪婪攫取财物的得意谈话。此外,他又别出心裁地采访了在德国的数十名中国留学生,受到国内读者特别是学生家长们的热烈欢迎和感激。
期间,最重大的事件也许就是到美国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作者认为,这是“在国联失败后,全世界集体安全的又一次试验”。读者可在书中读到关于大会的详尽报道。给我启迪最深的,是萧乾从整个大会领悟到的一个道理:“个人与个人之间,有时兴许会出现利他主义,但国与国之间,只会出现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连标榜‘工人无祖国的苏联也不两样。在歌剧院讲台上,只见争,绝无让。”这话说得何等精辟!对观察和分析今天国与国的关系同样适用。
纵观全书,我感到最值得细读的还是《血肉筑成的滇缅路》。1939年春,作者专从香港赶回昆明,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条正在修筑的路上来回奔走采访,一连发表了五六篇有关通讯,最受读者欢迎的显然也是这一篇。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中描写许许多多意志坚强的汉人和兄弟民族,为了抢筑这条对祖国生死攸关的生命线,壮烈牺牲在汹涌的山洪里,惨死在“瘴毒”的魔爪下;特别是在开凿惠通桥时的山岩爆炸中粉身碎骨,其状之可怖,其情之悲壮,常令人含泪屏息,不忍阅读下去。让读者尤为敬佩的,是这些路工们朴素高尚的爱国热情。一位从山洪中死里逃生的路工自语道:“怨谁呢?我谁也不怨。这就叫国难呀!”还有一位老秀才,带着儿孙同来修路,他常在放工时主动对路工们演讲这条国防大道的重要,并引用历史上举国对抗入侵暴力的掌故。这位为公路贡献余生的老人,最后也被瘴气摄去了生命。临死时,还望了望那行将竣工的公路,脸上浮起一片笑容……
现在,这条公路几经修整和改道,已成了相当宽阔的高速公路,还是一条挺热闹的旅游要道。但是,请听听作者的提醒:“有一天,也许你会跨过这已坦夷如平地的横断山脉,请侧耳细听,车轮下咯吱吱压着的有人骨呵!”
萧乾还写道:“长城的建筑史已来不及搜集了,我们却应该知道滇缅路上那些全凭人力搭成的桥梁是怎样筑成的。”写于1939年的这篇散文,详细而形象地记载了修筑之艰难堪与长城相比的滇缅公路的建筑情况,文字凝练优美,充满激情,意蕴深厚;既是翔实准确的史料,又是感人肺腑的记功碑和颂歌——歌颂了中华民族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伟大创造精神。
而在《在滇缅路开放之前》一文中,萧乾尖锐地揭露了1940年7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悍然与日本侵略者签约封锁了滇缅路这一不义的出卖行径,并介绍了数万英国民众(包括社会名流)签名请求“立即开放滇缅路”的情况;该文于当年10月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与此同时,萧乾还应援华会的邀请,在英国许多城市做过关于滇缅路的演讲。
五十多年后,萧乾曾这样回顾道:“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有数不尽的桥梁。然而没有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足以载入史册。……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条公路同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的了。四十年代,滇缅公路不仅是一条公路,它是咱们的命根子。”
请翻开此书,让我们跟随着萧乾,去重温那段既充满血腥和正义,又充满着教益的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