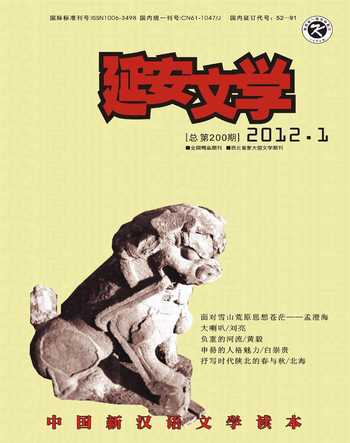请原谅我带走那只陶罐
史鹏钊
请原谅我带走那只陶罐
故乡,请原谅我带的那只陶罐
这也是村庄的惟一口粮,经受不起
山雀那长长的口舌,最轻柔的啄吻
陶罐的皱纹参差不齐,看不清方向
就是月光,也不肯入眠
在栅栏的露水上吮吸秋天
故乡,请原谅我带走那只陶罐
所有的风和白草一起,掀起波浪
淹没的田鼠,只能靠存贮的时光度日
陶罐底层的谷,颗大粒饱
收割丰盈的背后,是场院汗漫的痛
那只陶罐我抱在胸前,是多么兴奋
故乡,请原谅我带走那只陶罐
历史的划痕,是块难以愈合的伤口
陶罐是在乡村的深处,埋藏了许多年的
旗帜和图腾
雾是落满故乡的棉花
雾落下来,故乡就柔软了
满天的棉花,一团团
是母亲花费了一夜时间
从天空坚硬的壳里
剥落出来,撒满了故乡
父亲还没回来,他起得早
就去地里冬灌,满地苗株
都咕咚咕咚地喝饱了
他蹲在田头,把倒下去的
一棵棵地扶起来,稀疏的头发
愈显得让人心痛地白
雾是故乡,这个季度里
颗粒饱满的棉花,每当洒下来
柔柔地,痒痒地
把整个村庄填得丰满起来
我的心里就不再空落落地
雾是落满故乡的棉花
我多么地想一直捧在手心
怕洒了
为故乡捂热一颗籽种
半截秸秆的能量,袅袅地燃烧
故乡滚烫了起来,在这眨眼就凉的秋天
爬行了一辈子的蚂蚁,在黄豆荚里取暖
高粱垂下了头,打着盹。阳光不再刺眼
夜半的蟋蟀,成了乐团的非著名歌手
一曲曲弹奏,露水在深夜铺下来
湿了我无法前行且伤痛的脚趾
故乡的夜渐行渐远,没留下一丝灰烬
我身下是一片捂热了的土地,感谢植物
它老了,即将入冬,落入尘埃
身体骨渐渐酥软,白露的霜是一把
四季更替而又无情的利剑
我再也握不住故乡的双手,我是外来者
一把麦子能够填满我一生的胃口
当我走进故乡,我就留下这唯一的籽种
紧攥着,体温回升,然后埋入心脏
村庄的田地来年至少会变得葱茏
和父亲说墒情
给父亲打电话,他还是那么忙
穿着保安的衣服,显得很是单薄
在巴掌大的台子上,咬着牙
挺直着腰杆,他的腰病
三十年前就落下了
给父亲打电话,说起墒情
故乡的山田,还有一亩闲着
该是种豆子的时节了,天旱
红岩河的水,经受不住
吃夜草的老黄牛,一气地畅饮
墒情是庄稼的晴雨表
庄稼是父亲的另一些儿女
他比我们孝顺,永远不会离开
即使父亲老了,哪里都去不了
故乡的麦穗、豆苗、高粱和玉米株
都温顺地偎依着,在父亲脸庞上
那深如沟壑的皱纹深处
等一场透雨,淋漓尽致地落下
一棵白菜陪着母亲度过冬天
一棵白菜,从地里拔回来
潮湿的泥土里带着地气
作为粮食,陪母亲度过整个冬天
午饭,是白菜面团
晚饭,成了白菜糊糊
白菜是那个冬天的全部粮食
白菜是那个冬天的全部菜肴
一棵白菜陪着母亲度过冬天
多少年了,一提起她就揪心
就是那棵白菜,在1970年的冬天
成了自己一生无法感谢的恩贵
现在的白菜,一层层地被母亲剥下来
一瓣瓣地洗,然后腌制在瓷罐里
就像她的头发,一根根脱落
成为我在冬天里最大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