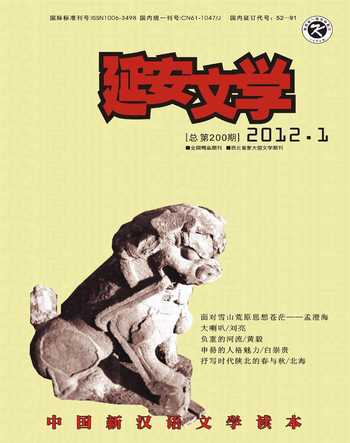九合
单志伟
1
延河流经董家河村时拐了个弯,在南岸留下一片河滩地,约莫五六十亩。河滩地头便是南山,南山东侧有条小河,叫安沟。村里人在安沟里筑了一座水坝,将河水引出来浇地。这五六十亩水浇地在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可是块宝地。有了这块宝地,董家河在前后川十里八乡都算是颇为富裕的村落。
董家河座落在延河北岸。村里在河滩地岸边箍起两眼小石窑,每年庄稼快成熟时,会派人暂住在那里看青。九合跟叔伯姐姐两人逃难来到董家河村后,村里将那两眼小石窑借给姐弟俩栖身。九合姐姐出嫁后,剩下九合一个人住在那里,村里没有收回石窑,这也省去了每年派人看青的任务。
1971年春,县里对部分北京知青的安置地做了调整,我被调整到了董家河。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了九合。
那天,康金贵队长给我派活儿,指着河对面南山根下那两眼小石窑说:“你去把九合叫上,你俩去坝上放水浇地。叫九合把工具带上,引水渠要是有泄漏的地方赶紧修上。水可金贵哩,可不敢糟蹋了。”
第一眼看到九合时他很黑很瘦,头发很长,把耳朵都盖住了。穿的衣服虽然不是多么破旧,但是很脏,窑洞里的光线非常昏暗,但还是能看到他衣领上的污渍泛着亮光。他四十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交谈几句之后,我就感觉到了九合的内心跟我一样孤独,这不由让我对他产生了一丝亲切的感觉。
那天我们两个去坝上放水,走到坝前,突然看到坝梁上趴着一只甲鱼。北京管这东西叫“王八”,陕北人称“鳖”。那只鳖听到响动,“滋溜”一下滑进水里。九合衣服都没脱就跳进水中,一个猛子扎下去,再露出水面时,手里举着那只鳖。我佩服得要命。陕北是个缺水的地方,会水的人不多。九合竟有这手段,实在是让我刮目相看!
那天收工时,九合在鳖的壳边戳了个洞,用树枝将鳖穿上,交给我说:“提上,回我窑里,我给你熬鳖汤喝。”
那晚我在九合窑里待到很晚,聊了很多。
九合说:“我家当年阔得很,榆林城里有名哩!种着上百顷地,喂着十几头大牲口,雇着几十口子长工哩!”
“你上过很多年学吧?”
“是哩。先是把先生请到家里教书,后来到榆林城里念的洋学堂。”
当我们聊到村里的事情时,九合却是一脸的不屑:“除了支书李生贵,没有一个好人,一群没文化的老土鳖!”
九合昂着头,很自负的样子。
村里人对九合的评价却不高,有的说他是“半憨子”,有的说他是锅揭得早了:不熟哩。一致的评价是:九合是个胆小鬼——怂包软蛋!
我不相信,九合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
“你们说的是真的?我不相信。”
“你才来多少日子,知道个甚?”
老乡告诉我,当年九合跟他叔伯姐姐逃难到董家河村,到各家门上去讨吃。康、董两大姓的后生看到九合姐姐,稀罕得要死要活。
“那真是好人才哩。”
那时候董家的人当着村主任,康家的人当着队长。两家的后生都去缠磨各自的老子,让把九合姐弟留下来。
“没有他姐,九合能落到这村上?”
村里将看青的两眼小石窑借给姐弟俩栖身。逃难的人算是有了落脚地,麻烦也随之来了。
“那几个后生天天去缠磨。九合看见那些人来,吓得躲到窑后掌去,任他姐受欺负,响屁也不敢放一个!多好的一个女子,生生让那几个后生坏了名誉。后来远远地嫁了人。”
“九合说他家当年是大财主,怎么会成了逃难的?”我问老乡。
老乡说这话拉起来就长了:当年普查的时候村里派人去九合家乡调查过,九合的家庭成分确实是地主,但不大,小地主。九合的爷爷辈儿还是贫下中农呢。可是他爷爷养了两个儿子。胡宗南进攻陕北时,弟兄俩偷偷给国民党带路。国民党败了,他大伯跟上败兵跑,让流弹打死了。他爸偷跑回家,让民兵抓住交给了政府,政府判了死刑。枪毙他爸那天,先绑上游街,再枪毙,都让人摁跪到刑场上了,他爸还梗着脖子骂哩。
我都听呆了。
“他爸行啊,像条汉子!可九合咋会这么怂包软蛋?”
“吓的么。他妈引着他去等着给他爸收尸,枪一响,把鳖怂苦胆都吓破了。”
“真的?”
“真的哩。不信你去他肚上摸摸,看鳖怂苦胆是鼓着还是瘪毬着哩?”说着老乡哈哈地笑了。
村里人一百只眼睛看不上九合,可谁家有事情,叫的却总是九合。
“九合,我家窑面叫雨水打坏了,你来给我抹上!”
“九合,我家院墙倒了半边,你来给我垒上!”
“九合,我家老母猪发情了,你把它牵上去枣林子老黄家,让他家那头骚公猪给配上!”
九合一万只眼睛看不起村里人,可谁叫他,他都欢欢喜喜跑去给人家白帮工。
我说:“九合,这样白帮工,耽误了挣工分,年底分不下粮食分不下钱,日子咋过呀?”
九合不这么想。他说:“咋样?村里离不开我吧?没了我,他们的日子麻达啦!”
九合认为自己是村里的一位重要人物。
而且九合的账也算得清清爽爽:想占我便宜?瞎了狗眼窝!
“我一顿吃了鳖怂六个白面馍!”九合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泛着亮光。
九合很节俭,过日子仔细得很。他蒸一锅玉米团子要吃三天,为的是节约烧柴。团子都霉酸了也舍不得扔掉。但有时大方得吓人,如果村里哪个人碰见,说,“九合,你这驴日的鳖孙!听说你做的饭比婆姨们做的还好吃,你可真能行!哪天给爷爷做上一顿尝尝?”
九合听见这话,浑身的骨关节都松泛了。他会把珍藏起来舍不得吃的白面拿出来,给那人烙上一张白面馍,看着那人舔唇咂嘴将白面馍吞进肚里,九合咽下一嘴口水,期待地问:
“咋样?”
“美气死啦!九合,你这驴日的鳖孙,可真能行!”
最少十天——九合像是踩在云里雾里。
九合是我的朋友,我替九合发愁,觉得他应该有个婆姨管上,省得成日里东游西逛。
我问九合:“你咋不要说上个婆姨?”
九合默然,半响,说:“要那做甚?一个人活得自在哩……”
我知道九合说假话。我听见九合哑起嗓子唱:
乾隆四十年哟,世事不周全,什么人留下咱这光棍汉?
出门一把锁哟,回家一把火,你看咱这光棍汉好恓惶……
九合分明是想婆姨哩。
可要给九合说上个婆姨也真难:他是外来户,没有根基,连住的窑洞都是村里的,而且只有一眼有门窗,另一眼只用几捆玉米杆挡在窑口。窑里只有一口铁锅,一只装水的缸,一只腌酸菜的缸,用九合自己的话说:“咱这窑里——毬干毛净!”而且九合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只能挣个女人家的工分。想想替他愁也愁死了。
然而九合有自己快乐。
九合爱跟婆姨女子们嬉笑打闹“犯骚情”。因为九合只算半个劳力,队里派活时经常将他与女人们分在一搭儿里。那是九合最快乐的时光。他会尖起嗓子唱一段酸曲,把女子们羞得背过脸去笑,婆姨们笑骂着追打九合,九合快乐地逃命。
九合不总是嬉笑打闹着混光景,他有时会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有一次他就跟我讨论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属于哪个学科:玄学?哲学?社会学?还是其它什么学科,总之是个大问题:关于转世托生的问题。
他先很严肃地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下辈子你想托生个甚?”
我想了想回答他:“想托生个鹰,鹰多自由啊!它不服从任何人的管束,它只……”
九合摇着头打断我:“不好。鹰活一辈子辛苦哩。春天里要先筑巢,筑个巢少说要一个月光景。母鹰下蛋后就不出巢了,剩下公鹰独自去打食。打食难哩,山鸡野鸡看见鹰来,一头钻进沙蒿刺。鹰身上被扎了刺,因为鹰的嘴大,又是个弯钩钩,挑不成刺,只好等化脓了刺自己出来。出来一根刺,带下一根羽毛。羽毛掉多了,鹰就飞不成,要活活饿死哩。鹰去拿兔子,老兔子看见鹰来,趴下不动,等鹰翻转身子扑下来,看看快到面前了,老兔子突然一蹿,两条后腿用力一掀——沙子石子掀到鹰眼里,鹰迷了眼,飞到空里寻不着南北西东,一头撞在崖畔畔上,撞死了。母鹰等不回公鹰,又舍不下自己的蛋,活活饿死了。托生鹰和托生人一样,活得不自在哩。”
“那你下辈子想托生个什么?”我反问他。
九合脸上现出一个诡异的笑容,问我:“你看见过公社那配种站么?”
“看见过。”
“看见过那头大黑叫驴么?”
“看见过啊,咋啦?”
“我下辈子就像想托生那叫驴哩。”九合自嘲地笑笑,“活着时整日里就干那种舒坦的事情,哪怕后人把咱送进汤锅里去呢,那也算值了……”
2
一天夜里,村里饲养室草料窑里来了个婆姨。康聚财老汉半夜里给牲口添草料,提盏马灯去抱草,看见了。那婆姨三十四五岁年纪。老汉问:“哪儿来的?”
“上头。”
陕北有“上头”“下头”之分。绥德、米脂、榆林一带称“上头”,延安、延长、宜川、延川一带称“下头”。下头人说到上头人时,神情语气中含点高人一等的味道。
“上头甚地方人?”
“米脂。”
老汉将婆姨细细地看了一回,果然名不虚传:米脂婆姨好看,全陕北第一。有顺口溜儿为证: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那婆姨虽然面有菜色,却生得眉清目爽,肉细皮白。
“到我们这搭做甚来啦?”
“讨吃。”
婆姨告诉老汉,上头去年旱坏了,黄风、沙尘暴飚了够半年。
“那风刮的,把我家院墙都推倒了。秋后生产队分粮食,带皮粮食每个人分了一百多斤,你说叫人咋吃么?没办法,跑出来寻个活命哩。”
“你老汉哩?”
“死啦。”
“你这种时候跑出来当盲流,叫公安看见麻达呢。”
“怕甚!比饿死强吧?抓住了能咋,枪毙我呀?”
“你叫个甚名字?”
“番娥儿。”
“好名字哩。”
“好名字顶屁的用,命不好。”
康聚财老汉五十三四岁,三十岁时婆姨生娃落下个子宫下垂的病症,从此断了老汉的念想。夜里睡觉,婆姨躺在身边,看得、闻得、摸得,却动不得,锅里有水没米——干熬。老汉受不住那份煎熬,便找当队长的侄子康金贵商量,谋下这份饲养员的差事,夜里来跟骡子做伴儿,眼不见、心不烦。眼下见了这婆姨,却似窑顶畔畔上跳下来个貂蝉妹子,把老汉看得那心撞得肋骨疼。老汉熬不住心里的那份麻缠,便涎下脸皮和番娥儿婆姨叙谈商量了一番。那番娥儿婆姨本不愿意,搁不住康老汉软缠硬磨,许下二十斤麦子,又打下保票:去跟当队长的侄子说说,保证让番娥儿婆姨在这村里住上一年半载,把荒年景熬过去。番娥儿婆姨思虑半响,想想眼下这处境,便心叹一口气,再把心一横,闭上眼咬上牙,憋上一口气,半推半就地成全了康老汉。
康老汉快活半宿,像一捆晒蔫巴的老韭菜又给浇足了水,梗梗地生动起来了。
第二天,康老汉没食言,跑去找当队长的侄子康金贵商量。康队长去看了,心里也愿意将这婆姨留下来。康队长四十七八,正当壮年,清清爽爽一条汉子,婆姨却胖得有他两个半粗,还是个“河东吼”。想着把那婆姨留下来,怎样留却是个难事。随便接收一个盲流,上面知道那还了得!正是“阶级斗争是纲”的年月,叔侄二人没主意,去找支书李生贵。
李生贵是外来户,在村里是小姓,只此一家姓李。上面安排他当村支书,是为了平衡康、董两大姓的势力。那李支书没什么本事,最大的本事就是和稀泥。听了康队长说明,自己不拿主意,倒是出了个主意:把村革委会主任董絮财找来一块商量。
董絮财主任也是四十七八岁,粗粗夯夯一条壮汉。婆姨和他同岁,年轻时干活使过力,四十岁出头就驼了背,陕北人称为“背锅”,自然再做不好夫妻之间那点事。董主任没有了地方交公粮,熬得倒像半年没吃上粮食的耗子。得了这个信儿,三步并做两步行,去草料窑里考察了一回,心下自然是愿意的。
董主任、康队长,村里两位主要领导,再加上一位李支书,自然有了好主意:把这婆姨说给九合做对象,名正言顺地留在村里。
中午,李支书婆姨做了一锅油泼辣子面,招待董主任、康队长、番娥儿吃饭,同时将这好主意告诉给番娥儿。番娥儿婆姨心下只能愿意,心里暗想着,只不知这九合是个甚样人?
吃罢晌午饭,三位领导引上番娥儿,准备过河寻九合。还没走出村,迎面碰上康队长的婆姨。那婆姨见了这几个人,哼了一声,似笑非笑地说:“几位当家的,交上桃花运啦?”
康队长已经感觉脚腕子发软,脸上赤橙黄绿的。李支书赶忙解释:“她婶子,可不敢耍笑哩。这婆姨家里遭了年成,老汉又死了,撇下一个男娃一个女娃,还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你说可咋活哩嘛?这不,夜黑里寻到咱村上。我们几个商量,把她给九合说上,过后把老人娃娃接下来,娘们几个逃个活命,九合也活成个人家。她婶子,你说这不是个好事情?”
康队长婆姨哼哼冷笑起来:“咦,李支书,你这眉户剧唱得有板有眼哩!……我还不知道你几个的花花肠子?”
李支书苦笑:“她婶子,你说我……”
“噢,我没说你,我知道你是个正派人。我说的是那两个瞎怂!九合他姐嫁远了,你两个够不上了,这会子给九合张罗个婆姨!九合得稀罕死!不是稀罕婆姨,是稀罕你俩给他送过去个顶大号的‘盖老帽子(盖老帽子即绿帽子之意)!”
董主任脸上有些挂不住,讪笑着对番娥儿说:“妹子,你可不敢往心里去,你这姐就爱摆个笑谈。咱赶紧去寻九合,见了你就知道了,那可真是个老实人哩。”
康队长婆姨将番娥儿上下打量一眼,转过脸对康队长喝道:“收起你那根花花肠子,跟我回去!”
康队长跟上婆姨回家了。李支书、董主任引上番娥儿出了村。
九合、番娥儿两个人见了面。看到九合这表人才,番娥儿心下觉得实在委屈了自己,转念想想,盲流的日子实在难过,上面公安抓得紧,可家里老人娃娃三张口等着要吃哩,不盲流讨吃咋办?可光盲流讨吃能挣几个?解决不了甚问题呀!过光景就像爬个大坡坡,眼下碰上个陡坡坡,咋办?寻上个拉帮套的帮一把吧,管他是驴是骡子还是个马,憋上一口气,努力上一把力,把腰杆杆一弓,不就上来啦?
想到这里,番娥儿觉得心下松快些。她细细把九合窑里看了看,确实像九合说的那样:毬干毛净。但窑后头荆条编的囤里粮食装得冒出了囤口;番娥儿婆姨把腌酸菜的缸盖掀起瞅瞅,满满一缸酸菜散发着淡淡的甜酸味儿。
番娥儿走出窑外透口气。看到地里的麦苗虽然熬了一冬天,那枯黄的麦叶仍梗梗着脖子不肯倒伏下去,等着春天,等着一场好雨水。番娥儿下了决心,回到窑里,对着窑里的三个男人说:“我愿意。”
董主任先欢喜得堆下一脸笑来:“妹子,你踏踏实实住下,有甚难处跟哥说,哥包下啦!”
李支书是个谨慎的人,嘱咐番娥儿:“你细细想好哩。要真愿意了,让九合驮上些粮,村里给公社粮站开个介绍信,把粮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和钱,你拿上做个盘缠,回家开个介绍信来,跟九合把结婚证扯下。你两个在队里挣工分,再把老人娃娃们接下来。”
倒是九合,虽然装了一肚子学问,平日里跟村上的婆姨女子们犯骚情时伶牙俐齿,眼下真送来个活人,倒像让箭穿了雁嘴,被钩搭了鱼鳃,就剩下门牙帮扶着舌头在口腔里捣蒜。
晚上该收拾睡了,九合心里犯了难,只有一床被子,可咋睡呀?想了想,九合上炕把那块羊毛毡子揭起来,卷上,抱起,下炕准备走。番娥儿在一旁说了话:“去哪里啊?”
“我去旁边窑里睡呀。”
“那还不冻死?”
“不怕。”
番娥儿从九合怀里拽回羊毛毡子,铺在炕上:“一搭里睡吧。”
“你看是个这……”九合呐呐地说:“你这样一个人,眼下遇上些烦难,我……我不能在这时候占你便宜哩……”
番娥儿没再说什么,上炕铺好被,自己先脱了衣裤,钻进被里说:“一搭里睡!”
3
下地干活遇到九合。歇息时,我把九合叫上,找个阳坡坡坐下。我问他:“番娥儿答应嫁你啦?”
九合不回答,两眼亮亮地看着远方。一会儿,扬起嗓子唱:
崖畔畔上开花崖畔畔上红,
受苦人盼着个好光景!……
我知道九合心里快活哩。
那天早起天就阴得死沉死沉,队长给大家放了假,村里人都欢喜。大家盼的就是:天上黄澄澄,地下刮大风,刮风就下雨,下雨就歇工!我正好有机会去九合家里串个门儿。
去了没说上几句话,董主任大摇大摆推开窑门进来了,看到我和九合,大模大样对我们说:“九合,还有你——北京娃,你两个出去一下!我有个重要事情要和番娥儿叙谈叙谈。”
谁都看出了董主任的司马昭之心。九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心里也感到了莫大的愤怒!
我说:“董主任摆笑谈吧,你跟九合婆姨说话,咋把九合撵出去?”
“咦——九合婆姨?他俩聘定钱交上啦?结婚证扯下啦?交杯酒喝过啦?先人牌位拜罢啦?……摆笑谈哩!把他往大了说,他也就是个拉帮套的驴么!他能拉,我不能拉?”
番娥儿听到这里冷笑起来:“董主任把话说得明白哩!那我就实告诉你:拉帮套要出些真力气呢!你要拉?行哇!拿来吧!”
“甚?”
“钱!”
“多少?”
“五块!”
“我那天老爷哇!你那里镶上金边啦?这么贵!”
番娥儿恨恨地说:“告诉给你,我有老人娃娃等吃哩!我在这里跟你干耍,让我老人娃娃饿死呀?!”
董主任悻悻地走了,然而终究熬不过心里的那份瘙痒,没个抓挠处。后半晌,带上五块钱来寻番娥儿。
番娥儿收了钱就放董主任进了窑……
九合远远地躲到南山崖畔畔上,跳起脚扯着脖子骂:“董絮财——!你这个老叫驴,总有一天不得好死!”
转过脸看见目瞪口呆的我,九合愣住了。
半晌,九合似乎才缓过神来。他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假做轻松地对我说:“我不稀罕搭理那些鳖孙!都是些没文化的老土鳖!……把我惹恼了,我骂他们三天三夜不重了样!”
我感到好冷好冷,心都给冻住了。
当天夜里,九合像是掷骰子输了钱,一心要把本钱捞回来似的,将番娥儿下死劲折腾了一宿。那番娥儿却是出奇地温柔,任由九合在上边要死要活,只是不做一声。
没多久,前后川十里八乡都知道了董家河有个番娥儿婆姨。有些害了馋痨的老汉后生便寻上门来。番娥儿来者不拒,一律明码标价:五块。
康队长偷偷去了两次,却是赊账。好事情办完想赖账,番娥儿直接寻到他家门上!
康队长婆姨气得四只脚往八下里乱蹬,把番娥儿骂了个狗血淋头。番娥儿只是冷冷地摔下话来让她听:“有本事把你老汉的裤带拴紧了!到食堂吃饭还得掏钱呢,想白白得便宜,门儿都没有!快掏钱!”
过了一段时间,上面似乎风闻了一些事情,派来两位公安调查情况。李支书亲自接见的。李支书平日谨小慎微,见了上面人却是另一副面孔:我就是上面挑选出来做支书的,上面人我怕谁!大不了继续当农民,正不想干这费力不讨好的毬差事!
“哪有这一回事情啦?哪个鳖孙放下这臭屁?人家九合全全正正一个好男人,番娥儿全全正正一个好婆姨。就差扯上一张结婚证,再把老人娃娃接下来,好好一家人哩!”
李支书来劝番娥儿:“跟九合把结婚证扯下吧。有了结婚证,就是咱董家河的人啦,就能下地挣工分啦。再把老人娃娃们接下来,好好一家人哩。”
番娥儿感激地抹眼泪:“我老汉死了不上一年哩。扯结婚证要回去开证明,惹村里人耻笑哩。转过年再说吧……”
李支书叹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忧心忡忡地走了。
九合好想和番娥儿名正言顺做夫妻。
“咱两个把结婚证扯下吧?”他试探着问。
“你不嫌弃我的坏名誉?”
“不嫌弃不嫌弃!你是为了老人娃娃们没办法哩!咱两个把结婚证扯下,看哪个鳖孙以后敢再过来欺负你。”
“我一大家人让你养活能把你累死。”
“不怕!我能行哩。我告诉你,我攒下一百块钱哩,用油纸包包裹着,瓷罐罐里装着,灶头地下埋着哩。你等我把它刨出来,都给你拿上,给老人娃娃们寄回去。”
“我不要你那钱,你好好收着吧,等以后寻个比我好的……”
“我就看上了你。”
番娥儿叹口气,伤感地看着九合。
下地干活遇到九合。歇息,我把九合叫上,找个背坡坡坐下。我问他:“番娥儿答应跟你扯结婚证啦?”
九合不回答,两眼呆呆地看着远方。半晌,压起嗓子唱:
荞麦羊腥汤,
死死活活相跟上……
我知道九合心里难活哩。
番娥儿顶着毒日头去了县城。
半后晌回来时,肘弯弯里夹着一卷布料直接去了村里,寻到董主任、康队长。番娥儿说:“把队里好棉花给我借上十斤!秋后结算叫九合把钱还上。”
两位领导人赶紧开库房,高高称上十斤好棉花,寻块被单子包上。写好借条,叫番娥儿签上名。
番娥儿回到窑里,细细缝了一床新棉被,用去好棉花六斤;细细给九合缝了一套新棉衣,用去好棉花四斤;又给九合细细缝了一条新单裤,细细缝了一件新布衫。
九合看见这,偷偷跑去窑后躲起来笑,欢喜成傻子一样,心里给天老爷烧高香!只是纳闷儿天老爷甚时间得闲睁开眼睛看见自己的,也没招呼一声,悄悄办了件好事情。
九合不知道该如何回报番娥儿,只是连连追问买布料花了多少钱?
“我把钱给你还上。”
番娥儿只是淡淡地笑笑:“两个人帮扶着过日子,分甚你的我的?以后再说吧。”
九合穿上新衣衫往人前一站,村里人眼珠子险些砸到脚面上。
夏收忙完没些日子,又要准备秋收了。董家河像小死水潭潭,村里人在里面忙忙碌碌活着,平平淡淡过着。
1972年大秋刚忙罢,一天夜里,饲养室草料窑里来了个汉子。康聚财老汉半夜里给牲口添草料,提盏马灯去草料窑抱草,看见了。那汉子三十七八岁年纪。老汉问:
“哪儿来的?”
“上头。”
“上头甚地方的人?”
“米脂。”
老汉将那汉子细细地看了一回,见那汉子带着全套的石匠家具,身边一条布袋袋敞着口,里面装着满满一布袋锅盔馍。
“到我们这搭儿做甚来啦?”
“揽工。”
“揽工?”
汉子告诉老汉,自己是个石匠,专为人家箍石窑。
“这村里能揽下活路不?”
老汉叹口气:“这年月能有几个箍起石窑的?我们算个好村子,也就将够吃哩。”
“这村里有个叫九合的吧?”汉子突然问。
“有哇,”老汉很惊奇:“你咋认得啦?”
“我们前世里有缘分哩。”汉子苦苦地笑笑回答。
“过了河,南山下那两眼小石窑就是他的家。”康老汉告诉汉子。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人都去了地里受苦。汉子从草料窑里走出来,背着包出了村。
汉子慢慢走到九合窑前,敲敲门。番娥儿开门出来,看到汉子,转身回窑端出一瓢水,汉子接过来慢慢喝了,和番娥儿说了几句话,就转身沿着原路慢慢回去了。
天傍黑,九合下工回到家,番娥儿做好了一锅油泼辣子面,在村里代销点买回两个咸鸡蛋,还破天荒打回半斤老白干酒。
饭也吃饱了,酒也喝美了,九合浑身畅快,看看坐在眼前的番娥儿,九合心里也痒得熬不住了,便拉上番娥儿叫早些睡。番娥儿婆姨一指头戳在九合脸面上,脸笑成了一朵花。
4
天大亮了,九合还在炕上梦黄粱。直到窑门上响起擂鼓声,九合才从梦里醒转回来,听到康队长在窑外骂:“九合,这都甚时辰啦还不出工?睡死了!”
一句话提醒了九合,这才觉出身边少了什么,赶紧伸手摸一摸,甚也没啦。
李支书、董主任、康队长,三位领导到齐了,几个人站在九合窑里发呆。
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啦?天老爷给请去啦?金刚背上跑啦?还是董主任脑袋灵光些:“快看看窑里少了甚?”
一句话提醒了康队长,两人赶紧检查,窑里检查起来倒不费事:看看粮食,荆条子编的囤里粮食满得冒出了囤口;腌酸菜的缸盖掀起瞅瞅,满满一缸酸菜散发着淡淡的甜酸味儿。
“九合,你的钱啦?”
“油纸包包裹着。”
“油纸包包啦?”
“瓷罐罐里装着。”
“瓷罐罐啦?”
“灶头地下埋着。”
董主任康队长两个人七只手八只脚地蹲在地下刨啊刨,刨了三遍,瓷罐罐终于刨出来。打开一看,油纸包包裹着老大一包钱,散发着霉酸味儿。油纸包包打开,董主任康队长两个坐在炕上数啊数,数了三遍,老大一堆钱,整整一百块。
李支书叹口气,背过手,低着头,走了。
董主任康队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怪毬事情!”董主任说。
“真是个怪事情!”康队长附和说。
九合明白了为甚番娥儿也没招呼一声,就悄悄走掉了——
“她家里一定出了大事情!她不告诉给我,怕连累我哩。出了甚大事情?……老人殁啦?娃娃病啦?……总之一定是出了大事情!这时候我要不出真力气帮她一把,我这个男人就白来这世上走了一回!”
可是九合并不清楚番娥儿家具体在哪里,他曾试探着问过两次,番娥儿不肯说,九合也没敢刨根问底。
“不怕!米脂——能有多大个地方?我就用两只脚丈量丈量哩!”
九合觉得自己活了这些年,第一次心里有了一个热火火的念想!这念想让他感到自己的苦胆鼓了,腰板直了,脚腕硬了。他梗梗脖子,迈起坚实步子,寻到支书李生贵:“帮我给公社粮站开上个介绍信!”
番娥儿走了。
九合也走了。
这件事情给董家河这个小死水潭潭里扔下一粒小石子。
康队长婆姨最高兴,她站在自家窑顶畔畔上手舞足蹈:“我那天老爷哇,你可睁开眼睛啦,你可让那骚货走了!我给你老人家烧高香、磕响头哇!”
其他人聚在一起纳闷儿,分析、研究。
康聚财老汉年纪大些,经过的事情多些,经过分析研究,老汉突然明白了!
“她跟上老汉走啦——她老汉没死!那天来的那石匠肯定是她老汉!这种事情这几年多啦。上头遭了年成,婆姨老汉相跟着跑下来,老汉去揽工,婆姨去讨吃。长的好些的婆姨就去寻上个拉帮套的。等年成好了,婆姨老汉再聚一搭相跟上回去,再过自己的光景哩。”
人们似乎也都明白了。
董主任康队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还是董主任脑袋灵光些,恍然大悟地给了自己脑袋一巴掌:
“咱们都是拉帮套的驴哇!”
我有个表姐,和我一起来陕北下乡,被招工到延安市里,和歌舞剧团一个人结了婚。我在延安市里也有了一个落脚点。
村里的手扶拖拉机、柴油发电机之类农机具坏了零配件,县城里买不到的,就打发人上市里去买。这差事落在我头上:可以给村里省几个住宿钱。
1972年的冬天冷得要命,可村里的手扶拖拉机还在跑运输,给村里挣几个零用钱。眼看快到年下了,运输跑得更忙了,急着把揽下的活干完好过年。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拖拉机的轴承坏了,县农机站上买不到。村领导急得不行,打发我到市里跑一趟。
到市里办完事,在表姐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大清早,我便赶着去汽车站买票,村里急等着用呢。
进了候车大厅,看见大厅北墙根下蹲着十几个破衣烂衫的人,旁边木制长椅上坐着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我好奇地看了一眼,发现蹲着的人里有个人很面熟,仔细一看是九合。我去售票口买了车票,慢慢蹭到公安坐的木制长椅跟前坐下,掏出一包“金丝猴”烟,抽出两支,给两位公安每人奉上一支。公安本不愿意搭理我,看在金丝猴的面上,脸上有了笑模样。我趁机搭讪:“公安大哥,你们这差事不赖,山南海北都逛逛。”
“不赖个毬哩。这大冷天,把人皮冻裂呢,谁愿出门?身不由己哇。”
“你们押送的是什么犯人?”
“都是些盲流。”
我一听只是盲流,心里有了底。
“这里边有我村里一个人。”我指了指九合,“我知道他不是盲流,他是去寻他婆姨呢。你们能不能把他放了?我给你们每人买上两包金丝猴。”
两位公安呵呵地笑了:“北京娃,你日鬼呀!你想打烂我两个的吃饭罐罐啊?……他不是盲流?抓他的时候他也说是寻婆姨,可他连婆姨住甚地方都不知道,还不是盲流?”
“你们这是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啊?要关多久?你们看他多可怜!我保证他就是想寻回他婆姨……”
两位公安看看我,点点头:“嗯,心眼还挺好。告诉你,我们把他送回你县里。你回去跟村里说一下,开上个介绍信,再写上个保证书,保证把他管上,别再出来当盲流。”
“谢谢公安大哥!谢谢!”我把金丝猴往一位公安手里一塞:“我能跟他说句话吗?”
“说去吧。可不敢耽搁久了。”
我向九合走去,看见他身上穿的是番娥儿给他做的棉衣裤。这才多长时间,已经破旧了,上面尽是柴草划下的口子。我想他肯定每天都得去钻柴草窑寻个睡觉的地方,他吃什么呀?我想应该劝劝他,忘了番娥儿吧,回去重新过日子。
我走到他面前,看到他更黑了,更瘦了,脸上的皮都干瘪了,可那双眼睛里却闪着灼灼的光芒,我分明从那光芒里看到了热火火的念想!我明白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只默默脱下大衣给他披在身上,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在他手里。
派去县里接九合的人回来了,却没有见到九合。
村里的三位领导问:“九合呢?”
“别提了,到半路上,他说要去崖湾湾里拉泡屎,我在道边抽烟等。等了半个时辰,不见他回来。我去崖湾湾里寻,看见他爬上山脊梁梁跑啦。”
三位领导半晌无语。最后李支书叹了一口气:“唉,九合疯魔了……”
“是疯魔了。”其他几人附合道。
春天了,南山崖畔上,山丹丹花开了一片又一片,红艳艳的让人看得心都痛死了。九合没有回来。
夏天了,村里有人想起九合来:“我家窑面面叫雨水打坏了……九合死到哪去了?”
秋天了,康队长想起九合来:“派谁去看庄稼呢?一夜蚊虫把人咬也咬死哩……九合这人死哪去了!”
冬天了,没有人再提九合了。
后来我回到了北京。离开董家河的时候,九合还没有回来。
很多年后的一天夜里,我梦见了九合。在梦里他的面目不清,但笑容灿烂。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眼角湿润了。
责任编辑:张天煜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