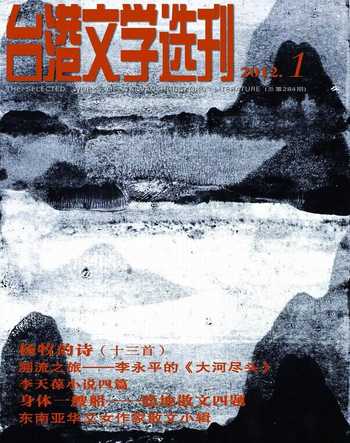岂殊蠧书虫,生死文字间
前几年住南港郊外,走路去研究室总不免看到小花圃里有几棵苏铁好像生病了,罩着一层冷淡的白粉。不久就听说那的确是一种虫害,很严重,有可能短期内将全台湾的苏铁戕贼殆尽。有时我站在人行道上远远观望,聊以凭悼,在暖冬的阳光下,其实并看不见凤尾叶上有虫的动静,只能信其有,而且知道有些更可能随风飘扬,为害远近栽植之其余。但我又知道,这件事也可以换一个方向思考;苏轼诗:“稻凉初吠蛤,柳老半书虫”,是植物本身抵抗不了自己的衰朽病变,才引起小虫长满啮食其叶成文字。古人喜欢这种带有教训意味的说法。我去翻书,大略认识了苏铁树上那虫雌雄各异的形状,但以我们迟暮的肉眼观之,非逼近端详,看到的也无非就是那棵与日俱衰的苏铁树上一层令人同情的白粉。
有一天下午我等绿灯过马路,才听见钟响,就看到墙里的小学生汹涌而出,和我前后左右走近那萎靡的苏铁。钟声犹未停止,多彩的小三角旗四处招展,走在前面的儿童当中有一个忽然驻足,退一步看地上,蹲下来专注观察着什么的样子,另外又有几个也随即加入,蹲下围成一圈,默不作声瞪着地上看,似乎带着无限的惊讶,那样研究着。而就在转瞬之间,我竟受到他们的感染,终于也好奇地弯腰睁大眼睛朝下看,不知道水泥砌的人行道上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如此吸引人,变成我们一圈老少目光聚焦的中心?我把白头继续靠近他们的圈子,闻到孩子们发梢颈项汗水的气味,在申时的老太阳下发散开来,看见底下隐晦细小紧贴地面的,正是一只误落混凝土结构的雌性苏铁白轮盾介壳虫。
我回忆这次经验,首先自以为欣喜的是在一特定的时空,幸能保有一份好奇,在适当顷刻,释放心血与神气,让那好奇自然流露,接受外在陌生、猜疑的挑战,并且于好奇不再的时候全身而退,将那际会找到一合宜的定义,为我所用,甚至,当时付出的血气,也因为单纯、专一几臻于透明,竟能在收放过程里丝毫无损,依然故我,还是属于我个人的。
所谓自然、单纯,或好奇,根据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理论,乃是一切创作的动力,生而有之,也随我们心智之成长展开,和宇宙山川的递嬗变化离合交接,似乎注定就要产生无穷的力量,直到肉身衰朽为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诗人自己有一天发现,他半生警觉最依恃的自然、他的单纯和好奇,忽忽焉已对他中止启迪,不但超越的神迹渺茫,甚至草木鸟兽的系统象征也为之溃散、陵夷,而他期期追求,尝试通过童年记忆以接近永恒之荣光的努力证明是空虚,失去了意义。我们无法想象,对华滋华斯而言,人之初生,即睡眠和遗忘的开始:婴儿呱呱堕地表示他正从有知多识的前生睡去,仅保留残存的记忆在童年阶段闪烁发光,与神异世界的性灵交接、互动,但也势必因今生岁月的推移和折损,因肉体成长,接受新知识,而逐渐将那些遗忘净尽,甚至失去孩提曾经拥有过、亲密的少许,我们惯习的“天真”,终于荡然无存。“和我们一同上升的灵魂,我们生命的大星,”华滋华斯说,“自有别处可让它赫戏沉沦。”大凡诗人感悟创作力之升沉与有无率属寻常,但华滋华斯叹息自责至于无所适从的时候,也还未到四十岁;奇怪的是他直觉或思维的天真竟提早结束、消灭,造成文学生命的危机,所以才想到试探以通过童年追忆去接近永恒的途径,在一首转折无穷的颂诗里深刻自剖,砉然响然,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再创前景,辞藻结构之不足,更在诗前专引另一首短作为提纲:“每当我抬头看见虹在天上,都为之心跳……”生命伊始的童年时代固然如此,现在成年还是一样,但愿老来也不至于改变,否则宁死而后已。诗人宣示,但愿一生的日子都由早年皈依自然的信望爱一体紧密结合,因为儿童乃原创成年之典型(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儿童的习性决定了成年的容止、行为,塑造自己的现在和未来,也影响外在环境,甚至于有意无意识间赋他人以矩矱分寸的思考。
我抬头朝那恹恹的苏铁多看一眼,知道介壳虫若是单独存在或不存在,虽然那么小,总是一个生命或一个死亡,并不是一片白粉。对这简单的发现我觉得满意。但我又想,我并不是靠近它而发现了它卑微的形状所以满意,显然还有些别的使我高兴,甚至为之怦然心动。在这样一个暖冬的午后,发现一具介壳虫的尸体和发现闲杂染色体或干细胞之类,对我说来,意义大概都一样,也许可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惟有这看见的过程,这些引导我去发现它的外在环境如此,活泼的知识诱因如此,多么直接、有力的动作,这些使我不期然触动久已迟钝的神经,拨醒我的好奇心;当儿童们迅速蹲下将眼光集中看地上的时候,我也自动参与,看那里有什么重要的活体(或死尸)将被我们发现,揭开宇宙间一伟大的奥秘。但我应该知道这势必是没有的事。无论如何,我应该完全了解,这整个情节如果有什么重要性,不外乎就是它证明我的好奇心还不曾完全消灭,而童年闪亮的记忆仍然发光,值得把我的直觉拿去和儿童的天真率性推挤,互相发明,如此而已。
甚至也可能不是我沉睡的感觉或想象神经被触动,或停滞的好奇被撩拨醒转了,而有可能就是我并不需要那环境、诱因,也即是说,或许那些儿童不期然、迅速的动作也属多余。我难道不能于沉静安详的脚步里自我调度,保留或扬弃一些即兴、偶发的思维?并且在适当时刻,当午后的太阳持续倾斜到一个位置,四垂仿佛无声,辄为人行道上一接近不存在的白点驻足,甚至蹲下来加以观察,看到前生或今世几已失去的记忆里,一似乎看过的意象,迢递而遥远,心智触觉于是重复反应,再一次震动,看到那介壳虫,看到我自己。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诗:
时常,那奇异的幻觉就翻过
脑海,使现在(当那闪光犹未消灭)
仿佛变成过去未知之复制,万种
感觉杂沓,灵魂迷乱,睡梦中
兀自责究不已;有人说我们前世
曾经活过,穿着迥异今生的血肉。
所有现在正进行的,过去都发生过,而且势必在未来重复。
这或许是说,假如不是小学生先后蹲下,付出如此巨大的注意力对人行道上一未知加以勘察,我就不可能自动止步去追究、探索,所以是儿童的行动启示我重拾好奇,或想象;即使我否认受了陌生人启示,甚至坚持这些都与儿童无关,反过来说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去日的自己,毕竟我不能不承认这前后的动作,乃是连贯而构成情节的,虽然我因为心虚,只愿妥协,将儿童权充这整个事件不可或缺的前台角色,被我看到,以引起我带着戏剧感的反应。然而,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考虑。我现在自然不会否认我是继儿童之后弯腰探头才看到地上的介壳虫,但我似乎又于困惑之余,怀疑当我趋近他们的圈子的时候,看见那领先蹲下的儿童原来正是我。
入冬以来,断断续续整理着这一本诗集,有时也在恍惚间以为是重复着过去已经做了的事,正确和不正确的执行、修正,但有些地方就由它去吧。从前如此,现在也应该就是如此。然而,冥冥中又感觉到心神有一种异乎平常的负担,可能是什么思维的累积,挥之不去,再三出现如荷马史诗里锲而不舍、勇敢的武士,被我这个最投入、一路尾随已经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末代读者所揶揄:但愿我们也像那频频跌撞的昆虫——兀自不挠的希腊苍蝇在玻璃光影里对着召集令鼓翼、盘旋。然后接下来想到的,就是屡次被我们援引,无限敏感、超越的谢玄晖,和制奇定法、创造力不穷的韩愈: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
2006年3月初于西雅图
(本文为杨牧诗集《介壳虫》的“后序”,题系编者所加)
·本辑编辑 游锦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