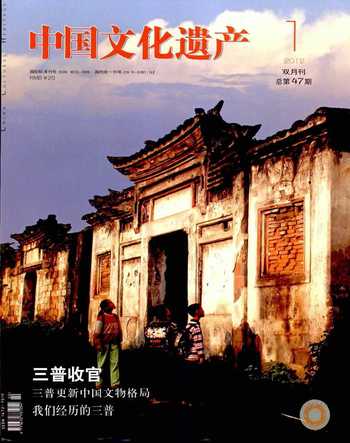北大上学记
罗琨

1958年,我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发放录取通知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参加中学组织的街道工厂劳动和街道扫盲工作,到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才剪断系联母校的脐带,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考取了第一志愿去北大读书,当然高兴,因为北大是我熟知的学校,上小学的时候,我家住在西老胡同,每天都要经过北大理学院的大门,穿过一个窄窄的胡同——“大学夹道”,才能到达我们的东高房小学。听说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的时候,特务就曾蹲守在附近监视学生,而我们六年级班主任杨春荫老师,则常在小酒馆和北大学生一起吃酒、聊天。那时父亲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我也曾随着父亲去过五四操场和北大红楼。
我还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907~1911年我的外祖父曾在那里任教务提调,专办学务;1909年我的祖父也从学部调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筹建农科。1919年正在北大德文系读书的一位舅舅因参加五四运动的游行示威,曾被关在午门内;1922年另一位舅舅则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研。而就在1958年前后,一位姑母家的表姐在北大读地质地理系,且为侯仁之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另一位姑母家的表兄正在北大读化学系,后来专攻尖端科学。我的同班同学也有不少考上北大、清华,所以我觉得自己考取北大是一件太平常的事了。
接到录取通知后,母亲送我一把梳子、一把雨伞,这是上学要用的东西,此外没有特别鼓励、叮咛的话,更没有像现在高考后的“庆祝”活动,当时我上有年迈的外祖父母、祖母,“空巢”病弱的姑母,下有四个年幼的妹妹弟弟,够他们忙的。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1957年姐姐考上北京农业大学,父母很高兴,告诉他农大的前身就是祖父罗振玉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农科。所以我想这时父母更多是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曾有过约言:“伏生有女传经史,莫羡邻家占梦熊”。
就这样,我怀着一颗平常心,一个人背着行李坐公交车去北大报到了。
一
北大五年的学习生活,节奏都是很快的,刚刚报到安置好,第二天就分配到图书馆善本室去抄资料,同去的还有两位历史班的同学,他们比我早一天报到,也早一天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踏进北大图书馆,第一次知道进善本室是不能用钢笔的。
不久,就开始报名分专业,那正是“考古专门化”改为“考古专业”的第一年,我们58级在大一就分专业,我毫不犹疑地立即报了名。因为我们的时代重理轻文,在我读高中时,北大地质地理系读书的那位表姐,多次来探望舅父舅母,谈起学习生活,尤其是野外实习,我十分羡慕,心向往之。但我不可能学地质,因为自幼体质差,初中得了肺结核,高中还免修体育,学地质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转向了考古。
我从小喜欢乱翻书报,高中时知道了苏联发掘了花拉子模城,又读了一本苏联小说《成吉思汗》,讲到花拉子模城的毁灭,开始对田野考古及通过考古,发掘、复原被岁月淹没历史的工作很着迷。回首往事,我常想就像《成吉思汗》里赢弱的小图干一样,他的影子被缝到了托钵僧的斗篷上,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我也是从那时起,就把自己的影子和考古学缝到一起了。而且后来因为身体不好,系总支书记吴为能找我谈话,希望我转到历史专业,但我还是毫不犹疑地谢绝了组织的好意,坚持留在考古专业。
学考古父母当然是支持的。不过高考、选专业填志愿,都是我们自己做主,甚至没有和父母、老师商量,当时高考填六个志愿,我没有填满,好像只填了四个,包括北大历史系和图书馆学系。现在想来,父母确实希望我们姊妹能继承家学,但是继承家学不一定要局限于祖父和父亲专长的学问,选择有互补性的专业会更为有利,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即对所选事业的热爱,才能有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在攀登中不畏艰辛。
我在北大正是1958~1963年,正值反右过后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小高潮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当时北大还是重视教学的,这五年的记忆就是劳动、运动,抓教学质量。
劳动,我们参加过首钢的大炼鋼铁;农村的抢种抢收,北大的建校劳动,我们参加过修建北大的石砌围墙,听说吕遵谔先生是砌虎皮墙的高手,而虎皮石是我们肩挑、手搬,穿过半个校园运去的;参加过“一百号工地”(北大分校)迁坟、修路……劳动的高潮延续到经济困难时期,还遭遇食堂管理员贪污,生活条件可想而知。在校外劳动,有时下工要摘野菜带回食堂,从而认识了马齿苋等一些野菜。还有一次劳动,每日午餐都是馒头、熬大葱根(葱须)、蒸锅水(代替汤),我一直不解有这么多葱根,葱都到哪里去了。不过在当时,和市民比,大学生的粮食定量还比较高,和广大农村的同龄人相比,我们更属于“幸运儿”。
运动,主要是各种政治学习、批判,常常开会到很晚。搞运动更要学习、讨论、准备发言,生活节奏很快。
每当一个运动高潮过去,抓教学质量就被提上日程,除了在文史楼和各个教室楼间奔波上课,就是奔波找自习的场所,2 7斋寝室两张双层床,一个小方四屉桌把房间装得满满的,只能留一人自习,多数人都去找阅览室。记得冬天的清晨,六点多时天还没有大亮,大饭厅外的路上,就会有不少影影绰绰的移动的人影,其中不乏打一大碗玉米面粥,边走边吃,奔向阅览室的学生,晚了文史楼阅览室就没有座位了。一二节有课,就不去阅览室,27斋后面、五四操场旁,一个小土山的桑树下是我读外语的地方,当时北大没有那么多人,五四操场也鲜见有人活动。后来还发现了绕过五四操场,有一个理科用的阅览室,宽敞、舒适,而且人少,晚上我常去那里自习。
1960年代前后北大的生活条件,当然不能和后来相比下乡、下厂、各种劳动等,虽然繁重,为过去所不曾经历,也由此病过几场,但使我了解了象牙塔以外的生活。磨砺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其它活动多了,学习时间少了,使我懂得了珍惜,而学习考古专业课,就像是追随托钵僧去探索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对我有无穷的吸引力。
燕园的生活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参加“大搞科研”,好像是1960年寒假,学校再度掀起大搞科研,班上大部分同学参加编写《北京史》(或者叫《北京文物志》?),首先是下去调查,回来编写、讨论提纲,重点在于如何“突出红线”,记得张永山讲他去焦庄户调查地道和抗日战争的地道战。我作为刚修过石器时代的考古班的学生,被分配到世界史教研室,参加编写世界史讲义的课题。在批判“科研大跃进”的过程中,曾谈到“由低年级为高年级写讲义,不啻为笑话”,确实,科研工作不适宜采取“大跃进”的形式,作为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在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班子里也起不了作用,但在我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寝室没有暖气,在27斋,清晨醒来总会不由自主地摸摸床边的暖气管,却总是冰凉的;打回一壶开水放在地上,待到拿起用水时,总有壶底沾上的水已冻结在地上的感觉。38斋也是一样,听说一些男同学要戴着帽子睡觉……但迈进世界史教研室就像进入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齐思和先生十分风趣又平易近人,一些青年教师就像孩子一样围绕在他们周围,记得一次一位青年教师刚刚起身想出去一下,抬头一望,忽然低语“齐先生要讲故事了”,赶快又坐下。而我,总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饶有兴趣地观察并倾听他们的一切。当然,还有工作,在我,主要是学习,我读了当时出版不久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第一卷后,带着问题找到了严文明先生,先生给我开了一个书单,告诉我了解这些问题要看哪些书,第一次给我指出科研工作的门径。
大学生活也有很多有趣的事,同班有十位女同学,大学五年室友都是同专业的,除了外出实习、劳动,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我下铺几乎是住了五年。同室三年多的是57级毕业分到考古所的曹延尊、刘一曼。初进北大就同室,前后住了一年多的是李东琬、许爱仙。57级毕业以后,我们又和59级的林秀贞住于一室。这些室友们都很有事业心,很用功,和他们相处都很融洽,他们至今大都不枉一生,取得很多成果。
记得到北大报到后的第一个周末,同为家在北京的我和李东琬都决定不回家,因为萦绕心间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十八岁/对于人生/只有一次/年轻人/一定能代表所有的孩子/向年长一代战斗者说/我们要改变大地的生活”。十八岁,我们成年了,该独立了,但这第一次的离家难免思家心切、无法成眠。夜晚,我们对坐在桌前,望着外面大雨滂沱,冲刷着寝室的窗户,一只大壁虎紧紧扒在窗外玻璃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观察到它的肚皮和四肢。在那些日子,也曾抓过碧绿的很大的尖头蚱蜢,栓在墨水瓶上,作为“宠物”,伴我们读书。
记得分专业不久,57级曹延尊、刘一曼刚从周口店发掘工地回来,带回来发现的鹿牙和鬣狗粪化石,得知我们是考古班的新同学,在上交系里之前,特地取出让我们开开眼。我第一次面对他们带回的“圣物”,轻轻抚摸这些远古世界的见证。转眼四年过去,五七级就要毕业了,1962年是他们在校的最后一个新年,除夕之夜,曹廷尊、刘一曼、樊锦诗和我在二十七斋的寝室里畅谈毕业后的工作,憧憬未来,直到午夜临近,才匆匆跑到大饭厅参加聚会,元旦钟声响了,四双手紧紧的握在一起,相约十年后再会。在我们年轻的心中,十年是十分漫长的,我们能做很多的事,会有很多体验可谈。然而直到2005年中秋,才践行了重聚约言,这本应是一次愉快的聚首,四十年,为了青年时代的理想我们都尽了力,并且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四十年,我们都经历了很多苦辣酸甜,但是只有三个人走过来了,曹延尊英年早逝,想起他的未竟之业和当时尚不解丧母之痛的幼子,在莫高窟前、在中秋之夜清冷的月光下,禁不住无语凝噎。
二
我们五八级分专业早,参加田野考古较多,尤其是“认识实习”为其他各届考古班所不设,在田野工作中,我们的实习包括了从测量、开方、挖土到用小铲清理发掘、绘图、刷陶片、拼合、简单地修补、画图、整理,对学生是很好的锻炼。
1959年认识实习,参加陕西华县发掘,先在遗址区,所在探方方长是56级的劳伯敏,记得挖的第一个灰坑,靠坑壁有一个坚硬的二层台;后来发掘一座地穴式的房子,中间一个柱洞,李仰松先生两次来看我的房子,第一次告诉我,把柱洞清理出来,第二次检查清理结果。这是一座用一根柱子撑起遮挡风雨棚顶的椭圆形房子,坚硬平整的居住面上,留下一个陶灶,一堆螺蛳壳,房子的主人是怎样的人,当陶灶点燃的时候,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曾引起我长久的遐想。
后来我们班分配遗址区和墓葬区的两组调换工作地点,以便对两种遗迹的发掘都有感性认识。我则被分配到修补室,帮助工作并学习修补技术,我的师傅是考古队请来的一位当地教师——紫娃,手很巧,在这里我看到、学到不少修补、复原的技巧。
在华县,除了参加田野考古,当时的苏联留学生刘克甫给我们讲授摩尔根《古代社会》。课堂在室外,他让我们“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半圆,就开课了。纠缠起起拗口的亲属称谓,别有一番乐趣。
发掘工作结束,我们参加了麦收。华县生活使我们见识到八百里秦川的富庶,麦收时生产队提供的午餐是半斤一个的粘谷面窝头,也是一种难得的美味。麦收后去华阴参观了考古所的一个发掘点,又背着从华县带的馒头登华山,在山上据说是慈禧太后避难住过的地方住了一夜。下山去西安参观。由于数日连续紧张、劳累,到了西安半坡博物馆我就发起了高烧,曾在西安工作过的同学张岱海陪我去了医院,直到数日后,同学们参观结束,才能起床和他们一起回京。虽然由于生病,错过参观西安雁塔、碑林的机会,但西安之行使我第一次知道唐长安规模宏大,后世帝都如北京故宫无法与之相比。
1960年,怀柔发掘是抢救性质的发掘,于2月28日开工,领队是北京文物工作队的郭仁先生,我的方长是56级的杨育彬。我们住在怀柔饭店,当时怀柔县城只有两条街,饭店用水比较困难,吃饭时只能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简单冲冲,难免把残留在手上的的骨头渣、棺材灰和手上的馒头一起吃下。
這是我第一次发掘汉墓,很开眼界,第一次知道了用探铲可以准确找到墓葬四界。这批墓葬保存不错,有漆器,可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保存。这次发掘虽然天寒地冻,条件也比较差,但我的方长喜欢唱歌,而且唱得很好,一面以半蹲半跪的姿势剔骨架,一面陶醉于墓坑中的歌声,真是一种难忘的经历。这次发掘结束,我们还在当地大庙里办了一个展览。
1961年,雪山发掘是正式的生产实习。以前发掘都有高年级带领,这次是独立工作,邹衡先生要求严格,记得有一位同学用大铲“敛平”技巧掌握得不够好,邹先生看到,把大家召集起来,让他把探方地面敛平,然后指出他的错误,再敛平,直到正确了才让大家解散。还有的同学,在敛平耕土层时发现底部拖拉机留下的痕迹,以为是遗迹不敢往下做了,邹先生也大声、详细地指出其错误。这样虽然少数同学自尊心有点受伤,但多数同学受到教益,所以大家都很尊重先生。当然,先生不仅严厉,也很关心学生的方方面面,当时我和张永山在一个方,曾发现一座圆形房子,地坪坚硬,还有一灶坑,该次发掘房子少见,先生看见很高兴,立即给发掘者和房子合了一个影。后来我看到先生在《手铲释天书》中讲,主持洛阳王湾发掘,工作进展顺利,不仅“对成仰韶、龙山完整陶器共达500余件”,还有
“6位男女同学,居然对成了终生伴侣”,从而感到“有说不出的欣喜”,我才明白那也是先生对我们未来的美好祝愿。
“民以食为天”,“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雪山发掘正是困难时期,当地村民(包括我们请的民工)基本是以红薯充饥。考古队师生虽然都有基本的粮食定量,但副食糖、油,还有动物蛋白和脂肪都很匮乏,田野工作是体力劳动,老師们除了指导我们发掘,还要到周围地区踏勘、调查,更是辛苦。吃饭问题有时不能不受到关注,记得一次我们都吃完了饭,邹先生才调查回来,当他从厨房出来,一手拿着调查找到的鬲足,一手拿着馒头,满脸充溢着笑意,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位有事业心的学者最幸福的时刻。
1962年,毕业前的专题实习我参加的是山西组,共五人,包括张永山、曹定云、徐治亚、祁惠芬和我,指导老师是苏秉琦先生。在山西侯马,具体指导的是工作站王克林先生(北大考古专业52级),由王先生带我们踏勘、考察周边遗址,介绍要我们整理的遗存出土情况等等。分工我和徐治亚整理一批小墓,首先是绘制全部随葬陶器图,然后编写发掘报告。张永山整理的是铜器墓,还制作了一些拓片。
苏秉琦先生是在我们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时才去的,检查我们的器物排队,型式划分是否得当等。记得是张永山去潼关接先生过黄河,再陪同到侯马。当时在侯马有不少先生的学生在那里工作、实习,先生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学生们纷纷汇报工作、请教问题,除了畅谈学问外,先生还请大家吃了羊汤。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真是一种难忘的美味,有人笑谈,吃得都快要“张口可见”了。
三
回首此生专业的选择和学生时代,我确实是很幸运的,第一件幸事就是我出生在一个父母非常明智的家庭,他们很重视身教,而且不仅爱子女,更懂得如何爱、如何教育,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子女开创自己的道路。记得六七岁时,闲谈中母亲问我们姊妹俩喜欢什么(后来读了《论语·公冶长》“子曰‘盍各言尔志”,才知道这是一种教育方式),姐姐说了以后,我脱口而出“我也是”,母亲马上讲“不要拾人牙慧”,虽然当时不免有些委屈,这却使我受用一生。1984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商史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殷墟卜辞中的高祖和商人的传说时代》,得到胡厚宣先生的鼓励,说此文“发前人所未发”;也曾有编辑来函约稿,认为我关于先秦史、甲骨文研究的一些论文“给我国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觉和成果”,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能有一点成绩,只不过是记住了母亲的话:“不要拾人牙慧”。
更为幸运的是我读北大是在1958~1963年间,在这里我们受到磨砺,懂得了珍惜,更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在校期间虽然运动多、劳动多,读书的时间打了折扣,但同时很注意抓教学,大学教育的专业训练基本没有缺失,尤其是系领导说,“都是劳动,考古班与其上工厂农村,不如去考古工地”,于是我们获得更多田野考古实践的机会。这段经历,对于毕业后转入史学领域的工作者尤为珍贵。记得1980年代或稍晚,一次学术讨论会中间,参观二里头遗址,当时对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以及夏商分界断在哪两期之间,有多种看法,争论难分难解。在邹衡先生旁边看陶片的一位历史所先秦室主任说:如果能让我把一个灰坑从头做到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旁提醒他说,各种不同意见的论者,可都是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抬头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订正我说:“岂止是多年”。我想学历史的若有多一点的田野工作实践和见识,就不会有这样简单地看问题,历史学和考古学者也能够更好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