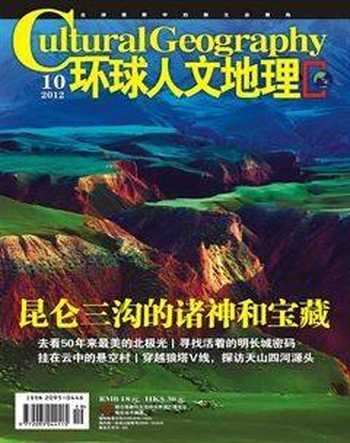古徽村唐模的风水与“贾儒”典范
黑陶
徽州人极其重视水的处理。水寓财,如果一村之水,不管不顾,让它径自流出村外,那么此村的财气、福气就会外泄一空。为了凝聚旺族之气,唐模村人对于檀干溪的送别,可谓空前隆重,分别以树、桥、亭、坊、园作为送水的仪仗……唐模人读书和经商一样出色,这个小村竟出过3位翰林,成为它最大的骄傲。
在黄山市徽州区的古徽村唐模,从那陈列着十八方名人碑刻的临水镜亭中,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朱熹、文征明、董其昌、八大山人等名人的字影……顽强地渗逸出来,仿佛暗布于宣纸一般清白的空气中。
深冬的天色向晚,村中行人寥落。我投宿的村民吴森洪家已亮起灯火,暖意融融。主人妻已烧好了晚饭,煨山芋和蒸咸肉热气腾腾,农家土菜,风味独特。席上的酒是此村几乎家家自酿的糯米酒“翰林红”。不断倾倒在碗里的鲜艳酒液,加上热气弥漫的菜,以及关于历史或现实的散漫话题,尽管窗外北风吹动,屋内的晚餐却是温暖的,美好的。
完整而缜密的风水体系
这个唐代古村唐模,在我见过的徽州村落中,是存有完整而缜密的风水体系的典范。白墙黑瓦的民居中间,一株至今年年枝繁叶茂,却已1370多岁的古银杏树,告诉我这座村落的古老。
在村西,依然可见此村先人将上游的“筠溪”和“上川”二溪挖渠筑堤,汇成的檀干大溪——将众水归合,象征着财富的汇集。蜿蜒一公里的檀干溪穿村而过,村中民居夹溪而建,溪水两岸分布着近百幢徽派古建筑。溪水的驳岸用红色岩石砌成,路面则用青色的茶源石铺就。为方便行走,檀干溪上共建有10座不同风貌的石桥:蜈蚣桥、五福桥、灵官桥、义合桥、高阳桥、四季桥、垂胜桥、戏坦桥、三石桥、石头桥,而以位于村中心高阳桥为主桥。在高阳桥近侧、檀干溪北岸,还留有避雨长廊,其长40余米,廊下临溪侧设有“美人靠”,供往来行人歇息。由此,这座古村的总体形态,透露出了江浙一带水街的风韵。
唐模最为经典的部分,在檀干溪的出村处,也即它的“水口”景观。
徽州人极其重视水的处理。水寓财,如果一村之水,不管不顾,让它径自流出村外,那么此村的财气、福气就会外泄一空。为了凝聚旺族之气,唐模村人对于檀干溪的送别,可谓空前隆重,分别以树、桥、亭、坊、园作为送水的仪仗。树,是至今已有400岁的大樟树;桥,是蜈蚣桥,据村中老人介绍,桥墩下还埋有铁制蜈蚣,用它盘踞水口,以镇风水;亭,是始建于明代的沙堤亭;坊,是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同胞翰林坊”;园,则是唐模水口的精华所在——建于清初,模拟西湖景致的檀干园。如此隆重的送别之下,村民们的心中便得到安慰:檀干溪的自然之水流出村去,而溪水所承载的吉兆祥瑞,则全部被留了下来。
而从更为广阔的范围来看,唐模也的确是福地:其环村皆山,风调雨顺,四季分明。
“贾儒结合”的典范
“贾儒结合”是徽州的文化特征。我所探访的唐模,又是这一文化特征的缩影,极具代表性。
先说“贾”。
徽州盛产商人,这是它的自然地理环境促成的。客观上,徽州地区是“八山半水半分田,还有一分是庄园”,山多田少,出外经商于是成为“第一等生业”。有统计显示,明清时代,徽州的成年男子中,外出经商者占到七成。徽商活动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素有“无徽不成镇”之说。而周边的杭州、苏州、扬州、兰溪、金华、芜湖、安庆、南昌等城市,是其主要经商目的地。徽商经营行业主要是茶叶、木材、盐和典当,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
现有1400多人口的唐模,历史上出过不少声名显赫的大贾,其中以建造檀干园的清初巨商许以诚为代表。相传当年他在全国开有36家典当铺,非常富裕。他70多岁的老母亲一心向往“人间天堂”杭州西湖,但苦于山水阻隔、路途遥远,加上年老体弱,不能前往。许以诚为遂老母心愿,不惜巨资,挖湖筑堤、修亭造桥,模拟杭州西湖景致造出了“小西湖”檀干园,供母亲游览、养老。
再说“儒”。
唐模人读书和经商一样出色,这个“地僻历俱忘”的小村竟出过3位翰林,成为它最大的骄傲。
村落水口的“同胞翰林坊”,就是康熙皇帝为表彰唐模村的两位同胞兄弟皆入翰林院而恩准建造的。这兄弟俩是许氏家族的许承宣和许承家,他们分别于康熙十五年和康熙二十四年考中进士,被康熙帝钦点为翰林。
唐模村的第三位翰林,是近代著名诗人许承尧。许承尧(1874—1946)是清代最后一科进士,曾官至翰林院编修。作为“慈祥热情,蓄着长须的长者”,许承尧旧学深厚,却思想开放——他倡导男女同校,是徽州师范的创办者。他所著三十一卷《歙事闲谭》,已成为现代徽学研究中的重要典籍。他的故居,被他自号为“眠琴别圃”、“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原来包括住宅、大厅、书房和一个大花园,但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现在只能看到一部分。站在绿苔暗生的狭窄天井内,白色的天光像巨剑一样射下来。我爬到蒙尘已厚的昏暗的楼上,目睹众多散乱堆放、斑驳漫漶的贺寿牌匾,一种人事的沧桑之感便油然而生。
古村的“文心”和“文化卫士”
拜访许士曙和许海生两位老人,让我感受到了此地的千年气脉至今仍在延续。
81岁的许士曙先生与我同饮,他胃口尚好,但已自觉不多喝酒。灯光和入肚的少许“翰林红”酒,还是使他的脸色稍显酡红。他散漫缓语,讲唐模的过去,讲古时徽州充当邮递员角色的“信客”,讲京剧,讲当年徽杭公路的修建……从他断续的讲述中,我也得知他于1946年毕业于徽州师范,一生从事教育,退休后主要是“看看文史书,写写毛笔字”。士曙先生是现在整个唐模的“文心”,因为在我拜访过的唐模人家里,几乎都挂着“檀干士曙”的书法手迹。
许海生老人则是黄埔十六期学员,抗战期间任国军机枪排排长,最高做到营长;1949年后,因为历史问题,老人回到唐模后被生产队安排养猪。老人对唐模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文革”期间保护了镜亭中那十八方珍贵的名人碑刻。这位瘦矮的老人戴着帽子,脸上布满了黑褐的斑点,但耳聪目明。对于“文革”的那段往事,他记忆犹新。
“当时我在镜亭养猪,红卫兵说要来破四旧,要砸镜亭里的石碑。我知道这些刻有苏东坡、黄庭坚的字的石碑不是四旧,而是文物,就连夜用猪圈里的猪粪和些黄泥,把石碑都涂了起来。第二天红卫兵来了以后,看到石碑上全是烂糊糊的粪泥,嫌臭,就全走了。”他屋里的墙上,我注意到有许士曙先生书赠老人的一个小条幅:“忠厚老者,文化卫士”。
喝了“翰林红”酒后,我便在主人吴森洪家一夜好睡。吴家就在檀干溪上的高阳桥畔。清晨,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醒来,穿衣后出外走走,见家家院前收获的山芋和萝卜堆上,都已积了白霜;檀干溪旁的“美人靠”上,散坐有三三两两的端碗吃早饭者。水街是湿漉漉的。晨岚,溪气,以及从桥头馒头店弥漫出来的袅袅热雾中,衣着鲜艳的孩子走在上学路上——一种恬静、悠久的生机,在这座古徽村中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