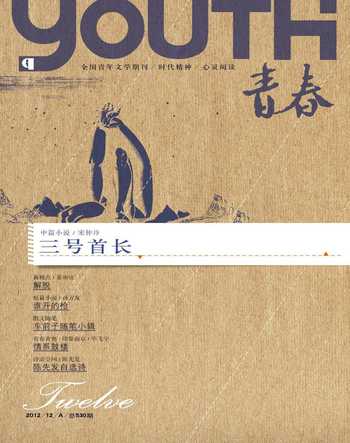我的村学乡学
张晶
说到学历,几乎是我一辈子的痛。后来尽管学历持续提高了几个层次,仍感到有种压力。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的世界里,学习便成了一辈子的追求,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读书,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关于这一点,还得要从头说起。
一
我的早期求学过程,虽没有多少传奇,却有着独特的经历。
我的老家在苏北沛县东北部,更具体地说,是在山东与江苏交界的微山湖西畔。通往微山湖的姚桥河,从村北缓缓流过。据家谱记载,我们张姓家族,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从山东寿光迁徙到现在的安国镇张庄村。虽然沛县在汉时就得到过高祖刘邦的“恩典”,而安国又是历史上著名的“五里三诸侯”原产地,甚至安国还因纪念汉朝开国元勋王陵而修“安国寺”得名,然历史的悠久,并未能改变那儿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百姓生活的疾苦,加之黄河屡屡泛滥,致使家乡洪灾频发, 即便依傍著名的微山湖与精巧的姚桥河,也改变不了那片土地上时常出现的旱灾现象。
1961年中秋之后,我来到这个世界并成为父母掌上的第五个“明珠”。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我的降临无疑有点“不识时务”。好在经过父母亲与兄长的努力,还能确保一家人不至于饿死。我没有像兄长们那样拖着讨饭棍去“河东”(即“京杭大运河”之东,属山东)讨饭糊口,也没有像村里的不少人家一样逃到“关外”谋生。不仅如此,九岁那年,我还有幸进了小学。说来有点不可思议,从小学到高中,我在班上的年龄几乎都是最小的。记得小学毕业时,我们班上有位叫刘昭银的同学便结婚了。那时的昭银,大概十八岁,还不到法定结婚的年龄。可这样的事,在偏僻的农村,有谁去管呢。他的婚事是其父亲决定的,我们当时只把昭银结婚当作一桩好玩的事。据说现在昭银的孙子都快结婚了。没想到仅三十年光景,他整整比我多了一代人。
当时的小学在村子东头,我家住在村西头,距学校四、五百米。学校面积不大,三、四亩地的样子,由一条小路将其一分为二:北侧是教学区,南侧是活动区。在活动区里,有两个破损得几乎遥遥欲坠的篮球架。教学区有三排,所有的教室都是土房子,和当时的民房一样,不仅低矮,而且光线昏暗,只是在临门的那面墙上,有扇不过两平方米的窗户。至于课桌,是用土坯加上一块木板组成。所谓学习(大人们叫“耕读”),也不大正规:一个班里有好几个年级的学生,第一、二排坐的是一年级,第三、四排坐的是二年级,第五排坐的是三年级。这样的格局,给老师教课带来了很大困难,他们只好先教一年级,让其它二个年级自习;当教二年级时,再让另外两个年级自习……以此类推。授课难,管理也难。农村孩子,学几个字就行了,没什么远大志向,加上又是“文革”期间,在学习问题上,家长、学生都任其自然,所以学生几乎没什么负担。但教我们的老师是严厉的,现在看来,那时的老师完全是出于良好的职业修养和道德要求。我的第一个老师叫张兆举,年龄和我父亲相仿,管理学生时,极像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老私塾先生,对不好好学习的孩子,总要施以惩戒:用笤帚把子狠狠地打屁股,有时也会用木条尺子(像戒尺)打手。班上几个调皮的学生,经常受到这样的“特殊教育”。我因胆小听话,学习成绩好,没有受到那样的“待遇”。不仅如此,一年级刚结束,我就直接升到三年级。和我一同跨过二年级的还有另外三个同学。
记得五年级时,教语文的张兴沛老师希望我们每周多写一、两篇作文交他批改。当时大概有四、五个人按照张老师的要求做了,我是其中之一。一学期下来,果然有效,我的作文常常成为课堂上的范文。有一次,我的文章还上了“公社”的活页文选,让我激动了好一阵。
想起五年级,现在印象最深的是做好事。那时,我家经济条件虽不好,但在当时农村还是处于中游偏上。我大哥在山东当兵,大姐在外面工作,我们家被当地称为“来元户”(指有人在外工作能寄钱回家)。因此,这样的条件令村上人羡慕不已。我向父母要钱,和别的同学(像周楼村的“解放”、本村的张兴华等)把从家长要来的钱凑在一起,每次凑够了几元,就到小店里为班上更加困难的学生买些铅笔、纸张、橡皮之类的学习用品,然后用纸包好,趁老师不在之际,悄悄放到班主任桌上。这样的“无名英雄”,我做过一止一次,以至每当想起,心里总会偷着乐儿。
二
1974年小学毕业后,我面临着上中学。按理,我该到湖西中学去上。可后来,我被安排到一个新建的孙井中学读初中。
湖西中学与孙井中学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县里为我们临近的几个公社创办的完中,而后者则是当年公社为几个村所办的一所中学,因为仓促上马,孙井中学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后来之所以创办,是因为赶上了初中扩充之年,至于什么原因要扩充,我猜想可能是生育高峰引起的入学难,所以几个村子就合办了一所初中。正好这样的学校,教育质量和水平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当时学农机、农技之外,我们也上课,但一个老师可以教好几门课程,这可苦了学生。记得每当上地理课,吴永超老师总会手拿一只篮球不停地比划,告诉学生那几条线分别代表着赤道、回归线、极圈以及经线,然后又按照地球旋转的规律不停转动着手中的篮球。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只知道吴老师的表演极其别扭:歪着个身子,两个膀子拧成一个交叉状。其实,当时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够看到一只真正的地球仪,可这一愿望,直到高中毕业都未能实现。
湖西中学是我的一个梦。在此之前,不仅村上的适龄孩子都去那儿读书了,而且我二哥和二姐也在那所中学读过书,他们常常会用充满自豪的语气谈论着那儿的数学老师、化学老师、语文老师等,使我心中充满了渴望。无奈那时学农、学工成为一个重要课程,又逢“文革”高峰期,“批斗”已成家常便饭,所以在孙井中学的两年时间,细细回想起来,真的想不出究竟学到了什么。好在后来的几次复读,总算让我机会跨进了湖西中学。
1976年,社会上正流行“推荐入学”的风潮。既是推荐,当然就不需要考试。按理,我家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然而,大队没有推荐我上高中,理由是,我二姐已在两年前被推荐上了高中,所以要把指标让给别人。这样,我就被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因为实在想上学,我只好央求父亲托人想办法。尽管那时我已习惯了劳动,可并不情愿一辈子在农村劳动下去。至于父亲是怎样不顾脸面四处求人的,他一直没有告诉过我。好在他的奔波总算有了结果:因为远门堂嫂的哥哥赵呈义在朱寨中学任校长,我终于进了朱寨中学。
那时刚刚闹过唐山大地震,我作为唯一一个住校的学生,只好和住校的二十几位老师一起住在一个用帆布搭起的很大防震棚里。一开始,我在老师的食堂里搭伙,吃饭采用“记帐”的办法:饭毕,自己到贴在墙上的纸上记帐,吃多少记多少,我的名字列在最后。至于伙食,平时一般以素菜为主,其间吃过一次红烧鱼。第一个月下来,我记得伙食费好像是四、五元。即使是这样的开支,家里也有点难以承受。到了第二个月,我只好带些大米到老师食堂去蒸饭,每周回家时,再带上一塑料袋皮蓝腌制的小菜。偶尔,也会在老师食堂里买道荤菜。记得当时是初秋,气温还比较高,包在塑料袋里的咸菜没过几天就霉烂了,粘糊糊的。按理说,那是不能再吃了,可不吃又怎么办?所以勉强糊到周六下午,便急急忙忙地朝十公里外的家赶去。毕竟那时才十五岁,步行两个小时还不懂得累。在家停留半天时间,周日下午就又赶往学校。
虽然在朱寨中学只待了两三个月时间,可那所学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士珍老师的数学教学全县有名;化学与物理老师每当要做实验,都会让我做助手。据说,有几年朱寨的高中毕业生中,考上清华、北大的都有。可我当时因一个人住校,又一个人来回,多少有些孤独,所以后来便动起了转校的念头。
我想去八堡菓林中学,因为那儿有我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在读书,名叫张建华。真是天赐良机,对方学校正好也有一个姓梅的同学想转到朱寨中学,于是我们很快达成了互换协议。
八堡菓林中学的原址坐落于原八堡菓林场西北角的一片荒野里,转到这里后,我才发现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多么荒唐。这里地处黄河故道边缘,每到冬季,飞扬的黄土铺天盖地,人若走在路上,满脸满嘴满头满身都是黄土,根本看不清方向。那种景象,让人见了不免有些恐惧。
因为这里离家有九公里,平时都得住校,一般周六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可有一回,我和同班同学张建华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周日下午回校,只好周一一大早往学校赶。当时家里没有闹钟、手表之类的“奢侈品”,现在已回忆不起是什么时辰起床的,只记得我们一边步行,一边打着瞌睡。后来实在太困,我们就决定在一座水泥桥的桥墩上眯一会儿。没想到很快就睡着了。其实所谓“睡着”,顶多不过半个钟头,因为醒来时,天还是黑的。于是我们继续赶路,终于在上午第一节课前赶到了学校。
转到八堡菓林中学后,一开始因没地方居住,学校就把我安排到一位来自县城的孟老师所住的防震棚里,和张建华一同居住。孟老师住的是木板床,而我和张建华睡在地铺上。有一次,我和张建华回到防震棚,打开一个歪歪扭扭的小门后,借着微弱的夕阳光线,竟无意中发现在地铺靠近门口的地方,居然长出了一簇簇“麦芽子”(像蘑菇模样的一种真菌,当地俗称“狗尿台”)。为此,我们好奇了好半天。还有一次,可能是晚上没地方可住,我和张建华索性睡到了草堆里了。记得当时教室走廊里,堆满了附近农民预备冬天喂羊的饲料。我们等到晚自习结束,就把被子抱到了走廊的草堆上。草堆是随意堆放的,并不符合作为地铺大体平整的标准。我们俩简单整理了一下,就把被子铺上。我倒头便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听到一阵哭哭啼啼的声音。迷迷糊糊中,我知道是张建华在哭,而此时被窝里,早已充满了树叶、杂草。我问他为什么要哭?他抽泣道,太苦了,你看看,这咋睡觉?因为这件事,他很快转到了他舅舅担任校长的那所朱寨中学。
当时,学校虽开设了高中生应学习的全部课程,可师资力量明显不足。数学老师黄绍乾兼任化学课,班主任孟老师兼任语文课。孟老师大约四十七八岁,虽是班主任,可平时对班级管理不多,基本上依靠班干部来管理。其实,班干部也管不了什么。由于当时还存在着前些年社会上所流行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班上四十多个学生没有几个人对学习产生兴趣。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学习风气多少有些好转,然后这样的好转也是微弱的。尤其是对于理科类课程的学习,学生基础太差,大家普遍不感兴趣,当然也包括我。这样一来,老师的教学常常进行不下去。印象最深的是教数学的黄绍乾老师,他的课虽然教得好,然大多数学生都不愿认真去听。有个名叫谢厚军的男同学,经常会在黄老师的课上站起来讲些让同学哄堂大笑的话。黄老师本是个暴脾气,但在课堂里,他只是说:“真是老公公背儿媳妇上山,哪里黑哪里住。”当时我还不大理解他的话的含义,现在想来,这多少表现了他对学生不想学习的一种无奈。有段时间,我曾经住在黄老师与另外一个老师的宿舍里,知道他的为人,他常常会心疼地叹息班上同学的混日子,并教育我不要学他们。显然,我的学习得益于黄老师的教诲,不仅数学成绩有了很大提升,而且后来在高考中,有幸成为这所学校两名被录取的学生之一。
三
“非典”那年的清明节前,我抽空回了趟老家,去拜祭生我养我的父母。同行的大嫂告诉我,五叔近来身体不太好,已有点迂了。我颇感意外,甚至还不大相信,因为就在几年前父亲过八十大寿时,还专门请来五叔一聚,而那时他的身体还挺硬朗。然而有一天,大哥打电话告诉我:五叔去世了。
五叔,其实是大嫂的娘家叔,排行老五。他个头不高,约一米五、六的样子,不胖,但敦实,老实巴交的,没有多话。过去,大嫂的娘家比较贫穷,五叔又是个文盲,所以就一直单身一人生活。说起来,真有些对不住五叔:直到现在,我只知道他姓王。和他相处过的人,都说五叔是绝对的好人。晚年,五叔和他的哥哥生活在一起。
五叔于我是有恩的。当年,我在八堡菓林中学上高中时,和五叔曾共同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其实是五叔在照料我的生活。那时,四十左右的五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八堡果园“打工”——养猪。和他一起养猪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从沛县城里下放的知青。他们每人负责养三十多头母猪。养猪场坐落在种满梨树、苹果树的果园里,离学校有三里多路,这在满是风沙的大沙河畔,也算是个“世外桃源”。我住在学校,五叔负责我的一日三餐。一开始,五叔总是等我回去一起吃饭,由于放学时间多数不准时,五叔就一直等着。我让五叔先吃,五叔总是说:“我又没事,等你一起吃饭”。我坚持不让他等,五叔只好一脸地歉意表示:“那我把饭给你热在锅里,要是冷了,一定要再热一下,否则吃了会拉肚子。”
养猪场距离朱寨中学有七、八里路,五叔不会骑自行车,每次买菜都是步行。这对一贯吃苦的他来说,算不了什么。有一次,我见他平时黝黑的脸庞有点发黄,便问道:“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说;“没事的,饭在锅里,你快吃了去上学。”后来我才知道,五叔在赶集回来的路上晕倒了,可他仍然强撑着为我做好了饭。他时常感叹自己没文化,一辈子也就是养养猪了,并鼓励我好好学习,争取将来有点出息。末了,他总不忘加上一句:“千万不要像五叔这样。”
依然记得,听收音机算是五叔的最大爱好。在那个物质奇缺、文化生活沙漠化的年代,一台收音机算是像样一点的“家用电器”了。更重要的是五叔单身一人,平时连说句知心话的人也没有,因而,收音机在五叔的生活里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记得一次回家,我怯怯地向五叔表达了“能不能把收音机带上”的想法,五叔很爽快就答应了。可我没想到后来竟把收音机的“调谐”给弄坏了。我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误,赶快告诉父亲。父亲着急得不行,批评我不该带五叔的收音机回家来“烧包”。回到养猪场,五叔知道比事,嘴上虽说“没事、没事,”,可焦急的表情分明印在脸上。并且嘴里还不住地发出“啧啧”的烦躁声。第二天,我上过早课,到五叔那里吃饭时,他的同事告诉我,五叔一大早就赶集去了。中午,五叔早早就做好饭在等我回来。看到我,五叔高兴得如同孩子般地说;“我说没事的,这不一下子就修好了吗?”我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高中毕业后,我只见过五叔两次面。一次是在省城求学时,回家专门看望过他。那时,果园的养猪场已经解散,五叔回到他的老家继续种地;一次是在父亲过八十大寿的时候,把五叔也请了过来。当我把买的夹克衫给五叔穿上时,五叔不由得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但那笑声带给我的是一丝低沉,因为五叔已经老了。送五叔回家时,我给五叔带上了几斤白酒。五叔一再推脱道:“我哪能要这么多东西?”
没想到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的五叔说走就走了。大嫂在电话里哭诉道:“一个孤老头子,走了也是个解脱,他到那边,也许不再是孤身一人了。”大嫂是在安慰我。其实,大嫂也是在安慰她自己。
解脱的五叔啊,在那边,你一切都好吗?
如果说,五叔的离去让我感到难过,那么,偶尔一次“窃书”的经历,则让我惭愧不已。
后来,我无论搬了多少次家,还是经历过怎样的世事变迁,可那三本窃来的书,却始终被我完好无损地保留在身边。
我永远无法忘记高一那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建华没有回家。当时,我以刻钢板的名义打开了老师办公室的门。在办公室左侧,立着一个不大起眼的木橱。出于好奇,当我们把木橱下面的门打开时,一眼便看到了几十本图书。我和建华一下子惊呆了,因为这是我们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多的一批课外读物。于是,我们先是匆匆翻看了一番,然后如获至宝地分别从中拿了几本。我拿到的三本书分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和《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战例》。
这三本小册子,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摆放在我的面前。其中,前两本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定价分别为0.14元和0.13元;后一本是由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定价为0.21元。三本书内,都盖有“沛县菓林初级中学革命领导小组”的公章。须知,它们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极好佐证,也是我求知若渴的一次反面见证。
哦,我的难忘的青葱年代!
我的永远的村学乡学!
责任编辑⊙青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