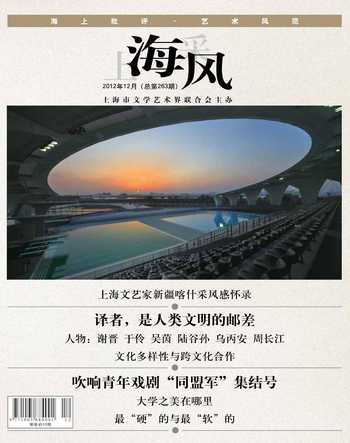长夜一行人


认识于伶是1962年的事。
其实,我早已在他的作品中“认识”了他。抗战胜利之后,我有机会读了他的《长夜行》《杏花春雨江南》等剧本,从他的作品中,我体味着“孤岛”中爱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主人公在那混混沌沌的社会里,在是非曲直交错的年代中,能够洁身自好,保持了一身清白而感动过;也曾对他笔下那位进步人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而感奋过。剧中人陈坚慷慨陈词时说的要“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那句台词,也曾让我受到激励,曾希望自己就要做一个像陈坚那样的人。我青年时期的朋友尤德衍曾经以“保持一身清白”来自勉和告诫我们,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你就是于伶先生笔下的俞味辛。”可见《长夜行》这个剧本对我的影响。而《杏花春雨江南》每一幕中,于伶都引用了陆游那些著名的诗句来“点题”,更加难忘。
例如:第一幕用的是“青山历历乡国梦,芳草也知人念归”;第二幕则用了“灯前抚卷空流涕,何限人间失意人”;第三幕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和“但愿胡尘一朝静,此身不憾死蒿莱”;到了第四幕,他又引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脍炙人口的诗句。陆游的诗,提纲挈领般地将剧中人所处环境,他们的心情与愿望以及情节发展的脉络都“拎”起来了。曾经经历过沦陷区生活的我,自然与剧本中人物的心产生了撞击,受到了启发和教育。
我崇拜这位作家,但我们之间却“无缘”接触,我与他是“遥不可及”的呀!
调到天马电影制片厂便找人打探于伶,他们告诉我这位上影的老厂长身体不好,已经长期不上班了。我哪里知道,他早已被某些当权者“挂”了起来,不给工作了!
196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与葛鑫导演从延安饭店作家沈西蒙暂住处出来,沿着常熟路向南,在巨鹿路口迎面看到了一位面容瘦削枯黄的“老人”(其实,他当时应为55岁,但在我眼中看来他已十分苍老了),葛鑫上去与他拉手,问道:“于伶同志,好久不见,身体好吗?”于伶笑答道:“好,还好,暂时死不掉!”话中带有调侃的味道。
他转脸看着我,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的眼神似乎在问:“谁呀?”
葛鑫见状忙介绍:“陈清泉,跟我一起帮沈西蒙搞剧本。”他没介绍我的场记身份,似乎要抬高我哩!我忙说:“我调到天马才一年多,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做场记。”
葛鑫插嘴说:“他是陈婵的爱人,从扬州调来的。”
他显得很高兴:“到上海来了好!好!”
接着,于伶便询问起剧本改编的情况,并说:“这是一部好戏。”然后我们便分手了。路上,葛鑫告诉我:“他是三十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的领导人,受‘潘杨事件牵连,已经‘靠边好些年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有好心情,肝也不好了,长年在家养病哩!”说着,指着巨鹿路上从西数去的第二幢小洋房告诉我:“就住在那里。”
这一别,就是十三个年头,再次见到于伶,已是1975年了——他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
在他遭受牢狱之灾时,我们与他的夫人柏李已成为“患难之交”,来往频繁,而且无话不谈了。
“文革”前,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结束之后,柏李便来到天马厂担任创作办公室的支部书记。
当时,我是个犯过“严重右倾”错误并且失去共产党人资格的人,我对柏李有些回避,觉得对这位支部书记应保持距离为好,以免自讨没趣。不料一天早晨,在办公室的走廊里迎面碰上了她——回避不掉了!正当我准备在沉默中与她擦肩而过时,她却绽开满面笑容向我点头打招呼了,我只好站定了身子回礼。过了不多时,我与陈婵到淮海路买东西时又碰见了她,我们三人便在人行道上拉了一回“家常”,这就让我取消了对她的戒备。我想,她肯定了解我的“劣迹”,但却没有一丁点儿对我的歧视,反而十分热情地与我们交谈,这是一位非同一般的共产党的基层干部。
“文革”开始以后,她当然“靠了边”,不久又听说于伶被抓起来了。出于一种同情,我与陈婵和王洁(时为导演助理,与陈婵多年同事,成为好友)特地到巨鹿路于府去看了她。
我们在客厅坐定,听柏李讲事件发生的经过,看着贴着封条的那些书橱,得知于府被抄家的情况(前后被抄了十次之多),不禁心潮难平,辛酸与苦涩交替侵袭着我们。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长夜行》中那位铁骨铮铮的地下共产党人陈坚,我曾经把这位剧中人当做于伶的自我写照,为什么共产党的监狱要把这样的同志关押起来呢?
我们的待遇步步升级,我曾经与柏李、宋崇(导演,粉碎“四人帮”后曾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曾就读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是柏李的门生之一)关在一个“牛棚”中。宋崇以敢于讲话闻名,他虽身处逆境,仍不忘指点江山,曾多次受到柏李的劝告和批评。身在牛棚中的柏李,对同志的关心——生怕被“造反派”揪住宋崇的“辫子”不放,令我不禁肃然起敬。
她被隔离审查了,还听说,这是因为她是一个国民党特务。这怎么可能呢?打死我也不信。当时,“造反派”指定我每天上班前就要将办公大楼的地扫干净,厕所冲刷好。隔离她的地方就在大楼北侧,食堂仓库的一间屋子里。于是,趁着无人我便悄悄地去探望她,她却一脸严肃地让我“快走”,她是怕被人瞧见对我不利呀。自己已身陷“囹圄”了,对别人还是那么地关心、爱护。
不久,我和陈婵在同一天被“隔离审查”并被抄了家。我被关在传达室后面一间小屋里,陈婵则与柏李成了“难友”。她们同“拘”一室三个多月,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于是,在五七干校建立“同窗之谊”返回上海后,我们成了最为密切的朋友,隔三差五总要相聚在一起。包括我们子女的恋爱、婚姻,都成了互相讨论并商量决定的话题,只是对于于伶大家却只字不提。
于伶回来了,回来得十分突然,但却让我们极其高兴,我们夫妻俩与王洁一起来到于府。那一天,谈起了他被捕经过时,我们才了解:他先是被关在上海一座小洋房里,过了个把月就转到上海市南市看守所关押起来。一年多以后,又被送上飞机来到北京,关押到秦城监狱。
我们问他:“在狱中九年,用什么打发时间呢?”
他说:“一是读书,二是吟诗,三是做气功。”他特别强调,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不但身体没有垮,而且连肝病也好了,是得益于不间断地做气功。他发现陈婵的面色不好,便劝陈婵也学做气功,并给她做了几个示范动作。我与陈婵后来对气功产生了兴趣,陈婵学了智能功,我学了香功,并坚持了一个时期,是与于伶的谆谆告诫分不开的。
他的女儿力文已在五年多以前结婚并育有一女彤彤。他叫于伶公公,于是我们中有些人如王洁也跟着叫起“公公”来,每次聚会时,大家“公公”长“公公”短的,煞是热闹(江浙的不少地方,有随孩子称呼长辈或同辈的习惯)。而我,则以于伶同志相称,一直未改,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良师益友,从年龄与他的经历来讲,他应该长我一辈,但由于陈婵与柏李已形成的姐妹之情,加上小彤彤见了我则呼为“眼镜公公”或陈公公,见了王洁、陈婵等人也都称“婆婆”,于伶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关系,所谓“祖上无亲,三代弟兄”也。
这种十分密切的交往,对我的帮助极大——我可以随时随地拜访他,讲我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和困惑,请他指点我处理某件事时应取什么态度、采怎样的步骤,等等。
厂里要我担任厂长助理,可把我吓坏了。那天夜里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我在文学部和第二创作室搞编辑工作,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先后搞出了几个定稿本并相继投入摄制,与一批作家也结下了创作友谊,可以纵谈“创作经”。丢下这么好的工作基础,去干那个陌生的一套——接替身患重病的杨师愈副厂长,分管财务、劳动工资、基本建设、职工教育……我怎么对付得了?!
我求教于伶,他那十分锐利的眼光从镜片后面直视着我,不疾不徐地说:“没有信心?”
我说:“对这些工作我一窍不通,哪里有信心?”
他反问我:“你搞剧本有信心?”我点点头,他又问:“刚做这个工作时也有信心?”
我说:“我喜欢这个工作呀,开头不懂,努力学呗!”
他笑了:“对呀,你学得不错,不是成了一个好编辑了吗?”
我这才明白,我已经“进了他的套套”了,但,他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启示——在干中学嘛。
我接下工作以后,马上就遇到“拦路虎”,财会科长拿了一份“资金平衡表”,我横看竖看看不明白,怎么不同数字相加起来贷方和借方的总数会一样呢,这又说明什么呢?我得马上实行于伶的启示了。
我儿子陈跃正在静安区业余工业大学读书,我问他有没有财会课?他第二天告诉我,有个财务管理班正在招生,我一听,说:“行,我去报名。”我们父子居然成为“同学”了。
不到一个月,我已经看懂资金平衡表了,一学期下来,可以与财会科的同志们讨论财务上的一些问题了。
于府从巨鹿路搬到吴兴路,组织分配给他一套三居室、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我也从上影厂调往市电影局工作。于伶对我的“进步”非常高兴,我也经常向他汇报电影局工作进展的情况。他给了我一个“特殊待遇”,可以在他的卧室中与他对谈。他的卧室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除了他坐着写作用的椅子外,还备有另一张大藤椅,冬天则放上棉垫子,他可以一半坐在房门口,一半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这张椅子便成了与他谈心时我的“专”坐,他在接待客人时是坐在客厅里与人见面的。
在于伶健在的日子里,我们每年总有好几次这样对坐着谈天说地,有时则是我专门提出问题向他请教。
在我记忆中,有这样几次讨教是终身不会忘记的。
组织上让我到文联工作,太出我的意外,我的担忧、烦恼的心情比调我担任厂长助理还要“结棍”,我找过几位老先生问计,也找到了于伶。
他听我说完之后,好像让我先吃一粒“定心丸”似的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分析了以前几位担任文联党组书记的同志的情况。
这不仅没发挥“定心丸”的作用,反而让我更为焦虑,便对他说:“于伶同志,他们是何等样的人,都是文艺界赫赫有名的前辈,我与他们之间的水平、资历、能力、威望相比,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呀!”
于伶不慌不忙地说道:“你看到了与他们的差别,这就很好。我同情你的处境,我也不太希望你去那个地方,但恐怕你不得不去!”
这最后一句话语气很重,一下子让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民主集中制原则不知在口头中讲过多少次,个人服从组织是党员的行为准则呀,叫我真为难死了!
于伶变换了口气接着说:“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一个为文艺界人士服务的地方,不是做官的地方。你的特点是,你与文艺界没有历史上的那种瓜葛,负担也就少,多数人会接受你。只要你坚持为大家多办一些好事,就可以立住脚。”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文联这个单位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剖析了文联工作中的难点,特别指出在与一些资格很老的同志相处时可能会碰到的困扰,要我注意,要与他们把关系搞好。
这是一次很有启发的谈话,与巴金、贺绿汀等老同志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也有许多谈得更直接,更深入的地方,让我受益匪浅。
这次谈话让我明确了几点:
一是当组织上考虑了我的意见之后还是决定我去文联的话,我只有服从——硬着头皮在文联闯一闯;
二是决不能把党组书记当官来做,而是要诚诚恳恳地为大家办事,做好服务性的工作。在主持主席团工作时尤须以小学生的身份出现;
三是对复杂的人事关系要谨慎对待,决不能搞亲亲疏疏的那一套。要谦虚而又不失原则,不去迎合什么更不要排斥什么,对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不要去“掺和”。
后来,我到了文联,于伶同志的种种嘱咐和亲切的指点,我是能够恪守的。由于于伶的意见与建议都被我消化了,虽然在工作中碰到过不少问题,也基本能化解。
在当时的文艺战线上,“左”的倾向与“右”的倾向同时存在,如果反应迟钝,很可能陷入某种倾向之中。这是我经常与于伶同志讨论的话题,在这种有趣且有益的讨论中,我,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文艺领域有一股“左”的思潮蠢蠢欲动之时,我去于伶府上向他介绍了一些迹象。他告诫我:要全面理解“双百”方针和“双为”方向,千万不要跟着一些人盲动,深刻理解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大意义,与文艺界的同志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他鼓励我说,你在文艺界现在的地位,要求你在与“左”和“右”的倾向斗争中带个好头。根据他的意见,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在全委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提出反倾向的问题,效果还不错。
他还及时提醒我,党组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文联的会员中,有不少是非党同志,要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头脑一定要清醒,原则一定要坚持,方法一定要妥善,态度一定要诚恳。这四个“要”成了我的座右铭,对我帮助极大,对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帮助。
1990年的2月7日(农历正月十三),于伶夫人柏李的几位好友,也都是于伶的老部下,闹着要给于伶过85岁生日,于伶与柏李都答应了,大家欢天喜地地祝他长命百岁。后来一算日子,我们提前了一年给他过了85虚岁生日。
再往后,他的前列腺毛病越发严重了,有人怀疑他是前列腺癌,总之他是经常在医院中了。
一次我去看他,见他精神不如从前,身体与脸庞都更加瘦削了,但他仍然问这问那,关注之情和爱护之意都溢于言表。我内心很感动,也因对他的病情不乐观而在情绪中流露了出来。他给我念了一首诗来证明他在狱中尚且那么乐观,对付病魔更“不在话下”了。
一位在旧中国漫漫长夜中,为了追求真理、民主、自由踽踽而行的斗士,在迎来新中国的曙光以后,却又有一些年头在等待光明的重新来临。
他写过《长夜行》,他长期在黑夜中的境遇莫非是这位前驱者的宿命。袁鹰先生为他作的传,书名为《长夜行人》是对于伶一生的生动写照。
谢谢袁鹰先生录下了于伶在狱中写的也是在病榻上念的那首诗,否则我是不能准确地写出来的。诗曰:
囚心何事起微波?
六十生辰梦里过!
俯仰胸怀天地阔,
灯高影淡舞婆娑。
革命者的胸怀是多么地博大,身陷囹圄的他,虽然连60大寿只能在狱中度过而有些无奈,但对于未来,他仍然满怀信心。长夜行人,因为时时都能看到光明的前景,他并不感到长夜是多么地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