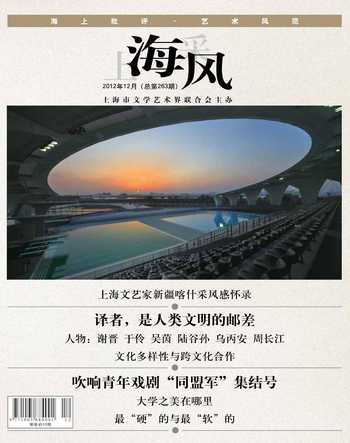我会用一生记住援疆人
梅平
金秋,随文联采风团走进层林尽染的新疆。从此,那一个个援疆人,就一直占据着我的脑海,他们欢笑着,泪流着,激昂高歌着,沉默无语着,鬓发白了,皮肤黑了,甚至乡音都改了……
我们到达的第一站,是设在喀什的上海对口援疆指挥部,副总指挥闵司林和他的同事们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席间,多才多艺的闵副总手舞足蹈为我们唱起了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你还有多少童年的朋友》——“已逾子夜/心又旁骛/独自抚摸自己的踌躇/我只是一棵树/……具有童年的梦想/还有一番深深地孤独/坚守着一种纯粹的追索/那是多么温暖的感觉呀……”闵副总说,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在帕米尔高原下的村庄,眺望着东方,眺望着上海,突然就有了这样的创作冲动。我明白了,为什么迎接我们的场面会如此欢腾热闹,是因为他们有着太深的孤独。望着面前这些晒得黝黑的有着纯粹追索的援疆人,眼前升起了一层热热的薄雾。
未露笑脸的女医生——在喀什的第二天,我们去了上海援建的第二人民医院。会议室里,十几位来自上海的医生端坐在我们面前。喀什的维族市民,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民族习俗和汉族有何不同,上海的医生,是他们最最顶礼膜拜的。上海医生,不仅在这里以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一位坐在前排的女医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欢迎的掌声中,她未露笑脸;在大家相互问候的笑谈中,她未露笑脸;当熊院长介绍到她时,她也只是微微欠一欠身,依然未露笑脸。她始终靠在椅背上,沉默着。她是厌烦我们,还是刚刚动完手术太累了?在远隔万里的边陲,见到家乡人,不应该是这样的。熊院长终于说到她了——这个坐在你们面前的女医生,知道她克服了多大的困难吗,家里没有老人,她的孩子寄放在了亲戚家,突然她丈夫又遭遇了车祸……熊院长语塞,掩面而泣,全场一片肃静。家里的大树倒了,她可以倚靠的肩膀没了,她只能靠着这张薄薄的椅背。但她依然坚强地坐在我们面前,依然坚守在这座医院里,她心里的那份信念一定没有倒。忍了很久的眼泪,夺眶而出。
乡音已改的兵团老兵——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的飞机晚点了,但大家决定不改行程。下午,我们一出机场,就驱车直奔需要二小时车程的石河子市。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象征,出乎意料地整洁、漂亮、现代、绿树成荫。走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我一直在寻找一位上海女兵的身影。五十年代,她离沪援疆,因为父母早逝,她就很少回上海。当上海电视台的镜头对准她的时候,白发苍苍的她,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贺知章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可她连乡音都改了,是怎样的沧海桑田!在浩瀚的图片中,我没有找到她,但我会记住这些把一生都融入边疆的兵团老兵。正如博物馆前言道:历史将永远铭记,是他们让荒漠变成绿洲,沙漠升起繁华,边陲更加安宁。接待我们的博物馆负责人说:上海和新疆建设兵团,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就为了这句话,不管会不会喝酒,我们端起手中这杯兵团自酿的烈性白酒,一饮而尽,被燃烧的感觉,直入心灵最深处。
我会用一生记住这些援疆人。
(作者为上海曲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