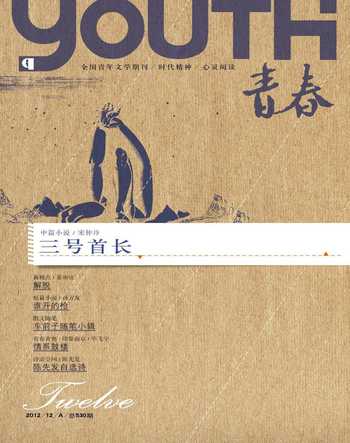热带雨林
佳佳和她男朋友带着一帮同学走了之后,我感到浑身疲惫,他们大战三国杀的这一下午,我就闷坐在墙角里喝红莓汁。我向来讨厌麦当劳的饮料,但那个下午除了喝红莓汁我没别的事可做。佳佳那个长得像何炅的男友花了半个多钟头教我们玩三国杀,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没学会。佳佳执意不让我走,佳佳说瑶瑶,给我点面子,请你喝红莓汁。
地下室的暖气开得很足,甩掉羽绒服的美女们像一颗颗从壳里蹦出来的饱满的花生米嗤嗤地冒着热气,熏得我有些神智不清,其实红莓汁的味道不算坏,看着男男女女一拨拨来又一拨拨去也不算太无聊,跟看戏差不多,只是他们的剧情比较单一,无非是循环往复的说、笑、咳嗽和吃。情侣们窝在墙边相互喂食打打Kiss,正中间的环形吧台边围着一群疯狂自拍的少年,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是那么High,不管是玩桌游的,玩手机的,还是谈情说爱的。在喝到第三杯红莓汁时,我终于感到了一阵恶心。
我抬腕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我想跟佳佳说拜拜,但一看到她兴致勃勃的样子我又犹豫了,我这人总是这样。
我注意到他时已经晚了,虽然他距离我并不远。那天下午他戴了副硕大的黑框眼镜,绒线帽裹粽子似的紧绷在头上,膝盖一会岔开一会并拢地在高脚椅上扭来扭去。吧台边除了他,只有一个瘦瘦高高的男服务生在收拾堆满垃圾的托盘,等走到他身边时,他突然抓起面前的一个纸袋,稀稀拉拉地倒出了几根碎薯条,随手将纸袋叭地窝成一团往地上一扔,大喊了一句:“×!”
男服务生一声不吭地捡起空纸袋掉头就走,那声“×”刹那间平息了三国杀的战火,佳佳第一个跳起来嚷嚷不玩了不玩了去KTV,花花绿绿的纸牌被十几只手搅着绕着桌上桌下四处翻飞,有几张还飘到了我的脸上。有刘备,小乔,还有关羽。
他趟着那股骚动的气流走来时,我已做好所有的准备,但当我的名字被他毫无差错阴阳顿挫地念出来的那一刹那,我还是几乎不能把持甚至相信自己的存在。
“焦——窈(yao)——瑶。”
他特意在第二个字上顿了顿,强调了一下那个字是上声。他说焦窈瑶,我盯你一下午了。
他接着说,×,焦窈瑶,你不认得我了。
他劈开两腿在我对面坐下,扭头冲着还在楼梯上朝这边张望的佳佳们打了个响指。
“都你同学?”
“嗯……有……”
“高中?”
“初中……也有高中……”
“你上大学了吧。大几了?在哪上?”
他像是突然被口水呛住了似的猛咳起来,一手卡住脖子,一手“嗞啦”一下扯开了羽绒服的拉链,咳一声就骂一句,×。
我说我认得你,皮伟。你嘴巴边有个黑痣。
他随手捻起桌上几张脏兮兮的面纸,朝后往椅子上一靠,右腿直直地伸出去,撞了一下我的左脚尖。
我说皮伟,我想不出要说什么,只好笑笑。
他的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只是在很卖力地擤着鼻涕。
最后我说皮伟,你现在是上学呢还是。
“上个×学!”
他“嗖”地一下将那团湿乎乎的面纸投到我面前的空纸杯里,伸出舌头来,一点一点将黏在嘴唇上的鼻涕舔了个干净,他“唉”了一声说焦窈瑶,我没你那个命。
我在楼上的洗手间门口排队时,天色已经黑下来,满厅里一片敞亮的灯火和人气,冲进门来的孩子们手里捏着大团大团的雪球相互往脖子里塞,嘻嘻呀呀地怪叫。
×,焦窈瑶,你不认得我了。
认出一个人的过去远比认出过去的一个人更具冒险精神,它需要一点智慧的膨胀和记忆的瞬间燃烧,皮伟认得的焦窈瑶不认识认得焦窈瑶的皮伟。
有点意思。
十三年前的皮伟剪了个西瓜太郎头,雪白的两颗大门牙龇在煤炭球一样的滚圆脸上,两手揣在肥鼓鼓的黑羽绒背心口袋里,见着女孩子嘴巴就开始不安分,小妞小妞地乱叫一气,被安上“小色狼”的绰号后他依然照叫不误:叫小妞是给你们面子啊,不信你们去热带雨林看看,你们到了那儿都是一群丑八怪。
皮伟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在班里散发他爸爸的名片,那些散发着刺鼻香水味的五颜六色的卡纸总是被皮伟工工整整地叠压在铅笔盒的底层,他用黑粗的小胡萝卜似的手指蘸蘸唾沫,一张张地捻起它们,嗖嗖嗖地往我们的座位上飞弹过去,“皮亚新经理”“热带雨林舞厅”“华鑫街28号”和那一串电话号码渐渐在我们的木头课桌上生了根发了芽,在教室一座大网棚里交织成蔓,流淌出一股股甜腻的油粉汁液,熏得我们昏昏欲睡。直到有一天,皮伟被班上个头最大最壮实的男孩按在窗框上,一边把他的唇颊往死里掐一边大把大把地朝窗外播撒着那些被撕烂的名片。
“叫你骗人!叫你再骗人!”
皮伟一动不动地仰着头,碎纸片噼噼啪啪地盖了他一脸,又倏地被一阵猛风扇刮得七零八落。他将两只胳膊高高举起,掀扯开湿甸甸地钩挂在树梢上的云霾,他又看到了,只有他看到了华鑫街28号的大火仍在熊熊燃烧,无数珠宝、酒瓶和女人从倒悬的一座宫殿里汩汩而下,他那戴着金王冠的父亲将他裹在被烧焦的大氅里躲闪着四处爆炸的火球,他在他父亲的指缝里看见狞笑的王后,他的母亲,在最大的一颗火球里舞起黑纱,渐渐地扭曲成了一道狭长的光环,锁住了他和他父亲的身体,他感到一阵被灼烧的剧痛,接着便是一股炽烈的液体顺着他的大脑门流到了他的嘴里。
男孩子们一哄而散后,皮伟仍然将头仰在窗外,两只胳膊在空中抡来抡去,他父亲拆线的那天他也是这样,被他祖母抱在怀里,挣扎着朝窗外伸出手,想抓住树枝上打架的麻雀。
他的脸猛然贴住了一片陌生的肉赤色的领域,那里曾经被无数女人的红唇占领,如今却只能忍受一个小男孩稚齿的屠戮。他越是大哭大叫,他父亲就越不放过他,最后他被震碎了,骨头关节一寸一寸地软将下来,沉沉地瘫睡过去。
十三年后的华鑫街28号是小镇上最大的一家KTV,“热带雨林”四个大字不分昼夜地向四周挥发着赤裸裸的光和热。如果不是和皮伟的一次重逢,那些被时间的藤蔓缠绕得奄奄一息的往事和记忆是不是要在那一座热带雨林中贪得无厌地继续沉睡?
等我回到楼下的座位时,皮伟已经不在了,刚才那个高高瘦瘦的男服务生正在清理着桌上的一片狼藉,那团湿乎乎的面纸从纸杯里掉了出来,染上了一大块漏在托盘口的番茄酱。
红莓汁勾起的恶心开始重新泛滥。
我走出麦当劳时发现雪停了,风刮得依然很猛,我翻出手机里三个未接的佳佳的电话回拨过去。
我听见电话那头有人在扯着嗓子吼着“死了都要爱”,佳佳不耐烦地冲我喊道:“喂,喂,你来不来啊,在热带雨林呢,要来赶快啊……喂,喂,听见没……挂啦。”
我试图从我刚刚摆脱掉的那个喧嚣乏味的世界中彻底地清醒,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我甚至怀疑起刚刚过去的下午是否存在,我是否真的喝掉三杯红莓汁的下午,我是否真的遇见皮伟的下午。
我决定去一趟热带雨林,当我抬起靴子一脚踏进雪里时,我又犹豫了。我这人总是这样。
自从皮伟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他父亲的那些名片后,他并没有再弄出什么别的花样,他一门心思地扑在了他的“小黑”身上。
小黑是我们在中午的上学路上一起遇见的一条土狗,长得精明健硕,唯独右边的后腿稍稍有点瘸,一见我们就直梗梗地挺着细长的脖子汪汪汪地撒起野来,当男孩子们争着抢着逗引着它玩时,皮伟依然将两手揣在肥鼓鼓的黑羽绒背心口袋里,一声不吭地盯着它在火腿肠之类的诱惑下乖乖地舔着他们的手臂,突然“嘿嘿”冷笑两声:“呸!不就是一条脏狗么,有什么稀奇。”大家散去后,他常常一个人落在后头,嘴里不知在咂巴着些什么,那只狗(他们后来都叫它“小黑”)一开始还会围着他兜几个圈子,到后来理都不理他就一瘸一拐地跑开了,我们走了老大远后,回头就看见皮伟还蹲在地上朝小黑溜去的方向一颗一颗地砸着石子儿。我们都觉得有些不大对劲。
终于还是出事了,那天皮伟主动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小浣熊干脆面,掰下一小块来悬在小黑的鼻尖上,小黑扑上一步,他就后退一步,愣是不让它够着,起先大伙儿都在旁边跟着起哄,突然,小黑抖着鲜红的舌头猛蹿到皮伟身上,对准他的右胳膊就是一口,还没等大伙儿反应过来,皮伟已经嚎叫着跑出半米开外,小黑追着他一路狂奔,眨眼就没了踪影。
那天下午我们都看到了皮伟他爸,他中等身材,穿一身笔挺的西装,左眼角下方有一大块红褐色的疤痕,他阴沉着脸走进教室,哗啦一下将皮伟课桌上的东西都揽进书包里,“嗞啦”一声拉起拉链,随即提着书包走回门口,向班主任点了个头就大步离开了。
皮伟没过几天就回到了学校,他捋起袖子给我们看他的伤口,龇出的门牙显得很得意,最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皮伟竟然撺掇着他爸将小黑从狗主人那里要了过来,他把它调教得服服帖帖,从此和他形影不离。
“焦窈瑶,你现在还学那个什么什么琴的……叫什么叫什么……”
“你说琵琶?”
“啊,对对对……”
“早不弹了,怎么了?”
皮伟转过脸去又咳嗽了一阵,呼哧呼哧地往嘴里吸着鼻涕,脸上涨起的一股潮红一直泛到了脖子根上。
“喂你还好吧。”我随手递给他几张干净的面纸。
他将揩完鼻涕的纸团放在手心里搓着,有好一阵子我们就这么面对面地干坐着,也不说话。
“你上班了?”
“嗨,瞎混呗。”他“嗞啦”一下拉上了羽绒服的拉链,“你同学是不是去热带雨林了?刚那女的不是说要去K歌的么。”
“我不知道他们啊,可能是吧,干嘛?”
“热带雨林是我爸开的,他妈的开不长了,××的王紫紫在跟我爸闹离婚……喂你不会不记得王紫紫吧,贱女人不是跟你们一伙的么,弹个×琴,搞个×艺术,我呸!”
于是我就听见了热带雨林藤蔓下咯吱咯吱的响声,那些四分五裂的记忆碎片挣扎着投身热带雨林里燃起的浓浓烈火,我在被火焰扭曲的影像中看到了十三年前抱着琵琶,坐在那次演出的高背椅上双脚悬地的自己,看到了坐在舞台中央浓妆艳抹的王紫紫,我还看见了缩在广场旮旯里的两团黑影,他们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直到像野兽狰狞的大口吞没了整个舞台,整片烈焰,整座热带雨林。
一阵剧烈的咳喘后他把黑框眼镜向上推了推,朝我伸出手:“焦窈瑶,有面纸么。”
在皮伟眼里,天下最美的女人是他母亲,他很开心他妈一把火烧死烧废掉了热带雨林舞厅里一群勾引他爸的“贱货”,他给我们看过他偷偷藏起来的他妈妈的一张半身照。
“能烧的都被我爸烧了,这是我外婆后来给我的。”
照片上的女人长得和皮伟一样的滚圆脸,微蜷的头发披散在双肩,锁得紧紧的眉头下的一双细长的眼睛显得有些失神,两片薄嘴唇神经质似的轻抿着。
反正没人说她丑。
算起来,王紫紫曾经还是我的同门师姐,我们跟的都是小镇上颇有点名气的章琴师,当年章琴师常带着我们参加区政府文化教育部门组织的一些文艺汇演,有时在剧场有时在露天。皮伟被小黑咬伤的那年我们在华鑫街上文化馆前面的广场演出过几次,我很意外地看见皮伟他老爸带着一群人跑前跑后地调试和安排现场的音响布景,他似乎比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胖了些,长长的头发乱七八糟地甩来甩去,他站在舞台斜上方的平台上指挥着下面时,常常激动地边大喊着这那的边一把捋过头发,那块眼角下的疤痕在阳光下醒目地一闪一闪。
有时皮伟他爸会趁着彩排的空隙坐在章琴师身边边聊天边抽上几支烟,他注意到王紫紫是必然的,王紫紫往我们这群孩子中间一坐实在是太出挑了,细黑的辫子被编成几缕缜密地盘在头上,她天生了一幅宽宽的额头和一张很大很丰满的嘴,冬天露天演出时我们都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只有她仍然穿得熠熠夺目,那把据说是章琴师最好的琵琶在她翘起的大腿上颠簸着,当章琴师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纠正我们的指法时,王紫紫就将琵琶横架在腰下,涂得鲜红的指甲反反复复地拨挑着闷弦。
我们都不晓得王紫紫的来历,有人说她是章琴师的亲戚,也有人说她以前是做小姐的,我们甚至没见过她卸妆后的样子,有人猜她十八,也有人猜她已经三十了。
元旦演出前的彩排皮伟跟着他爸来过,有时小黑还汪汪汪地跟在后面,那阵子他爸早已和章琴师打得火热,穿得鼓鼓囊囊的两个男人一边搓手跺脚一边吞云吐雾时,王紫紫突然就提着琵琶摇摇摆摆地晃过去跟着大说大笑起来,皮伟远远地望着他爸把手臂揽在了王紫紫的腰上。
皮伟就走了。
演出那天的天气很不错,舞台上方高悬着“欢庆元旦”的大红横幅,四面花团锦簇地扎着气球和彩带,广场上的观众席一排排的高背椅摆放地整整齐齐。皮伟他爸将一头长发打理得油光锃亮,又穿起了笔挺的西服,端端正正地打着领带,点头哈腰地朝在前排落座的领导递着香烟,一边时不时地跑上舞台对着正在调试中的话筒“喂喂喂”地吆喝几句。
我在舞台右后方临时搭起来的化妆间里见到了皮伟,化妆师正在往我脸上扑粉,一个模糊的影子突然闪了进来。
“嗨,焦小妞。”
那些化好妆坐在一边的女孩子们都咯咯咯地笑起来。皮伟依然罩着那件油渍斑斑的黑羽绒背心,冲着她们来了个飞吻:“嗨,小妞儿们。”
女孩子们笑得更欢了,这时裹着白色羽绒服的王紫紫抱着琵琶走过来,不耐烦地把皮伟往边上一推:“臭小孩儿,滚一边儿去!”她怒气冲冲地往那个女化妆师面前一坐,“这都化得什么妆,你眼瞎了啊,快给我重化,快点,快!要来不及了!”
王紫紫的独奏《十面埋伏》被安排在第三个节目。
我都没注意皮伟是怎么溜出去的,直到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后主持人宣布王紫紫登场,我和女孩子们抱着琵琶坐在候场席上等待下一个合奏,当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王紫紫身上时,我终于在密密麻麻的人头中找到了皮伟,他蹲缩在广场南面的角落里。
他并不是一个人。
我的眼前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了皮伟蹲着拿石头砸小黑的场景,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就当王紫紫叩响了全曲的高潮时,人们看见一束黑光像离弦的箭般从他们眼皮底下飞驰而过,肆无忌惮地纵身一跳,将舞台上架起的一排话筒猛扑在地,接着便是“咕咚”一声巨响后王紫紫尖利凄惨的近乎撕裂的喊叫。
皮伟给小黑做了一个坟,当时我们都围着他,看着他用指甲一点一点地抠着土,直到抠出血来,他从黑羽绒背心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了他母亲的那张照片,啪啪几下撕了个粉碎,把它们埋进土里时皮伟哭了,他跪在那个土包前用沾满鲜血和泥土的手紧紧捂住脸,热带雨林里燃起的大火就这样熄灭了。
寒假结束后我回到城里继续上学,我有些后悔没有和皮伟要个电话号码或者QQ什么的,但是我又想不出和他再次见面的理由。约上佳佳他们再去热带雨林K歌么,说不定能遇到他,或者他爸,还有那个什么王紫紫也说不定。
又过了两三个月,五一节放假前我挂了个电话给佳佳。
我说上次真不好意思,我说什么时候再聚聚,把大家约出来去热带雨林怎么样。
佳佳“哈哈”了一声说还热带雨林呢,我的小姐,上个礼拜我回家的时候就拆得不成样子了,最近事儿多,没空,有空再联系啊拜拜。
我一个人去了华鑫街28号,“热带雨林”四个大字已经被掏空了,像是陷在一座空楼架子上的四个骷髅洞,震耳欲聋的敲击和爆裂搅得我心烦意乱,但当我顺着华鑫街一路小跑直到跑到当年的文化馆,现在的金浦大酒楼附近的小巷子里时,我的胸口又涌上一阵难以忍受的空虚。
也许下一秒,皮伟就会从巷子那头蹿出来,歪戴着一顶鸭舌帽,两脚擦着地“嗞啦”一下滑到我面前,刹住车。
皮伟朝我笑笑,将鸭舌帽往前面一转,昂起脖子仰望着被两座居民楼夹得紧紧的狭长的天空。
皮伟指指上面说焦窈瑶你看,热带雨林。你看见热带雨林了吗?焦窈瑶。
【评语】
这篇小说语言细密,形象的选取很特别,因为“我”与主人公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意识的粘性很强。在饱满地刻划形象的同时,完成了意识的传达,而主题没有先期设定,消隐于整体的过程之中。这样的写作,是开阔、丰富和诚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