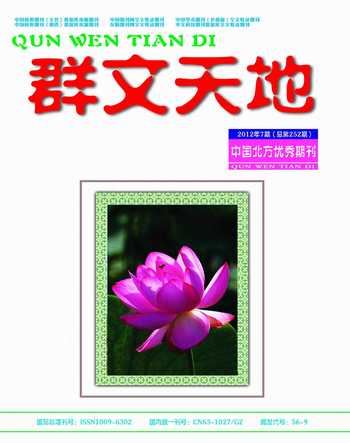吾国是个“文人国”
尹臻
“文人”即“文学人”。说吾国自古是一“文人国”,应该不算太过分。古时候大凡识文断字的,或粗通文墨的,总之是多少有些文化的,也就多少懂些文学。多少懂些文学,便是多少有些文化,也就大小是个文人。这还是最为基层的草根文人,至于高层的高雅文人,当然都是文学上的通人。或者说,正因其文学上很通,所以才有资格走上高层政治,成为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古中国的政治,与其说是“士大夫政治”,不如说是“文人政治”。文人政治下的古中国,当然文风很盛,当然很容易成了“文人国”。
“文学”一事虽早见于孔圣人之门,但它的含义毕竟与今日有很大的不同,大约等同于“文章博学”,其范围要比今日的“文学”大得多。古时社会分工的程度甚低,知识系统亦因之缺乏分化,今日人文学科里卓然独立的文史哲三科,古时却是整合在一起而不分彼此。所谓“文史不分家”,说的正是此种情形。实际情形甚至比“不分家”还要严重,“文”简直就是“史”,“史”亦径直成了“文”。太史公的《史记》,固然是“史”,却也被古人视作天下之“至文”,“汉世文章两司马”,司马迁显然成了古人心目中超一流的文章高手。甚至说太史公首先是“文学家”亦不为过,毛泽东追悼张思德,曾引史公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分明将史公呼作“中国古时候”的“文学家”。章学诚谓“六经皆史”,而在古人的意念里,“六经”又何尝不是“文”呢?韩愈就说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他的为文之道,不过是整日“泡”在这些“经”里,“沈浸浓郁,含英咀华”,然后“作为文章”。“六经皆文”,而“六经”乃中国文化之命脉,乃全部学问之渊源,由是而谓“文”乃学问之源,也就顺理成章。青年毛泽东苦思为学之道,有一阵忽有所悟,乃叹曰:“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终其一生,能文艺,娴诗赋,削一分地葆有文学家乃至诗人气象。
在古中国这个“文人国”里,士大夫是文人,皇上也是文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不一定就“略输 文采”或“稍逊风骚”,“茂陵刘郎秋风客”,汉武颇谙风骚,亦具文采,这是“鬼才”文人李贺也都认可的。皇上叫士大夫命题作诗,或者皇上与士大夫相互唱和,是士大夫的雅事,亦是皇上的雅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下激荡间,文学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因而获得“文化霸权”。既获得“霸权”,势必越界挺进,而行“学科殖民”之能事。于是乎,原本就整合在一起的各科知识,更加一一沾染了浓烈的文学气。细思起来,这个“文学气”乃是一种弥漫开来且深入骨髓的观物方式或思维模式,不妨径直名曰“价值观念”。在此模式或观念的主导下,士大夫习惯于以文学化的方式发现问题、看待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
他们往往怀揣浪漫理想且富于激情,一副孤冷而往,“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样儿,确实显得很高远很大气。更多的时候,他们很火热,甚至在燃烧,此间他们经常发生如下情状:喜怒无常,一惊一乍,哗众取宠,急躁冒进。在这种情状下做事,他们的行事风格也就不外乎“大”与“空”。“大”是说他们最喜大而化之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满嘴圣人语录,言必论“道”称“王”,动不动就好大喜功胆大妄为,要为这个“立心”,要为那个“立命”,动不动就是上下几千年,继的皆是昔日几千年的“绝学”,开的都是未来几千年的“太平”。同时,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小事,均属“形而下”。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像他们这样的文人君子,“务”的只能是“虚”,干的只能是宏伟的“道”的事业。他们认定此乃命也大,按照孔老夫子的说法,乃是“天生德于予”,完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则“大”矣,然过度的“大”必至于“空”,“迂远而阔于事情”,到头来一事无成,这便是千古文人的宿命。
文人又无一不是狂狷之徒。浪漫躁进,即是典型的“狂”,所谓“狂者进取”。一般说来,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吾道自足,不假外求。很多时候,他们还会将自己与“天”联系起来,如“知天命”或“知我者其天乎”,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或“尽心”进而“知性”进而“知天”。如此联系起来,文人就更是了不得了,更是狂得不得了了,动辄“万物皆备于我”,动辄“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总之是一副“舍我其谁”的模样。此间,他们明显地产生了幻觉,仿佛普天之下,唯我独醒,又仿佛自己就是“天”特派下凡,或者简直就是“天”的化身。狂态百出的文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替天行道”,也就是以吾道改造世界,为天下苍生谋永远之福。至于“狷”,乃是一种更厉害的“狂”,“狷者有所不为”,稍有不合己意处,就耍性子,还要撂挑子,索性退回去,退到田园去,退到终南山去。此乃以不合作的清高姿态凸显他人的卑鄙龌龊,以“退”的方式完成更好的“进”。文人这一“退”,一般而言,能退出莫大的名声,能激起偌大的社会舆论,他们最终还真能进步一大步。
除了狂态百出,除了富于浪漫激情,文人还非常容易产生道德义愤。他们悬了一个高不可及的道德境界,唱出十分悦耳的道德高调,让大家产生一种美好的错觉,似乎天地之间唯有道德最宝贵,或者天地之间所有的事情皆一一可约化为道德,一切的问题皆可归结为道德的问题来解决。道德固然重要,但人生和社会不能只有道德一事,道德决不能代替一切。事实上,那么高的道德,大家都清楚自己几乎没有做到的可能,加之他们大树特树“道德楷模”,并诱之以功名利禄,大家便一起作伪,“假道学”之所以盛产于古中国,原因即在此。他们愈是看重道德,愈是能体验到道德的诗意和美,而人间世是如此的不道德,他们也就不得不生了很大的气,气急败坏地骂大家都是“禽兽”。
古中国如此深厚的文人传统,时至今日还在大畅其道。放眼当下的人文研究,很快会发现,仍旧有不少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人”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挥洒激情和才气。何以如此,原因多多,但不可不察文人传统的“遗传密码”。上述所列的文人情调,他们一个也不少,同样是浪漫多情,激情似火,一会儿天马行空,凌空蹈虚,一会儿又无事生非,故作惊人语;同样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一副真理在手的俏模样,若是喝了若干洋墨水,更是“飘飘然有凌云之意”,直不知自家身价几何,或者身在何处;也同样是道德至上,尤其喜欢把人道问题道德化,总在发道德脾气,总在骂大伙道德堕落,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不懂中国的历史,没有任何历史感,也不屑于眼睛向下,细心考察当下现实,耐心发现现实问题,只是迷信“主义”,崇拜洋教条,仅凭那儿条“宏大叙事”,就妄图包打天下,甚至妄图为天下弱势群体谋永远之福。
鲁迅在遗言里,曾谆谆告诫儿子海婴,切莫做“空头文学家”。还是鲁迅眼光毒辣,看准了“文人国”特有的“文人病”。他其实是想告诉儿子,一旦做了“文人国”里的“文学家”,便是集假、大、空之大成,想不“空头”都难。海婴果然不负乃父之志,做了一名无线电工作者。鲁迅有知,大可含笑地下矣。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