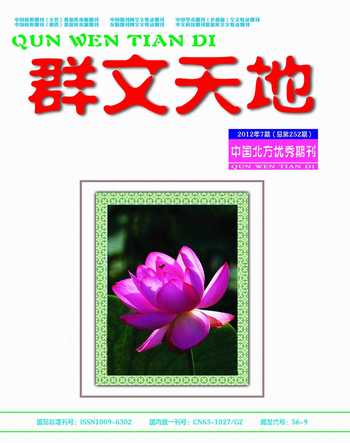史重人事长于征实
黄永泰 任玉贵
对湟源民众及其后人来说,要振兴古城,提高他的知名度,必须了解他的孕育、形成、嬗变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近年来一些媒体、作者在报道和撰写的作品中,存在许多扭曲现象,混淆了脉络,淡化了主旨,改弦了轨迹,诸如电影《藏客》、电视专题片《丹噶尔财富传奇》、出版物《青海之书》等等,令笔者看后痛心疾首。湟源丹噶尔的有关报道和作品,应将最丰富、最光彩、最重要、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观众,这个过程中决不能道听途说,浮皮潦草,胡编乱造。须知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史重人事长于征实。
关于电影《藏客》
看了电影《藏客》,心绪忐忑不安,笔者没有参与电影《藏客》,脚本也没看一眼,更不要说整个摄制过程,从未征求过意见,可说是局外人。作为反映湟源地方历史风云人物的该片,其实离谱太远,哗众取宠,过度包装作品,与朱绣丰功伟绩也无关宏旨。不知依据什么进行导演和把脉的。
朱绣赴藏和谈的资料非常翔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两相对照,电影《藏客》确有知殊少史实,弃旧图新,破绽百出,不伦不类,无稽之谈的假太空怪圈,笔者只是毛糙地说几点。
(一)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注释记载:“西藏于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在湟源首次设立噶尔俸(即商务办事处),湟源邑人才开始了解西藏地方商业行情。”据《湟源文史资料》记载:“湟源藏客起家并赴西藏的时间是民国23年(公元1934年),而且只有三人全系蒙藏牧民。
众所周知,朱绣赴藏和谈事件发生在民国8年(公元1919年)朱绣赴西藏和谈15年后才有藏客之名,电影《藏客》中反映藏客保护和护送朱绣进藏时过境迁,是故弄玄虚,飘渺无影之事。因而不能不说朱绣赴藏和谈与藏客分道扬镳,是毫无关联的两码事。故《藏客》冠名没有实际存在的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形同虚设,空担名声。
(二)朱绣赴藏和谈,是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倡议,甘肃督军张广建转呈北京政府批准的,后来朱绣完成使命,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并召开西藏善后会议,说明这是国家行为,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而不是算个人藏客或集团的私人行为。如果退一步说,当时就有藏客,也望尘莫及,凭借几个藏客,几条步枪,盘马弯弓,要护送朱绣险象环生的六千里路程,笑不量力,岂能成行?
(三)据史记载:北京政府批准朱绣等赴藏和谈名义是“甘肃政务友好慰问团”,因而甘肃督军张广建也不敢怠慢,立即将代表团成员活佛古浪仓、拉布尖贡仓召请到兰州,面授机宜,并叫二人立即返回玉树,做好前期工作,迎接朱绣等人的到来。然而电影中古浪仓却在湟源县扎藏寺与朱绣见面议事,既无可能,也无莫及,荒诞不经,纯属子虚乌有。
(四)据青海文史资料记载:朱绣赴藏和谈是关系国家之统一,民族之团结的大事,关系重大,非同小可,引起了北京政府、甘肃督军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经营青海,遥控西藏”的马麒作为头等政要,特意派选堂弟马彪,统领宁海军第22营,122名全副武装的骑兵,从西宁出发,作为朱绣赴藏和谈的安全保卫部队。这样,谁护送朱绣赴藏和谈不就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五)据朱绣编写的《海藏纪行》记载:“二十九日,晴,早八时,从湟源启程,陈县长及绅、学各界祖饯湟水桥畔。向南行,循湟水入药水峡。”依据这段记述,朱绣从湟源启程,县城倾巢而出,万人空巷,人头攒动,夹道欢迎,热闹非凡,至今有口皆碑。直达玉树,除中途遇到几个抢娃外,基本上畅行无阻。电影《藏客》中所演“东科寺枪战”、“日月山对峙”等,向壁虚造,生搬硬套,哗众取宠。
(六)湟源虽然有洋行十一处,但都是京津买办代理,《藏客》中所塑造的英国人,可说是个空降的,也可说是外星人,因为据《湟源县志》记载:洋人出现于湟源是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头一个是美国传教士伯立美。洋人在湟源干涉和阻止朱绣赴藏,在当时马家统治下,英国人有这种企图,也是黄粱一梦。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历史中的人又不断被历史所演绎和得以证明。朱绣一生,盖世奇功,棺盖定论,永垂青史,名震华夏,一代俊才,壮志早殁。请看笔者发表的《朱锦屏赴藏前后的政治背景》约一万多字,还有《惊世骇俗说歇家》、《朱绣生平略记》等,借前人后尘,说得比较全面准确,最近湟源电视台举办的“丹噶尔老故事”中,笔者多次讲到朱绣赴藏的事件,颇受观众认可。电影《藏客》无须节外生枝,胡编乱造。《西宁府新志》序中有“文要虚,史则实”之说,写小说可以虚构,但反映地方历史人物的电影,必须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如实反映,说一不二这是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电影《藏客》正失于其,所以放映后,作为娱乐片“昙花一现”、“嗤之一笑。”
其实,笔者以为,有关朱绣赴藏和谈,不在乎谁送谁接,与谁发生关系,而在于朱绣他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拉萨,与达赖及西藏上层和谈,慷慨陈词,耐心劝导,终于使达赖答应“倾心向内,民族共和”,彻底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分裂西藏,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罪恶阴谋。这才是朱绣赴藏和谈的真髓精要,灵魂所在。电影《藏客》能做到吗?
关于电视专题片《丹噶尔财富传奇》
最近中央电视台四频道“走进西宁”专题片报道了之三《丹噶尔财富传奇》(以下简称“传奇”),看了之后,有一部分观众认为好,以为上了中央电视台,规格高,名声鹊起,笔者不敢苟同,不以为然。如果说清代、民国初期丹噶尔商贸繁荣,给参与各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那么“传奇”抓住了芝麻,丢了西瓜,弄巧成拙,只说了些皮毛、表层现象,无关丹噶尔商贸宏旨和财富积累的要核,不信,请你参目,本文将拟出:一、对《传奇》的三点质疑;二、“歇家”、牙行、洋行、藏客的由来;三、丹噶尔财富所谓传奇的要核。
一、对《传奇》的三点质疑
首先,《传奇》没有给观众交代什么是“歇家”、“藏客”。“歇家”、“藏客”是清代以来商贸领域中唯一的符号,《传奇》却无所问津。对“歇家”、“藏客”主体定位中离谱太远,说什么“歇家”是坐商,“藏客”是行商,这种界限划分,作为编导妄言,令人哑然失笑。
其次,《传奇》表达关键方面有虚假现象。诸如“丹噶尔财富250万元,占当年清政府财政的十六分之一”,可谓“财富之奇、富甲天下”。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表述,丹噶尔财富250万元,是指双方或多方商贸交易的总额,既不算总收入,也不概括总产值,只是所反映的商品进出口流动资金指标而已。据《丹噶尔厅志》、《青海商业志》记载:丹噶尔商品进口中,蒙藏地区约占60%,内地约占28%,本地约占12%。在总销售额中,销往内地的占58%,本地的占28%,藏区的占17%,显而易见,财富多不积淀在丹城。有资料表明:藏客从牧区收购羊皮,每张白银一戋,到丹噶尔售价白银1两;一两白银在丹地买斜布16尺,却在牧区收银3两,其利润超过10倍多为藏客所有。洋行在丹城收购羊毛,每百斤市价在10元上下,但贩运到天津售价达40-50元,除了运费、税金不足1元外,其全部被洋行所得,丹城望银兴叹,眼看肥水流淌外人田。
再次,《传奇》奇在什么地方?看了后甚觉没有突现商贸中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人文特色,给观众的印象不是传奇,而是一般;普遍性多,特殊性少。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奇货可谈,甚觉遗憾。在此,不妨笔者在下面介绍“歇家”、牙行、洋行、“藏客”冠名来历,此表诠释。
二、“歇家”、牙行、洋行、藏客冠名的由来
什么是“歇家”?清光绪时,令青海皮毛集中于丹噶尔,丹地既是蒙藏牧民出入之门户,又是全省皮毛的唯一集散地,牧民每年秋冬赶着牦牛、骆驼数百头(峰),运来以羊毛为主的畜牧产品,抵老街后,就地露宿,人畜在城镇上生活,在贸易方面有诸多不便。同时,洋行和内地人初来乍到老街,对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开展商贸交易困难重重,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手握资本、又精于蒙藏语言的商人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形成新兴的“歇家”行业。据《丹噶尔厅志》记载:“仅领取官照的歇家就有48家之多。”所谓“歇家”,都是熟悉蒙古族、藏民族的生活生产等情况,精通蒙藏语言,是蒙藏牧民的固定顾主。凡蒙藏牧民驮运来的羊毛、皮张等,除零星出售少许外,全部交给与已有联系的歇家,再由歇家介绍出售于洋行或住庄客商,有的直接由歇家收购,歇家囤积居奇,按照市场的供求变化,适时抛出,赚取更大利润。同时,以自己所掌握的物资,胁制外商,故洋行、山陕京津等客商,必须委托当地歇家,每年春夏先预付巨款或茶布粮食前往牧区预定皮毛,秋冬交回羊毛皮张,蒙藏牧民经歇家中介,将皮毛等销售后,又托歇家买回自己所需的青稞、面粉、挂面、茶叶、馍馍、布匹等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有的由歇家直接供应,有的由歇家从市面买进后转手卖给牧民。这样,歇家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不仅是蒙藏牧民经商的代理人,又成为洋商贸易的代理人,还从洋行外商、蒙藏牧民两方面赚取丰厚利润,这就是歇家广开门路,生财之道。
根据以上,湟源歇家具有较好的经营设施、经营技术和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具有较强的向内吸引和向外辐射的流通能力,对扩展牧区之间、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繁荣和稳定商品市场,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什么是牙行?由于市场繁荣,民贸发达,客商辐辏,货物云集,所以各类经纪牙行业应运而生。直至民国初年,明清老街共有各类牙行十个,其中有羊毛秤行、斗面行、山货过载行、水果行、鱼行、青油行、煤炭行、牛羊牲畜行、骡马行、裘皮行等,各行业经纪人近40户。诸如大宗成批交易的羊毛都须经由羊毛牙行居间介绍,寻求买主,评定等级,商议价格,成交后由牙行过秤结算,清结帐款。该行业组织形式健全,颇得买卖双方的信任,全行设有固定办理业务的地点,推行总负责一人,司秤、划码、记帐、结算等若干人,羊毛成交过秤中买卖双方及牙行三方划码记帐,经核对无误后,由牙行负责结算,按期收会货款,收取佣金。对各经纪人在一个年度内,按佣金收入,分次预分给部分个人所得,年终结算后扣除各种税费及行内公用经费外,余额部分按各经纪人应得分额进行分配。
各行因行业的不同特点,经营形式也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经营形式:一类是设立店铺,定点经营,如斗面行、鱼行、山货过载行、水果行、青油行等;一类是沿街市巡回、流动经营。在流动经营中,有的行业如羊毛秤行则定点办公,统一集中流动。如煤炭、牛羊、骡马、裘皮等行,各业主时合时分流动经营。老街贸易,十分火爆。
什么是洋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市场上羊毛、皮张火爆,国内外商人合资经营的天津洋行,开始伸入湟源地区,以明清老街为据点,投入巨额白洋,大量收购羊毛,先后来驻庄的外商有英商新泰兴、天长仁、仁记,美商平和、怡和、居里、瑞记,俄商美最斯、华北、土商瓦利等十家。羊毛市场逐渐被垄断,当时英国希尔兹在一份报告中称“丹噶尔毛主要握在十大洋行手里”。美国人费里朴评价:“毛在亚洲毛区八个品种名列第一,是世界上难得的地毯毛”。青海羊毛统称丹噶尔毛,在国际市场上负有盛名,转手之间,获利很大,当时毛价由最初的每百市斤白银十两转手天津涨到三十至四十两。丰厚的利润,对驻庄天津的十大洋行有着极大吸引力。
什么是藏客?湟源首批藏客,进藏时间约在民国10年(公元1921年),至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原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黎丹组成西藏巡礼团,前往拉萨考察时亦请他们结伴同行。上个世纪30年代,藏商队伍逐渐扩大,一些富商眼看藏客生意兴隆,获利可观,遂不避路途艰辛,长途跋涉之苦,跃跃欲试,以展雄图。藏客进藏时,采办的主要商品是:以骡马为大宗,其次是生活用品,有湟源陈醋、威远烧酒、陕西红枣、柿饼及景德镇龙碗,还有少量枪支,名为自卫枪,领有护照,但至藏后,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丹地至西藏行程约6000华里,行程近四个月,路途遥远而艰难,途中骡马及货物损耗亦属不小,但只要平安进入西藏,获利也巨。以大宗骡马为例,在湟源以白洋300元购进的,到西藏只要顾主看中,可以卖到白洋1600元;再如烧酒,每市斤约合白洋三角,而售价一盅(约二两多)酒可卖白洋五元。酒、醋是用木筲包装,待运至西藏,其消耗已在一半以上,但其利润十分可观。藏客返回时,运往内地的商品仍然以民族用品为主,如氆氇、藏香、经卷、金线、水獭皮、名贵药材、藏红花、斜布(俗称藏斜)、皮鞋等获利上倍。从西藏购进每匹氆氇价60元,到湟源出售高达150元,水獭皮在西藏价是30元,到湟源出售就达90元以上。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遂以手表为大宗,手表体积小,便于携带,以罗马表为主,是上世纪5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鲜货,获利很厚。湟源藏客返回时,由藏政府尕本宴请即将返回湟源的商人(包括青海各地的在藏商人),一是为了会面(尕本每三年一换);二是商定起程时间,一般是农历九月从拉萨起程,年底抵湟;三是由尕本负责解决各商家的驮牛。议事结束后,由尕本带领,在拉萨八角街举行祭神仪式并骑马环行八角街一周。宴请即告结束,按期起程。
解放前湟源人到西藏做生意,深受藏人的喜爱和尊敬,藏人称湟源人为“西令巴”,认为是佛祖宗喀巴的娘家人,颇受青睐,藏政府特别允许在西藏购置房地产,允许筑室娶妻,办理出境(如印度、尼泊尔)手续也及时方便。
以上所述明显看出清政府、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采取的特殊措施以及顺运而生的“歇家”、牙行、洋行、藏客使清代湟源民族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牧产品和日用百货生活用品贸易存在,保障了从事单一游牧经济的蒙藏民族对于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大量的畜产品、药材进入湟源而集散内地,内地的日用百货也大宗输向湟源,也促进中原腹地的经济发展,正是这种互补互利起中介的湟源,由一片不毛之地一举成为湟水上游环湖区域性的商业重镇,发挥了青藏高原与内地经济联系、物资交流的枢纽作用,正由于此,环海商都之名遐迩闻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领事馆在中国西北旅行》一书中无不惊叹地写道:“西宁丹噶尔(今湟源)是伟大的青海湖贸易中心,贸易如今达到非常大的规模”。《丹噶尔厅志》也一呼三叹地写道:“迄今商业发达,几成巨埠,岁输白金数十万,盛矣!”
三、丹噶尔财富所谓传奇的要核
阅读以上什么是“歇家”、牙行、洋行、藏客畅晓明白,丹噶尔财富传奇在什么地方,它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人文特色是什么?它之所以在西陲不毛之地一举发展成为环湖国际贸易中心,“小北京”其来龙去脉,说得绘声绘色,历历在目。如果翻开《丹噶尔历史渊薮》、《湟源史话》、《河湟历史文化纪实》,一清二楚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丹噶尔财富传奇要核,概括起来是:(一)区位交通的战略地位;(二)周边环境的不断优化;(三)厅署招商的特殊举措;(四)国际资本的大量投入;(五)能工巧匠的荟萃智慧;(六)军事保商的强力抓手;(七)行会组织的新兴崛起;(八)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九)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十)商贸交易的繁荣昌盛等。这些多元元素的作用,使远在昆仑深处的玉石、戈壁浩瀚的青盐、祁连山下的骏马、中原内地的日用百货、环海周边畜牧产品,都能在这里自由贸易。据《湟源史话》记载:民国13年(公元1924年)集散牛羊25000只(头);羊毛500万斤;各类皮件30万张;青盐30万石;湟鱼20万尾;大黄10万斤;鹿茸2000架等等,如此大宗商品专销国内外,中原各种洋货、珍珠玛瑙、茶粮布匹、陶器五金涌进丹噶尔,古城商民3000余家,各类手工作坊1000多户,国际十大洋行开庄设行,国内30多家著名商号开铺坐庄,本地48家“歇家”、72户藏客,省垣商贾大家来此进货,当时流动资金白银500万两,可谓“跃马昆仑,驰骋中原,万象更新,极盛一时”。电视专题片《丹噶尔财富传奇》反映了这些吗?挖掘了这些吗?以上中台,不亦慎乎!
关于读物《青海之书》
关于读物《青海之书》中被一些学者所谓权威炒作,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什么“除了那种导游词式的风光介绍外,任何对青海的书写都是困难的”,不由分说,除了他写的《青海之书》还没有人写,即使写也写不好。笔者粗读《青海之书》,也特别关照了有些章节,诸如“茶马古道,高原上的商业暗道”,“日月山,藏汉地理和文化分界线”等,甚觉作者有些奇谈怪论,刁钻古怪,令笔者大惑不解。不知所以,也不见经传,大谬不然,不平则鸣。
首先笔者肯定,丹噶尔古城不能冠名茶马古道,也不是暗道。据史记载:这块古老土地上,秦代时是雍州古道,西汉时是湟中羌道,东晋时是丝绸南路,北魏时是求经孔道,唐代时是唐蕃古道,元明清三朝是官马大道,民国时是青藏卫道,新中国成立后是109国道等,历史上的“八路汇通”都经丹噶尔,是古道交通的要冲关隘,故称“海藏咽喉”、“海藏通衢”。然而史书上从来没提到这里是“茶马古道”。笔者于2002年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云南召开的“茶马古道”论坛,并实地参观考察了那里的茶马古道。所谓茶马古道由马背驮茶,行走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马不并双,人跟马后”,行走非常艰难。
据考证,云南茶马古道兴于明代,衰于新中国以后,与中原“八路汇通”,尤其与丝绸之路、著名的唐蕃古道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没有茶马古道的称谓?原因是丝路和唐蕃古道超过商贸的范畴,有他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诸多元素,所谓茶马古道,其内涵、地位、作用在这里不可能超越丝路和唐蕃古道,而统局其上,或凌驾于上。
其次,《青海之书》管中窥豹,谬误多处,以下就作者原文用双引号摘出,并加笔者补正如下:
(一)“西汉以来,丹噶尔古城仅成为商贸中心。”必须指出,丹噶尔是清代湟源的称谓,至今不过200多年的历史,称丹噶尔为商贸中心也只有100多年的存在,所以湟源自古称“丹噶尔”也是错误的,把它提到西汉更是啼笑皆非。据《青海通史》记载:西汉时将军赵充国率军进军河湟,平定羌乱,在今湟源县东南修筑临羌城,汉王朝设护羌校尉,管理羌族事务,所以西汉至唐、宋、元、明以来,湟源也是一片不毛之地,哪能算得上商贸中心。
(二)“唐代的石堡城、定戎城、绥戎城、哈拉库图城”,这里作者把哈拉库图城列入唐代古城纯属子虚乌有。从史书寻觅,最早在明代称“夏拉号图”,清代《西宁府新志》中记载: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修筑古城,称“哈拉库图城”,史书中还有“河拉库图尔”、“托拉图”是蒙古语,意为黄色。民国改称“哈城”。所以把清代古城提升到唐代古城,时间跨度达1300多年,与史相悖。
(三)“当英、法、美、俄等国商人来到这里设洋行”。其实这里面作者有“画蛇添足”之嫌。据《湟源县志》、《青海商业志》记载:洋行最早在湟源是由英国人设的新泰兴、仁记、天长仁,美国的和平、居里、瑞记,后来陆续进驻的有俄国的美最斯、华北,土耳其的瓦利等。就是没有法国的,而且不是上述各国的商人,而替代他们的是平津商贾买办。
(四)“古城依然保存着镇海协营、中军都司、千总、把总、演武场名称或遗址。”如果作者近年去过丹噶尔古城,罗列的这些名称早已时过境迁,其遗址早已销声匿迹,如今只有新修的“将军府”。作者如果是听到,从哪听到?如果是看到,作者还有欠缺。追溯源头,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清代筑城后,首先设置了军事机关丹噶尔营,以参将衔。
(五)“藏商(歇家)”,作者在介绍“藏商”时用括号括上“歇家”,表明“藏商就是歇家”。其实藏商不是歇家,这是作者主观臆断的。据《湟源史话》记载:歇家是清代领有官府营业执照,为蒙藏牧民和洋行做商务中介的代理代办;藏商是民国时期去西藏经商的商人的称谓,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故绝对不能划等号,混淆其职能。
(六)“四合院”、“是小北京的一个依据”。这是作者对“小北京”最狭隘的诠释。“小北京”的荣誉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民俗、民风等诸多元素,其文化蕴涵非常厚重。所以,对“小北京”定位,不能以点代面,更不能以偏概全,就按作者说的“四合院”,也只是美称,“小北京”建房风的一部分。据实记载:当时丹噶尔有宴席风(肉八盘、海八盘、四平碗、十三巧),娱乐风(跑马、麻将、京腔、秦腔),服饰风(男性长袍马褂、女性旗袍),建筑风(庙宇、官府、学校、仓院),玩古风(古董、玉器)等与北京雷同,故称“小北京”。
(七)有关日月山的章节中,凸凹不平,含糊其辞,诸如日月亭修建于1984年,当时青海省长黄静波提议并拨款120万修建的,作者说1980年;其东是分水岭,又称噶尔臧岭,作者却说日月山东是药水峡;“日月山的隆起,倒淌河在无奈中低头向西”,其实,在日月山没有隆起之前,布哈河从东流入青海湖,青海湖是外流湖,当日月山隆起后,布哈河遗弃的河道,注入发源于騩山(今称野牛山)小溪,向西流入青海湖,形成了“大河都东流,唯我向西去”的倒淌河,日月山又称赤岭,作者说“赤兔岭”。
(八)“公元4年,地处青海湖的西海郡设立,最初叫‘西平郡”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汉时这里称“金城郡”,三国、两晋时才称“西平郡”。
(九)“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九字虎形碑”。据《青海通史》记载:应是22个篆字,即“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不是作者说的“九字虎形碑”而是上下两层的虎符与石匮,匮即柜。
(十)“唃厮啰意为佛子”,但据《青海通史》、《青唐传》记载:“唃”是佛,“厮啰”是儿子,意为佛子。
(十一)“隋炀帝将今乐都县赐名‘鄯州,取消了王莽时期的‘西海郡之名”。据《青海通史》记载: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崩溃,西海郡随之废除,共存在时间为19年,所以到了隋代时过600多年,无须隋炀帝宣布,西海郡早就销声匿迹,成为历史上的符号。
(十二)“后宏期,三贤哲的藏·饶赛·肴格迥·玛尔·释迦牟尼”。作者所标的三贤哲全用“·”,通读起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三贤哲指的是姚·格郡,藏·饶赛,玛·释迦牟尼。
(十三)“藏语塔尔寺的巴贤巴林,意为十万狮子吼佛像弥勒佛寺”。据《青海藏传寺院》记载:“塔尔寺,藏语,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身像弥勒佛州寺。”
(十四)“在藏语和蒙古语中,西海叫作‘青色的湖青海由此得名”。据《西部漫行》记载:青海湖藏语称“措温布”,蒙古语称“库库淖尔”,意为青色的湖。青海之名,始于北魏。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首次提出青海由此而得名,在这以前称“仙海”、“鲜海”、“卑禾羌海”,唐代诗中称“西海”。
(十五)“道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栉比共存”。作者忘记了青海宗教多元文化中,还有传统占居主位的儒学、西方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这些决不能遗忘在历史文化的角落。
(十六)“班禅博克多,班禅意为大学者圣者;博克多意为睿智英雄人物的尊称”。据《历代西部人物选传》记载:“班”是梵文班达智(元代著名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大的意思,“博克多”是蒙古语,对智慧兼备杰出人物的尊称。
(十七)“甘肃政务军务的护理都督张炳华下文指令马麒放弃玉树,任由四川管辖。”这个所谓指令与史相悖,据《青海通史》、《青海建省始末》记载:民国3年(公元1914年)西宁镇总兵、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上书甘肃都督张广建并呈北京政府“以速收玉树为他日恢复卫藏之计”,1915年3月北京政府决定玉树二十五族由甘肃管辖,四川军队即行撤退。
(十八)“1928年9月5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将青海改为行省。1928年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确定西宁为青海省治”。这里给读者莫名其妙的是“153次会议”怎么在9月5日、10月17日召开?
据《青海通史》、《青海建省始末》记载: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决定,9月17日发布命令,将青海、宁夏分别建为行省。9月21日任命孙连仲为省主席,9月24日任命九世班禅为委员。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又通过决议规定青海省所属,以西宁为省会。
(十九)“公元1724年2月西宁府正式成立。”据《西宁府新志》记载:西宁府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将明代西宁卫改为西宁府。
(二十)“玉树,一片遗址的意思”。作者的这个诠释有失水准,近来许多报刊杂志说“吉祥”的意思。不过笔者从《山海经》查阅,“玉树指不死的常青树”。
(二十一)“文成公主,在她之前有金城公主,在她之后有弘化公主”。作者在这里颠倒了,应当是和亲先有弘化公主(公元640年),中有文成公主(公元641年),后有金城公主(公元707年)。
(二十二)大非川战役“考虑到镇守西宁的郭待封”。大非川战役发生于公元670年,当时称“鄯县”,西宁之名见于北宋。
(二十三)“明清时,茶马互市从日月山逐步移到丹噶尔。”据《湟源县志》、《湟源史话》记载:明代称“俱尔湾”,明末清初称“德木尔卡”,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才称丹噶尔。
清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后,在治理《青海十三条》中提出在日月山设立茶马互市。所以依《青海之书》“明清时,茶马互市从日月山逐步移到丹噶尔”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历史记载。
(二十四)“青海省人民解放军军政委员会”这个提法不妥当,所有史料记载是“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
(二十五)“《山海经》称为生活在‘峚山中的‘峚人”。经笔者查阅《山海经》卷二(西次三经)中提到“峚山”,但无“峚人”的影子,所谓“峚山”中“峚人”是作者编造。
(二十六)“‘峚山在积石山西边,在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一带”。经笔者细阅《山海经》(西次三经)按图索骥,“峚山”在今格尔木以东,柴达木地域中。
(二十七)“峚人消失了,即便是明代的《明太宗实录》也称呼这里众生为果迷卜咂族,后来称为思果迷族。这些峚人的后裔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的曲什安河、恰恰河……”
这里明太宗应当是“明太祖”,在明代帝王年号中,从来没有太宗之称。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思果迷族,一曰果迷卜咂族,明洪武十三年招抚,在上隆卜西去卫(西宁)一百五十里,恰好在今海晏一带。
又在“申藏族”中记载:“居牧上思果迷,西近青海,汉西海郡地。”
(二十八)“《山海经》里的秘藏,峚人到羌人的1000年标题下,作者收集了一幅“山海经中峚山周围的峚人生活的场景。”经笔者查阅《山海经》发现(西次一经)是“英山一带”图本。据图标上看英山在陕西西安以东。作者把“英山”说成“峚山”,还凭空捏造“峚人生活场景”是对上古历史不负责任的“创新”。
从以上(二十五至二十八)几个方面看,有“峚山”没“峚人”;峚人后裔生活地方模棱两可;同时将陕西西安“英山”说成“峚山”,将“英山一带”一幅图“弄虚作假”说成是峚山周围的峚人生活场景,由此可见,所谓“峚人”历史上不存在的,是作者冥思苦索的。
再次,《青海之书》其资料大多抄袭,笔者只是指出部分抄袭的书目,诸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历代开拓西部人物选传》,该书中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扶持黄教的固始汗”、“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西部歌王王洛宾”等作者照抄不误;在该书第九章“庄学本,一个人类学者的影像青海”完全抄于200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一书;所有青藏高原动植物资料源于199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青海掠影》;有关青海马氏家族统治青海的资料全抄于200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步芳家族的兴衰》等。笔者在这里说明,前人呕心沥血研究的成果,后来者可以引用,但必须说明出处,这是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起码的道德品质。笔者粗略全书,表明作者对青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知之不多,甚至孤陋寡闻。笔者和李国权编著的《丹噶尔历史渊薮》,2010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其中许多摄影作品首次公开,弥足珍贵。洛克先生原摄影的底片收藏在湟源县档案馆,严密封存,从不对外开放,从底片到正式见诸于《丹噶尔历史渊薮》笔者花费了精力,付出了代价,而《青海之书》作者不可能从档案馆获取这些摄影原片,便顺手牵羊,原模原样照搬,放在自己作品中,装了门面;还有笔者在2010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湟源史话》、《环湖寻踪》中首次提出并定位的“湟源排灯”、“20余座古城”、“古城三峡”等都在《青海之书》中有所抄袭,不然,作者如果田野作业,深入调查,十年八载也无法写出来。作为“国内著名”记者,作《青海之书》视觉扫向何处?听觉落在何地?作者心知肚明。
纵观《青海之书》比较浮皮潦草,其中大多是老生常谈,没有鲜活新意,而且大多是抄袭改头换面的,除了做了几顶帽子外,没有什么超群绝伦。
作为青海的土著作家,笔者不敢妄自尊大,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必要展示笔者近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以正视听。这也正是《青海之书》作者查漏补缺,纠谬匡正的重要方面。
在昆仑文化方面:专著《发现古昆仑》、《西王母大专》等,文章有“西王母圣地新考”、“西王母石室有新说”、“从中国西部、环青海湖、黄水源头探寻昆仑文化”、“从地域、地名、地貌探寻昆仑文化渊源”、“大禹治水的历史与现实面面观”、“环青海湖是昆仑文化的发祥地”、“谁发现了古昆仑”等,约20万字。
在人文地理方面有专著《湟源彩珍》、《日月山风情》、《湟源史话》、《环湖寻踪》、《西部漫行》、《浪迹天涯》、《丹噶尔历史渊薮》、《河湟历史文化纪实》等,约300万字。主要文章有“羌人迁徙与后来诸多民族的融合”、“唐代三公主在河湟的光辉形象与传说”、“唐蕃古道的走向与历史意义”、“茶马互市的沿革与发展”、“扶持黄教的蒙古王”、“茶马互市日月山”、“湟源冠名小北京”、“青海湖祭海考证”、“青海建省的始末”等。
在青海这块土地上,笔者生活了70多个春秋,走遍了全省、全国,港澳台及东南亚,撰写过游记散文100多万字,毫不夸张地说,笔者对青海历史文化研究从内容、形式、深度、广度方面远胜过《青海之书》,不过笔者不吹不擂,也不炒作罢了。
青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长如江、深如海、写不完、道不尽,青海确有它的地域性、民族性、人文性,在国内外、海内外独一无二。《青海之书》作者以区区20万字概称《青海之书》未免妄自尊大、目无他文了吧!
最后笔者还有一件事,告诉读者,民国时期有位美国记者,从来没有到过青海,但他却写了《马步芳在青海》一书,有位作家没到石堡城,却接二连三发表石堡城作品,至今有些记者,刚到青海三天两后晌,就动笔撰文,笔者以为不管是到了或没到,想从别人撰写的现成资料或走马观花,或道听途说,那么他写出的东西肯定苍白无力,言之无物,可谓“盛名其下,其实难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