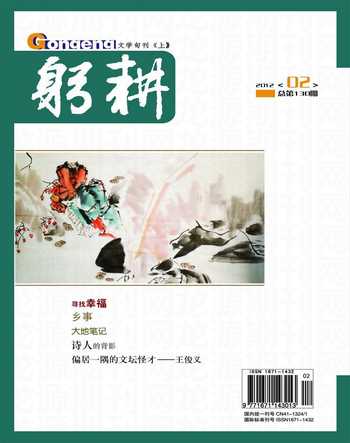大地笔记
向迅
稻谷上的村庄
把身子蹲下来,把头侧下去,偌大的一个村庄,似乎就生长在一片葱绿的禾苗之上。从这个角度望出去,那些红瓦白黛的房子与天上的云朵一样,都是随风而动的。还没有扬花的禾苗,似乎才是村庄的根和脚。
村庄,只是一粒古老的空谷壳。
我惊异于这个角度的发现,将很多原有的想念给颠覆了。
那个下午,如果你不在我的身边,是断然不会知道我发出了多少感慨的。出了长沙望城县靖港古镇,沿着湘江江堤上的马路向北逶迤而行,中途插入一条宽敞的泥土路。墙壁有些斑驳的院子,不时与我在笔直的泥土路上侧肩而过。不少正屋两侧,还搭建着稻草盖就的茅棚,其上是一派葳蕤的境况——长满了茂密的杂草。想必那都是喂养牲口的圈。院前的池塘里,荷叶田田,或红或粉或白的荷花,亭亭玉立。也有挤满了一瀑黄色花朵挂满了灰绿色瓜条的丝瓜架,蓬蓬勃勃地立在路边的坡坎上。鸡啊狗啊猫啊,或忙于生计,或趴在那里,以一双深邃的眼睛打探着你。
被那条泥土路分开的世界,虽与古镇近得离谱,却还是一个活着的村庄。
构成村庄的几个显著要素和那种令人心平气和的气息,都还保存得相当完好。作为一个从村庄里走出来的人,我对那种独属于村庄的气息,很是敏感——只要触摸得到它,我就有回到故乡的感觉——离开了村庄的人,总是容易对那些被农田包围着的院子,产生错觉。那条泥土路是外来侵入者的惟一通道,上面痕迹明显的车辙,即是明证。可它究竟还是大地的一部分,其上的野草们,从未放弃挣扎与突围——它们要重新占领那些被夷为平地的路面。
仅这些纯粹的乡村风物,已足够那些偶然的闯入者们消受了,可我更在意的,是以那条泥土路向两边铺排开去的稻田——那种绵延不绝的气势,是一部一咏三叹的农业史诗,是自农民心底挥掷而去的一大把排比句式的希望。绿色的禾苗,把个大地涂抹成了绿色的天空,直至那远处与灰色云朵连为一体的黑色山林。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找得出或创造得出比农田更富有诗意和美感的艺术作品了。漫长的时空跨度与比黄金白银更稀贵的价值,是其他任何一件人为的作品与发明,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这部史诗性的作品,是农民世代创作的结晶,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映。
我的胸中,也起伏着绿色的浪波。由于激动,我一下子拍下了好几段关于稻田的视频。我不知道,我为什会对农田抱有那么大的好感。特别是年龄愈大,这种感受愈强烈。当你深入稻田的田埂上,眼里就只剩下了那些还在拔节的禾苗;当你站在稻田中央环视一周后,发现稻田以外的事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矮了下去——需要用水灌溉的稻田,在村庄中所处的位置,或许是最低的,但一切又都在稻田之下——这才是大地上真正的高地。村庄和城市巨大的阴影,俨然成为这块高地无声的陪衬和虚化的幻影。
古老的稻谷,就是永恒的真理。
在稻谷跟前,一切都退居其次。
这天地间美到极致的所在,让人倍觉踏实。蹲在田间,我发现了那个特别的角度。这个角度,很好地体现了村庄与稻谷的二元关系。假若没有稻谷,没有高粱,没有玉米,没有土豆,村庄还成其为村庄么?只有漫漶着五谷芬芳的村庄,才是可靠的;只有炊烟缭绕的村庄,才是有温度的。
抬头的瞬间,一只在电线上歇脚的燕子,被一片挟带着禾苗清香的晚风惊起。我怔怔地望着它在村庄上空滑翔的身影,猛然记起了古镇水乡农耕文化展馆前的那副对联:
稻粱千古事,
稼穑一生业。
有生命的土地
我已然彻底变成了一个大地的观察者。
我对大地上事物的繁荣与衰落,对它们的此消彼长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眼里,似乎只有大地,只有那些让视野一下子变得异常辽阔的农田,只有那些与我们离得越来越远的山林,只有那些苟延残喘的动物与难得一见的蔚蓝色的天空。其他的事物,很难进入我的视野。我的审美趣味几乎全部聚焦在它们身上。我的一大部分感情,也投在它们身上。
尽管我有相当多的时间,都在远离它们的环境里疲于奔命。但我从未停止想念它们。
同时想念它们的,不止我一个人。
在我所寄居的那个小区,住着的都是一些公务人员。尽管小区管理处以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并三令五申住户不得在小区内种植蔬菜,可仍屡禁不止。这些种植行为,多半来自那些公务人员年老的父母。他们的身份不明,可能是退休在家闲来无事的老干部,也可能是被接进城的乡下父母。有一段时间在小区内散步的时候,发现很多住户前的花坛里的花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生长得一片旺盛的菜蔬。或许是受了管理处的警告吧,花坛恢复原样,重新栽上了月季一类的花草。可没过多久,花坛周围就多了一圈花盆,盆内的辣椒已开了一树米白色的小花,紫苏也长得眉清目秀。
不让种是吧,咱有的是办法。
小区内有一池塘,靠山的那一岸远离道路,就有好事者在柳树下摆放了若干大型花盆,春天是蒜苗,夏天是辣椒,秋天是青菜。还有南瓜的藤蔓,爬满了栅栏,丝瓜呢,吐了一树的黄色花朵。乍一看,还以为是老树开花了。不让种是吧,就有人翻过那道一人多高的栅栏,在山脚下开垦出一小片田地来,在其上也撒上了种子。栏内栏外的蔬菜们,时不时还握一下手,拥抱一下呢。最绝的是,在我所居住的楼后,竟然有人在墙根下种上了两垅土豆,生得虎头虎脑,光鲜得很,在五月竟还开出了朴素喜人的紫蓝色的花瓣。房檐下的空地上,是一大片密密麻麻麻的紫苏。后来才发现那个种土豆与紫苏的人,就是楼上的一个极慈祥的老妇人。她大概是从乡下来专门看管孙子的。可她一有空闲就坐不住了。
我的疑问在于,她把老家的锄头也带来了么?把老家的泥土、河流和天空也带来了么?
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沿着小区西门外一条直通这个城市所管辖的县城的大道上走走。这条超级宽敞的大道,是连接城区与郊区的一条大道。若干年以前,河西的这个区,是一片庞大的农田,是河东人一谈起就以为不耻,只偶尔过来调调口味的乡下。这条道路和现在我们望不到尽头的新城一样,都是踏着农田的血肉铺就而成的。在这几年里,我亲眼目睹了几个城中村的消亡——那些身份即将发生改变的农民,在被拆字包围的围墙里面的土地上,抢着种下了最后一个季节的蔬菜。那或许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在那些地方,买过农民刚刚从泥土里拔起来的水淋淋的蔬菜,其味道与菜市场的确乎有着天然之别——在一座被劈成一半的山丘与道路接壤的排水沟的上方,在一条逼仄得只能容下一只脚的土丘上,常年生长着时蔬。不时有农家粪的味道弥漫在道路的上空。我不知道它们是谁种下的,长长的一路蔬菜,似乎谁都可以摘一把。可究竟没有看见有人明目张胆地那样做过——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区域,但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原有的道德观念,依然还在约束着人们。虽然从这一块土地上转变了身份的人,可能正在变成城市猎人,或豺狼虎豹。
有一天,我竟然在那条大道旁的一角,又发现了一块菜地。而就在几天前,它还是一块碎石密布的废地呢。它的近旁是一个被高高的围墙圈起来的即将消失的村庄。毫无疑问,它们的命运是紧紧地绑在一起的。可又是谁,计算好了这块土地将在这个世上消亡的最后日期,而赶紧种上了一小畦四季豆呢?
那些长势良好的四季豆,无疑是对那一小块土地最好的安慰。
估计没有一块地,舍得放手阳光、雨水、空气与自由,而甘愿一生荒芜,甚至被水泥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见天日。
我对这些失去了土地,却依然想方设法进行种植的人,心存好感。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土地是有生命的。也只有这些人,才懂得珍惜土地,感恩土地。
我多次在作品中提及一件事情,即我在这条日渐繁荣起来的大道上,在一个即将完工的楼盘前的绿化带里,看见了一个简易而破败的土地庙。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周围拔地而起的楼盘中间,喧嚣的车声日夜刺激着它的耳膜。在这片土地还未被征用还未被城市揽入囊中的时候,这小小的土地庙,肯定是一块精神的高地。而现在,我不知道它从哪一块被征用的农田里被人搬过来,却是那么渺小。在它倾斜着的门框上有一行醒目的红色笔迹的对联:土中生万物;地里发千祥。每天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路过这里,他们或许看都不会看一眼这个破败的小房子,或许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这还是一座土地庙,但是有人懂得那副对联的深刻含义,懂得生万物发千样的土地——庙门前香烛的灰烬即是最好的证明。尽管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被打上迷信的罪名,但我相信热爱土地的人们,都会理解。
与其说他们供奉的是土地神,不如说他们拜祭的是一条与土地有关的真理。
无独有偶,也就是在前面我提及的那个下午,我从田野回到靖港古镇,在一条不算逼仄的街道上,遇上了一座名为福佑祠乌鸦洲土地的小庙。从名称上来看,建庙者是将土地与祖宗们一起供奉的。难怪在土地庙宇的隔壁还有一间小房子。对人类社会而言,土地与祖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等性。庙前也有一幅对联:土地恩泽生万物;福佑乌洲赐安康。这与前面那副对联是何其相似啊。
那个土地庙,离田野尚有一些距离,可它的香火从未停止燃烧过。虽与那些大庙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它依然是代表着一种无可替代的存在。
我推算那些前来供奉香火并义务打扫清洁的人,都是那些早已离开了农村生活的古镇居民。
大地上的寄居者
一生下来,我就被大人们哂笑为黑氏人口。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政府就按人头分了地。我没有赶上趟。以后也没有重新划分土地的事。这就意味着,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一个失去了土地的人,注定了我只能是一个暂时寄居在大地上的人。比我年幼五岁的妹妹,如果还谈自己有没有土地这样幼稚的问题,那就是痴心妄想,近于奢谈了。
很多年以前,我并不知道,如果拥有那么一两亩土地,是一件多么要紧的事;如果没有方寸之地呢,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
那些年头,虽然父母早出晚归,在那四亩多地里血汗经营,可每年春夏之交,真的会闹荒月——粮食每每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紧张。度过这样青黄不接的月份,不仅需要母亲的精打细算,还需要委屈那些牲口。我在这里说的粮食,仅仅指玉米和土豆两类粗粮,这是鄂西山地人的日常主食,同时也是牲口们的油。荒月里正是牲口们长架子的时候,油跟不上,或者稀稀拉拉的,都要受相当大的影响。
一些时候,我在心底一直在盘算这样的问题:按理说四亩地其实也不小了,为什么一年到头来还是不够一家人的口粮?还需要去田地多的人家买一些玉米?是不是父母种地不力,不懂得搞生产?
我把责任几乎都推向了父母,就如我面对读小学拖欠学费与生病时没钱治疗这样的事情一样,我都在心里暗自怀疑他们养家糊口的能力。当我现在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在整个院子里,除了田地多的几户人家外,其他的大都相差无几,没有余粮,没有余钱。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土地的多少。原本是三口人的土地,却硬要养活五口人,还有那么多的牲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些年头,包括现在,我一直羡慕那些土地多的人家。
前年回家过春节,我的六叔就告诉我,说他要给县里写信。我开始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吃了一惊。觉得闹腾到给县里反映情况的地步,非得是天大的事不可。
原来他是想让政府给他解决土地的问题。分家的时候,他仅分到一亩地。而现在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亩地怎么能养活四口人呢?我们在私底下算过一笔帐,假若他的两个孩子今后都在家里成家,那么一亩地就要一分为三了,每家三分地;如果是一个孩子在家,每家可分五分地。当然,最好的打算是两个孩子都能在城里安家落户。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他总是隐隐担心吃饭的问题,毕竟一亩地确实是太少了。六婶说,在那一块地里,根本就不能再套种其他的作物。一年的粮食,连一头猪都养不肥。六叔说,他要给县里反映这个问题,若不能解决,就反映到州里,再不行,就反映到省里,反映到国务院。
去年我没有回家,听母亲说,六叔和六婶带着小堂弟到外省打工去了。我不知道他到底给上面写过信没有。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父亲被迫走上打工之路的情形。到现在,他已在外打了十多年工,辗转了大半个国家,俨然一个老江湖了。父亲老了,可依然流落在外。几亩田地,实在种不出什么名堂。
这是发生在鄂西山地的真实境况。
近段日子,一个广西的朋友说他们村子里的人,几乎都迁到镇上去了。整个村庄,几成空城。原来生长庄稼的农田里,是遍地齐腰深的蒿草。我在他发过来的那些照片里,看见的确乎是一个颓唐村庄的影像。他说离开村庄的人,大多数都像他一样在沿海一带打工,挣钱后便发愤在镇上或者县城买房落户,以至于故园荒芜。几乎是同一时段,跟宁乡的一个朋友开玩笑说,我要去置几亩地,建一个草堂,过一把隐居生活。她便说买地的话呢,可以考虑去他们村子。村里有很多闲地,无人耕种。那些主人们,都到外面讨生活去啦。
想起这些掌故,胸腔里便堵得慌。在乡村,很多人因无田可种不得不背井离乡,可同时又有大片大片的良田因无人播种而沦为荒田野地。在城市,那些失去了土地的人,想方设法在旮旯和犄角处,种上一两棵玉米或几根青菜。
这样的悖论,让我无语。
寄居在城市的篱下,我认识了不少因城市扩张而失去了土地的人,他们要么在政府安排的工作岗位上谨小慎微的工作着,要么呆在家里无所适从。一双被农业文明打磨得异常粗糙的手,不再握锄头,不再接触泥土,却又怎么也闲不下来。我想在他们的下意识里,一定是在不断重复握锄头的动作,仍是在以劳作时间安排现在的生活秩序。
他们是被剥夺了农民身份的一群人。
不少人一辈子都在指望有一天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可当这种几乎不可能的妄想,有一天真的从天而降,他又整日不得安宁,失魂落魄似的,像丢了一件祖传的宝物。既住不惯鸟笼子似的房子,又没有熟人说话,还不能像过去那样无拘无束,孤独得活像被故乡抛弃了的孤儿。
仍然是上文所述的那个下午,我在那条泥土路的正中央,发现了一条被车轮活活轧进泥土路面的蛇。很显然,它已经死掉了。肯定是它正在跨越那条路的时候,被迎面而来的一辆车给结束了性命。这是一起蓄意的谋杀事件?还是仅仅属于一次意外的车祸?我们只能是根据现场进行无用的猜测。那条蛇,或许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明不白地死掉了。事实上只能说明,在不断变化的生活面前,它还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或许它把那条即将被水泥覆盖的马路,仍然当成了自己熟悉的地盘。
同样是这个夏天,我还看见了另外的一条蛇。那时,我正从公交车上跳下来,而它正盘在绿化带下烫人的马路上。我们把彼此都吓了一跳。根据花纹判断,那是一条毒蛇。马路的背后,就是一座小山。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它从山下爬将下来,躺在那条随时都可能毙命的马路上。虽然我只望了它一眼,便掉头快步走开了,却给它设想了几种命运:返回山上;被好事者打死;过马路时被车轮轧死……
这几种命运都是可能发生的,只有一种,希望实在渺茫得很,甚至是绝无可能的。那即是穿过那些望不见尽头的马路,越过这座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城市,去到地广物博、气候怡人的乡下。
大地的声音
秋虫唧唧的叫鸣,把个初秋的夜晚闹腾得丰腴而清凉。
不是一颗枯叶上的露珠,我也沉浸于如此浓稠却又轮廓分明的夜晚——像是有人握着橹,在墨绿色的水面摇落起一片一片珍珠似的水声。一整个夏天,就是在它们的鸣叫声中过去了;我经历的那些不算短的岁月,就是在它们的鸣叫声中过去了。那些唧唧声,好似就是时间的一种比较具体的呈现形式。我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近三十个夏天,竟被我故作大方地一掷而去——我没有一次认真地聆听那些动人的唧唧声。直到这个晚上,我才坐在一方池塘边,平心静气地聆听了一次那来自山野和草木间的小提琴交响曲。
繁星一般密集的鸣叫声,从池塘对面的一叠浓墨泼就似的小山里和岸边的草丛中源源不断地传诵出来。
——唧——唧——啾——啾——
此起彼伏,高低错落,远近有致。
初闻其声,以为杂乱无章,重复无趣,只是风吹草动惊起的回声罢了。但倘若把眼睛闭起来,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了——安详的大地,就如一架巨型琴键,而那些不甘寂寞的虫子呢,都是一些技艺绝佳的琴手,或避于一片树叶下,或站在一块爬满了青苔的石头上,或攀在一根草茎上,对着渺远的夜空,优雅发声,忘乎所以地尽兴弹奏——但我总是在它们的声息中,闻见了那么一点淡淡的哀戚和愁绪。我想,这大概是因它们把自身的生命体悟也融进了曲子吧,更或是命运逼迫它们用身体发出唧啾之声的呢。
可这样的比喻总是有些欠妥——它们的鸣声,是那般有序,节奏分明,层次丰富,像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又像是来自深沉的大地。
我又想它们到底为何要这么不辞辛劳地夜夜长鸣呢?是在低声祈祷吧,是在高声歌唱吧,是在朗诵诗篇吧,是在念诵经文吧,是在呼朋引伴吧,是在促膝长谈吧……有那么一个时刻,我躺在池塘边湿漉漉的既做绿化树的围栏又充作了坐骑的条凳上,双手情不自禁地和着那隐秘的节奏,在空气中像音乐指挥家那么划动起来——那些音乐竟惊奇地在我的手臂和呼吸间流动起来;那些音乐,像低垂的夜幕里极柔和的云朵;更像来自我的身体,我的灵魂。
我在一处草丛边蹲下来,捕捉到了两首独奏曲——它们分别来自两只我并未发现身影的促织——啾——啾——我学不来它们的叫声。我莫名的惊诧,继而又莫名地激动起来。我感觉天与地在此刻与我离得特别近,我就像一个睡在襁褓中的婴儿,在旋律优美的摇篮曲中,抵达天堂。
我心底还是无比清楚的,那鸣声,分明是生命的歌声,是生命的象征,是生命的旗帜——是大地的声音。
不止是那池塘对岸林深叶茂的山林,只要是那些没有被水泥覆盖和倾轧的泥土里,夏秋时节,就会有虫子们的歌唱和伴奏;这无言的故乡,就生长着无数生命。即使是那些密实而堡垒森严的水泥地之下,也有生命在无声活动;即使是干净而空荡的水泥地之上,那些哪怕是仅仅落得下一粒草籽的小小坑洼里,也会有精瘦的绿色,可怜巴巴地冒出来呢。
我知道,很多虫子的生命仅止于夏秋两季。秋天一过,它们要么深入泥土预备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天;要么连同它们飘荡在草木间的歌声和一缕精魂,化成了那么一小点泥土。生命究竟是短暂的,可它们用歌声构筑的那个音乐世界,是多么宽广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它们的舞台,大地万物,都变成了它们的听众。不仅是包括我在内的人,就是那些树木与月儿,也都静静地聆听着那生命精彩的绝唱。
虫子们的精神世界,真是海阔天空。
歌者的一生,哪怕繁华落尽,却仍然余音不绝。